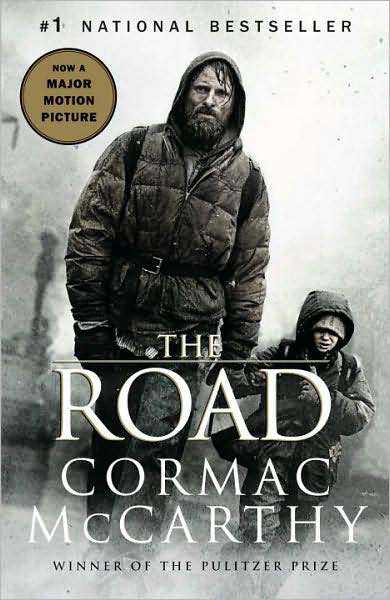
「TheRoad長路」之不好讀,在於形式,或許是作者Cormac McCarthy的個人風格,但在我而言,由於對作者的完全陌生(正嘗試另一本已改編為電影《險路勿近》的No Country for Old Men),我寧可相信McCarthy採用了如此要言不繁的極簡、不分段落的文體形式,便是希望構築一個荒漠、荒蕪的世界,、拉墜讀者的心、不讓讀者享受閱讀的快樂,並且讓讀者陷入如同書中父子一般的困厄無助情境,無法在章節分段中稍事停頓、喘息,一步步往毫無希望的未來前行。
我一度放棄,在讀了3、40頁之後,不是因為對故事不了解,而是停停頓頓的毫無故事性!換手、從其他書籍中取得足夠的勇氣後,撿回來、耐著性子讀完,恍如掙脫了壟罩多日的灰黑色天幕,有股重返人世的得救感受,堪稱非常不舒坦的閱讀經驗。但我享受這不舒坦,甚至翻畢到最後一頁,又重新翻回扉頁,沉入「永劫」的循環。只是有個根本問題:我讀英文版,網路書店提供中文試讀,兩相對照下,中文文字顯得太過繁複,太多的形容詞說明,讓原文的粗礪給打磨、順平,卻也削減了力量。舉例而言,譬如the man dropped to his elbows to smell the pipe but the odor of gas was only a rumor, faint and stale翻譯作「男人趴下來嗅聞輸油管,石油的氣味卻像不實的流言,衰微且陳腐」,原文帶文藝氣息,還好,但He screwed down the plastic cap and wiped the bottle off with a rag and hefted it in his hand. Oil for their little slutlamp to light the long graydusks, the long gray dawns譯作「他旋緊塑膠瓶蓋,拿破布抹淨瓶身,掂掂瓶子的重量:這是給小燈點亮漫長幽灰黃昏,與漫長霧灰清晨的油」,就有些過於矯飾而讓我不能接受了!顯然中文譯作繁複的語詞雖然豐美,卻失去了原著單調、貧脊的刻意形式,或許譯者十分為難,在缺乏故事架構下,如何營造氣氛、吸引讀者,跟隨著孤獨的父與子踽踽獨行下去?
永劫回歸:「對這個思想我們以它最可怕的形式來想想看,既沒有意義也沒有目標,由無出發又回到無,是不可避免的回歸,永遠如此,即永遠的回歸(die ewige Wiederkhr),這就是虛無主義的極限形式 -- 尼采」。這種末世來臨的景象,讓「希望」二字從未真正出現在書中,當文明消逝後,舉目盡是一片灰濛濛的大地,天不藍地不綠,連海水都是黑的,紛飛的雨雪嚴厲而冷酷,不僅無法將大地洗滌乾淨,反而讓萬物成為天地間的芻狗,只能在廢墟中翻找文明曾經的証明,和生存的可能,殘喘苟活、無盡無止。在至卑至賤、毫無尊嚴的掙扎中,生命只剩痛苦、失去希望,小孩的母親,或有更多浩劫下倖存的生靈,無法忍受這痛苦而自願消失,去取得最後的解脫。但父親不願意放棄孩子,所以不放棄自己,父與子扶持著往一個可能較暖和的南方邁進,一個繼續生存的可能,如同希臘神話中的薛西佛斯,渺小隱晦的希望,因為沒有任何訊息告訴他們這希望是否真實,或僅僅想像。中文書的文案以「優美輓歌」做為這部書的題辭,優美或許難稱,但輓歌卻隱藏在書中的每一頁,死神手持鐮刀四處收割頹倒的靈魂。
薛西弗斯面對的是逞罰,即使無悔,仍成為從此不可脫逃的命運。大災難或許也可稱作集體逞罰,但父親有愛,小孩相信,兩人合力共同對抗灰暗的降臨,撐起一絲微弱的光亮。我不斷想像,如果換作是我呢?能不能堅持?願不願意為了孩子未來的一線可能,去忍受幾乎無望的煎熬?選擇放棄最簡單,一了百了、遠離痛苦,不必再忍飢捱餓,但怎麼能讓孩子失去對藍天綠地的想望?怎麼能讓孩子在未曾享受過人生之前,便先奪走一切?而在人搶人、人吃人的世界,是否還有必須堅持的價值、道德?有沒有上帝、信仰?這種種問題,我寧可不回答,更希望永遠不必面臨必須回答的時候。
「我總忘不了他在寫作過程中每天是怎樣折磨自己、給自己罪受。每天工作完了,他從書房裡出來,面容憔悴,有時還淚流汩汩,兩眼哭得通紅,看上去比早上走進書房那人要老上十歲……」這段文字,不是寫McCarthy,而是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劇作家Eugene O’Neill的妻子,在回憶他在寫作「長夜漫漫路迢迢(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時的糾纏和痛苦。我不認為McCarthy的書寫會是如此椎心刺骨,但2003年,已經70高齡的McCarthy攜著稚子途經德州的ElParso,在荒漠的客旅中想像,30、50年後,這一座座的城鎮將會是怎般的景象?如果天地間只存在踽踽獨走的父與子呢?當科學家、宗教家、政治家、預言家,各宗各派不斷威脅恐嚇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的時候,身為老父的McCarthy該多不捨孩子遭逢一絲ㄧ毫的痛苦,多盼望孩子能完整的成長,所以天塌下來,他絕對、一定要頂住。這種書寫的情緒緩慢縕釀了三年,或許因為對末世描寫的書籍太多了,而力挽狂瀾的英雄也太多,McCarthy了解英雄無稽也不可靠,殘破不堪的世界,能依持的,只剩無私、不捨的愛,以及因此而生的勇氣:
"What's the bravest thing you ever did? "
He spat in the road a bloody phlegm. "Getting up this morning, " he said.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