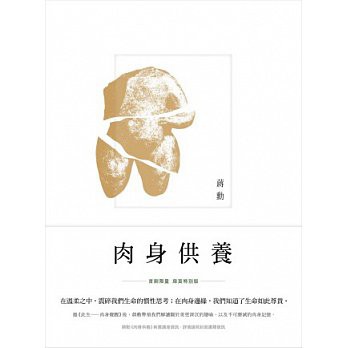
美學系列:肉身故事與神話世界
文╱蔣勳
普羅米修斯身上那一塊永遠解不開的石頭,常讓我想到《紅樓夢》一開始丟棄在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的那一塊石頭……
好幾年沒有在冬季回到巴黎了。有一點忘了這個城市在沒有花的繽紛、沒有樹葉濃蔭的冬天,原來是這麼蕭瑟、清冷、澄淨,像水晶或琉璃中凝凍的光,像波特萊爾一句散文詩。
灰色的天空浮走著灰色的雲,高大刺入天際的梧桐、橡樹的枝莖,一縷一縷,像倒懸飄揚的髮絲,在寒風的流光裡搖晃顫動。
走過一片一片鋪得厚厚的枯葉,聽到地上沙沙作響。是自己留在枯葉上的腳步聲,也是他人的腳步聲,錯綜疊沓,彷彿許多世紀以來走過、卻始終走不過去的腳步的聲音,在一個冬季的枯葉上停留著。和風、和雨水、和殘雪混合,透露出一點慢慢腐爛卻十分清新鮮明的植物的氣味。
走過塞納河,有一點忘了河流可以如此潺潺湲湲,流著銀灰色如金屬一樣冷靜的光,在橋墩下迴旋盪漾,彷彿徘徊、踟躕、游移,捨不得立刻就走,然而,終究浩浩蕩蕩朝向夕陽遙遠寬闊的天邊澎湃洶湧流去了。
冬季的巴黎,像路旁豎著衣領匆匆快步走過的路人,目不旁視,好像不希望被人看見,要在一陣風裡消逝。除非強風吹掉了帽子或圍巾,只好抱怨著,一臉不高興,但還是必須回頭追著風、趕著去撿拾。
低頭撿起帽子,發現一地都是落葉,四處翻滾散落,然而沒有一棵樹會低下頭多看一眼。
城市的時光是這樣逝去的,都以為只有自己留下腳步聲,卻不容易聽見每一世紀所有走過的腳步聲都還留在枯葉上,沒有一個曾經離去。初讀Camus,也總是聽到他沙沙的腳步聲踩在入冬以後河邊的枯葉上。
鎖
河上的幾座橋,到了冬天,不常有行人。
藝術橋(pont des arts)在夏天的傍晚,擠滿人群。認識的,不認識的,靠在一起,講話、抽菸、喝酒,很快熟了,擁抱著,或很快分手了,說:再見。但大部分知道,不會再見了。
見面與分手都不艱難,好像也少了情感的深度。
不知道為什麼,藝術橋的鐵欄杆上這兩年突然多了好多鎖。第一次看到這樣密密麻麻上千上萬的鎖,是在上一世紀八O年代的黃山。沿路的護欄上也是這樣密密麻麻扣著上千上萬的鎖。有專門賣鎖的人,替遊客把姓名快速鐫刻在鎖上,扣在護欄上,發願、祝禱,永遠在一起,然後把鑰匙遠遠扔向山谷。沒有鑰匙的鎖,再也打不開的鎖,祈願的人好像也相信可以永遠不分開了。
我細看了一下,鎖上鐫刻的名字,很多是夫妻、愛侶,兩個人的姓名,有時候圈在一個同心結中。也有的姓名是兄弟三人,或姊妹倆人,也有貪心的,把一家父母兄弟姊妹都刻上去,加上「不離不棄」「永不分離」等字樣。
黃山山路陡峻、坎坷、崎嶇,風景奇險,步步驚魂。一路上看著這麼多鎖,這麼多鎖上的名字,這麼多海枯石爛、生死不渝的銘刻,這麼多沒有鑰匙、永遠打不開的鎖,這麼多希望不再分離的親人愛侶的願望,心裡一陣一陣心酸。
文革十年浩劫剛結束不久,大概知道,重新活下來、親愛的人可以在一起生活,是多麼恐懼「離」「散」,要用一把一把的鎖,把彼此「鎖」在一起,要把可以打開鎖的鑰匙用力扔到遠方。
其實,在華人傳統裡,一直有給孩子頸脖上掛鎖的習俗。孩子誕生,親友送禮,也還會用黃金、白銀打一個鎖片做禮物。我去巴黎讀書時,母親給我打過一個特大號的銀鎖片,我當時其實還不知道「鎖」在一起,對戰亂中離散過的人有多麼深重的象徵涵義。
但是,華人「鎖」的符號象徵,為什麼會飄洋過海到了巴黎?是華人觀光客在這城市的祈願嗎?美好的度假時光,把自己跟親人鎖在異國的城市橋梁上,把鑰匙扔進塞納河裡,再也找不到,再也打不開,就可以生生世世不再分開了。半世紀以來,相見與分離都不艱難的巴黎人,可以了解這樣一把一把鎖相扣、相堆疊、密密麻麻牽連糾纏在一起的象徵意義嗎(圖一)?

石頭
永世不再分開,是說肉身的不離不棄嗎?還是說心靈的牽掛纏綿?那像是神話裡的故事,像普羅米修斯把火帶給人類,因此受諸神詛咒,懲罰他的肉身,永遠鎖在懸崖岩壁上,每日被兀鷹撕開胸膛,啄食肝臟,夜裡復元,次日再受撕裂啄食的劇痛。
跟普羅米修斯鎖在一起的,幾世幾劫,只是天荒地老堅硬冰冷永不動情的岩石。(圖二)
後來,赫克力士來解救他,為普羅米修斯剪開鐵鏈,但是,為了要瞞過諸神監視,就讓一塊岩石跟普羅米修斯永遠鎖在一起,永遠不會分開。那是諸神的鎖,是永世的詛咒,永遠打不開。
普羅米修斯身上那一塊永遠解不開的石頭,常讓我想到《紅樓夢》一開始丟棄在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的那一塊石頭。
那一塊石頭自怨自艾,幾世幾劫,就修成了人的肉身,他(它)轉世投胎,來到人間,就是賈寶玉。寶玉誕生時,口中還啣著那一塊石頭,石頭上鐫刻了字「莫失莫忘」,繫了五彩絲縧,掛在頸項上,也就是人人稱讚的「寶玉」。
或許,有緣就是寶玉,撒手去了,其實也只是洪荒中一塊可有可無的頑石罷了。
青埂峰下那一塊石頭,永遠鎖在普羅米修斯身上的那一塊石頭,都是神話世界的肉身故事,流浪生死,幾世幾劫,要了結自己與自己肉身的緣分。
華人的世界,肉身的故事,是一塊大荒中的石頭,一株靈河岸邊的絳珠草。那肉身還是草木頑石,還沒有人的形貌,連動物的體溫也還沒有,然而它們嚮往成為人,即使要在人間塵世受愛恨之苦。
白蛇的故事也是用幾百年的時間,日日夜夜,取日月雨露精華,修成女子的肉身。如此艱難,要忍受幾世幾劫的孤獨,一心修成肉身,然而這肉體剛剛取得,這女子的肉身就要去西湖岸邊,在春日明媚的細雨迷濛裡遇見宿命中鎖在一起的另一個肉體。
有人覺得巴黎橋梁上的鎖很醜,有人覺得在橋上兜售鎖的商販很壞,像詐騙集團,敲詐觀光客。有人覺得兩個遊客傻傻地買鎖,刻名字,念念有詞,不離不棄,把鎖鎖好,把鑰匙丟進河裡,真是很愚蠢。
「太愚蠢了!」我聽到有過路的人搖頭嘆息。
但那兩個默禱的人,手指相扣,不會聽別人瑣碎嘮叨。他們一心一意的虔誠專注,也讓我覺得心酸。
祈願,對不關痛癢的局外人,本來就是愚蠢的吧。
不知道白素貞當年如果知道她的結局,是否還是決定要去遊湖、借傘?
法海其實是那個在旁邊一直鎖碎嘮叨的旁觀者,他總是自作聰明,「蛇怎麼可以跟人戀愛?」腦中有枷鎖,打不開,千方百計,一定要拆散許仙白蛇。
神話讓人謙卑,因為好的神話都不在意結局。白蛇的結局會有不同的版本,她(牠)是被法海壓在雷峰塔下受永世的懲罰,還是終於在兒子跪拜下塔倒現身。民間戲劇,有時結束在「合缽」,有時結束在「祭塔」,沒有人會質問哪種結局才是對的。喜歡執著對錯的頭腦,多半看不懂神話。
法海可悲,沒有人喜歡他,覺得他多管閒事,但他也可憐,因為他不知道自己執著。
有人硬要把神話用理性歸納成合邏輯的結局,神話也就死亡了。有文字以後的歷史,開始把口述神話的多元性定於一尊,只有一個版本,「怪、力、亂、神」,統統要歸納成邏輯,神話原來可以天馬行空,此時飛不起來,被硬生生拉下來,摔死了。強迫故事有一定的理性邏輯,也當然枯燥呆板乏味,像文革浩劫,所有樣板都無趣單調,沒有人要看。

該隱
走過菟勒麗公園,看到高高台座上站立一個用右手蒙面的裸體男子雕像,那肉身如此孤單無助,蒼天白雲,在枯樹林間彷彿哭泣、彷彿顫慄、彷彿無處可以躲藏,如此恐懼,如此孤獨,我心裡叫喊:「啊!該隱──」
我走近雕像,台坐上刻著幾個字母:CAIN,果然是該隱,那個殺死自己兄弟亞伯的人(圖三)。
為什麼我們知道他是該隱?他身上沒有任何標記,沒有可以辨認的衣物,沒有殺人的動作,然而在他的肉身裡看到如此清晰帶著該隱的慌恐怖懼。該隱是西方神話裡第一個犯「謀殺罪」的人類。
中學時聽神父講「創世紀」,講到亞當和夏娃,生了兩個兒子,一個該隱,一個亞伯。該隱種地,亞伯牧羊。該隱獻祭田裡收成的五穀,亞伯獻祭頭生的羊和油脂。耶和華神喜歡亞伯的供品,該隱就生氣發怒,在田間殺了兄弟亞伯。
神父慢慢念,耶和華問該隱:「你兄弟亞伯在哪裡?」該隱回答說:「不知道。」並且說:「我豈是看守我兄的嗎──」
我那時沒有看過該隱的繪畫或雕像,但腦海閃過一個恐慌孤獨的肉身,一個犯了罪,無處可以閃躲的肉身,就正是這尊雕像的樣子。
所以肉身是帶著這麼鮮明的故事的標記嗎?屍體銷毀了,殺人的凶器隱藏了,身上的髒汙洗去了,沾染血跡的衣服剝光了,然而「神」來質問:「你的兄弟亞伯在哪裡?」基督教的肉身是要在塵世間做救贖的,米開朗基羅的「最後審判」,所有死去的肉身,要再一次復活,接受審判。封印一個一個打開,天使吹起號角,死者重新從地裡起來。我總記得那巨大的畫面裡浮浮沉沉的肉身,上升的,下降的,聖潔的,墮落的,有人蒙著眼睛,不敢看自己將要墮入的深淵,有人手中用一串念珠,試圖拉起一個沉重向下墜落的身體。肉身這麼沉重,可以拉起來嗎?

肉身,可以輕盈一點嗎?
我想到經書裡耶和華神對該隱說的又像詛咒又像祝福的話:「你必流離飄盪在地上──」
肉身流離飄盪,像《地藏經》說的「流浪生死」嗎?
在世界神話的國度有多少肉身在「流離飄盪」,有多少肉身在一次一次經歷「生死流浪」。
濕婆
印度的神話裡,肉身是一世一世一界一界流轉的,不止人的肉身如此,神的肉身也一樣「流離飄盪」。
希臘的神話故事裡的肉身比較容易辨認,普羅米修斯、宙斯、維納斯、阿波羅、酒神戴奧尼索斯、牧神──幾乎都有一眼可以辨認的形象。印度的神話常常令人眼花撩亂,一個神祇,會有多到數十種化身,千變萬化,讓人摸不著頭腦,然而,印度神話的「無常」,是不是也正是破解執著單一邏輯的最好妙方呢。如果沒有隨佛教傳入中土的印度神話,光憑儒家方方正正的邏輯頭腦思考,大概很難有「西遊記」這樣一部上天下地、呼風喚雨、時時七十二變讓人驚嘆的好小說吧。
我喜歡看印度的舞蹈和戲劇,影響到整個東南亞廣大地區,肉身柔軟,嫵媚曼妙,四肢骨節可以不受拘束,手指可以如花瓣婉轉,他們彷彿相信肉身可以這樣自由沒有限制。一個文明裡,肉身不自由、不柔軟,不能包容變化,是因為頭腦心靈的老死僵化嗎?
印度教大神濕婆(SHIVA),可以忽男忽女、忽老忽少,人世間的分別,年齡、性別、相貌、甚至美醜、善惡,對祂都無分別。神與魔,一念之間,原來也多半只是自己執著。濕婆神和大部分印度神祇一樣,他們的行為事蹟,如果要用善惡邏輯來分辨,大概一定一頭霧水。在人界定的善惡是非裡執著,或許就難看到天意的廣闊吧。印度的神話世界「摩訶婆羅多」或是「羅摩衍那」令人驚訝,數千數萬眾生如微塵死滅,不以為惡,沒有憐憫,數千數萬眾生得救,不以為善,沒有喜悅。善、惡是人間是非,不知天意,執著自以為是的善,也可能恰好走向為惡。
印度神話裡主要的濕婆信仰,像是創造,也像是毀滅,像是善,也像是惡,他有「忿怒相」,青面獠牙,其他民族很難理解這也是「神」,然而「祂」卻真是「神」。「不可猜測你的神」,「神話世界」本來不是狹窄的「人」的故事,而是把「人」的各種相貌組裝成「神」。
不止印度神話世界「神」的行為「人」無法猜測,基督教舊約的「神」也不可猜測懷疑。耶和華要亞伯拉罕把獨生的兒子以撒帶到祭壇上獻祭,親生父親要親手殺死獨子,亞伯拉罕二話不說,綑綁以撒,放在祭台上,刀要刺進喉嚨,「神」才說:只是試探。《舊約》裡充滿神話的「不可思議」,可思,可議,大多沒有真正的大領悟。像濕婆神,領悟了,就可以在時間與空間裡來去自如,佛教後來吸收了原始印度教的濕婆信仰,「祂」就被稱為「大自在天」。
我喜歡看繪本裡的濕婆,像一個平凡的父親,看著妻子帕瓦蒂(Parvati)手裡抱著小象模樣的兒子「甘拏夏」(Ganesha),濕婆神一臉慈祥,若不是他頸項上帶著一長串頭骨,我們認不出祂是濕婆。祂和藹可親,手持淨瓶,為小象兒子灌沐(圖四)。

甘拏夏已經是世界知名的印度神了,東南亞各處可以看到祂,象頭長鼻,大肚皮,給人間帶來財富幸運。據說祂是從濕婆神笑聲裡誕生的,父親怕他太過漂亮嫵媚了,所以給他安上一個象的頭。但每次看到祂的長鼻子、細眼睛、大肚腹,還是忍不住發笑,愛發怒的人、怨恨多的人,多看看甘拏夏,大概真的會比較幸運吧。(上)
【酒神】
我喜歡希臘酒神的故事,祂的希臘名字叫Dionysus,羅馬人給祂換了一個拉丁名字叫Bacchus。我們如果真關心神話,就叫他酒神吧,酒神原可以不拘束在人的國度,也應該跳脫人的歷史。
酒神的爸爸是奧林帕斯山的眾神之王宙斯,宙斯最偉大的工作好像就是不斷戀愛、性交,繁衍後代。祂變成天鵝跟麗妲做愛,生下兩個蛋;祂變成白色的牛追求美女歐羅巴,祂甚至變成一道光,讓封鎖在高塔裡的美女黛娜(Danae)懷孕,祂也變成老鷹,擄走人間的俊美少年賈尼美弟(Ganymede)。宙斯和濕婆都一樣千變萬化,其實很像莊子寓言核心的逍遙遊。可惜莊子的「神話」「寓言」被後來邏輯頭腦註解成「哲學」,北溟裡的大魚,失去神話魔力,也就永遠飛不起來了,肉身沉重,無法摶扶搖直上九萬里,無法幻化成一飛數月不停息的、自由自在的大鵬鳥了。
回來說酒神故事:宙斯愛上了人間美女賽美樂(Semele),夜夜交歡,賽美樂已經懷孕,被宙斯妻子天后黑拉(Hera)發現。黑拉,這個可憐的女神,總是跟在丈夫後面抓姦,祂發現賽美樂懷孕,心生忌恨,設計要讓母子兩人都死於非命。
黑拉偽裝關心,告訴賽美樂,這夜夜來的男人,神龍見首不見尾,不可靠,要塞美樂當天晚上強迫宙斯顯現全身。宙斯的全身是雷火,賽美樂是人間平凡女子,不知是詭計,不知輕重,宙斯一現全身,她就當場暴斃。
宙斯心疼胎兒,就從賽美樂腹中救出,切開自己大腿,把胎兒藏好,在腿肉中養到足月誕生,就是以後的酒神。
父親是大神,母親是人間美女,在女人子宮受孕,雷火中救出,在男人血肉中成長,這嬰兒又被赫美斯(Hermes)迅速帶到水仙處養大,火中之水,注定了祂酩酊狂醉恍惚矛盾的肉身特質。
我在奧林匹亞看過古希臘嬰兒的酒神,抱在赫美斯手中。我也喜歡16世紀卡拉瓦喬畫的酒神,手中一杯紅酒,頭上葡萄葉冠,眼波流轉,是縱慾耽溺的肉身,一晌貪歡,那肉身像眼前一籃飽滿熟爛的果實,散發著濃郁的甜香氣味,甜熟已極,已經要敗壞腐爛了,像我們自己在歲月裡留不住的肉身。

【珀修斯殺梅杜莎】
希臘神話中的珀修斯太迷人了,在翡冷翠的領主廣場總是看著祂俊美的雕像,一手持刀,一手高舉剛斬下的蛇髮女妖梅杜莎(Medusa)的頭。
珀修斯的出生就令人驚嘆,祂的父親也是宙斯,阿爾果(Argos)城邦的國王得阿波羅神喻,預言說他將來會被孫子殺死。為了逃過神喻詛咒,國王就把女兒黛娜囚禁在密不通風的銅塔中,不讓她見人,覺得如此可以避免她懷孕,沒法生孫子,就能逃過神喻詛咒。希臘神話總是告訴人的自大多麼可笑,自以為是的國王沒有料到,宙斯可以探知美女所在,祂化身成一片黃金的光,穿透銅塔,就讓黛娜懷了孕,生下了珀修斯。
珀修斯是希臘神話的英雄,祂最重要的事蹟就是斬下了女妖梅杜莎的頭。梅杜莎一頭的蛇髮,千蛇萬蛇竄動,她最厲害的本事是任何生命一看到她,立刻就變成了石頭。
所有要前去斬殺梅杜莎的英雄一一變成了石塊,珀修斯如何完成祂艱鉅的使命?靠諸神幫助,珀修斯借來了有翅膀的飛鞋,借來了明亮如鏡的盾牌,珀修斯靠著盾牌的反映,不直接與梅杜莎視線接觸,逃過變成石頭的惡咒,看著鏡面,斬下了梅杜莎的頭。
神話的故事總是被一代一代演繹,沒有真正的作者,我喜歡卡爾維諾在他《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裡接著說的珀修斯的故事:珀修斯提著斬下的女妖的頭,滴下的血使周遭的眾生都變成石頭。珀修斯為免人世繼續受苦,便帶著那頭,潛進海底,鋪了些海草,把頭放好,因此海底的水草都僵硬石化成珊瑚了。
神話是肉身的故事,肉身驚恐、怖懼、痛苦,惶惑、流離,世世代代,還在尋找安心之處。神話必然使人安心吧,一代一代閱讀神話的生命,其實也不在意神話原典一成不變,珀修斯的故事不止卡爾維諾用來解釋他對下一世紀的祝福:多一點溫柔、多一點善良、多一點體貼、多一點平和、多一點安靜,在許多動漫、卡通、通俗電玩遊戲裡,也不難看到各式各樣、甚至搞笑版本的珀修斯。
神話沒有死亡,恰好是因為這些影響廣大的通俗版本吧,讓神化活在人們的喜悅開心的視覺聽覺與心靈分享裡,用語言傳送,用圖像傳承,而不單單限制在冰冷刻板的文字典籍中。
夜晚抬頭仰望澄淨清明的星空,會看到人們不斷傳述的神話英雄珀修斯,已經升成天空的星座,網路裡的星空,已經全是希臘神話的領域了,讓我們遺憾,織女、牛郎的故事呢?紫薇、北斗的故事呢?天狼、天璿、搖光的故事呢?曾經也有過神話的民族已經失去了祂們在現代星空的疆域了。
【九歌】
星空裡要重新生長出民族神話的故事,不知道是不是還要從那一塊大荒中的石頭說起?說石頭如何經過幾世幾劫,一心一意要修成人的肉身的故事。
我們的神話死亡太久了,失去了在星空裡的疆域。《九歌》、《山海經》,或許還保留著一點古老神話世界的肉身餘溫。然而,文字版本的《九歌》也距離庶民的生活太遠了。清楚看到,少數知識者壟斷的經典,都使文化生命枯槁,在大眾不聞不問的狀況下一一死亡。
明末清初,有見識的創作者試圖用圖像救活《九歌》,蕭雲從,陳洪綬,為諸神造像,讓諸神復活,重新詮釋東君(太陽神)、「湘夫人」(愛情之神)、「雲中君」(雲雨速度之神)、「大司命」(死亡之神)、「山鬼」(山林陰鬱之神)。三百年過去,《九歌》諸神,還是輸給了其他民族,蕭雲從、陳洪綬也太古老了,失去了孩子仰望星空的渴望,神話必然是活不過來的吧!
雲門《九歌》用現代觀點重新塑造諸神,玩滑板、直排輪鞋的「雲中君」,如同希臘的赫美斯,如同印度青色吹笛少年克里什那,追求青春、速度,追求解放愉悅的肉體,隨著世界巡迴演出的足跡,已在現代神話世界留下民族肉身的深刻記憶,「山鬼」在月光下的陰鬱、憂愁、自閉的心理空間,也連接著希臘如同ECHO女神退避到山洞深處的幽微回音。
神話世界必然無國界的隔閡,回到人性的原點,回到每一個肉身最基本的渴望,就有了傳承神話故事的可能。
仰望星空,還是想重說一次織女與牛郎的故事,他們的愛悅、眷戀、貪歡,都如此真實,他們的分離、孤獨、渴望,也如此真實。他們的肉身還在星空,隔著一條浩瀚的銀河,期盼一年一次的見面,小時侯,母親說到鵲橋,我總擔心,那樣弱小的一隻一隻喜鵲鳥的身體,如何搭成橋,如何承載兩個渴望見面的肉體,我的擔心讓母親笑起來,她說:那是神話啊!是的,我們都有過曾經相信神話的快樂童年,我們的民族,也應該有過相信神話的快樂而且心靈豐富的童年吧。(下)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