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暑閱讀:《破戰者上下冊》WARBREAKER
書名:《破戰者上下冊》WARBREAKER
作者:布蘭登.山德森(Brandon Sanderson)
西元一九七五年生於美國內布拉斯加州林肯市,從小就討厭死讀書,直到中學八年級時老師給了他一本芭芭拉.漢柏莉(Barbara Hambly)的《龍魘》,才一頭栽進奇幻小說的世界。他開始大量閱讀羅伯特.喬丹(Robert Jorden)、梅蘭妮.朗恩(Melanie Rawn)、歐森.史考特.卡德(Orson Scott Card)的書籍,甚至嘗試寫作。
大學時代的山德森更因為愛好寫作,在就讀楊百翰大學時從生物化學轉至英文系,讓原本期待他從醫的父母大吃一驚。當時他在旅館當夜班櫃檯人員,趁著工作空檔寫作不輟,半工半讀完成學業。光是大學時代他就完成了七部小說,期間屢屢遭到退稿,直到二○○三年終於獲得美國奇幻最大出版社Tor編輯莫許.費德青睞。
二○○五年,山德森的首部作品《伊嵐翠》在美出版。數年內,「迷霧之子」三部曲、番外篇及《破戰者》陸續問世,構思已久的「颶光典籍」系列首部曲終於付梓,期間執筆續寫偶像喬丹的「時光之輪」系列更是叫好叫座。截至目前,山德森的作品已翻譯成超過二十種語言,全球銷售累計破三百萬冊。曾自稱是「夢想家」的山德森仍以驚人的速度創作,持續將自己的夢想幻化成書,與全球讀者共同分享。
譯者:章澤儀
西元一九九四年畢業於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曾任職於出版社、網路科技公司與廣告綜合代理商。自一九九三年起從事英日文筆譯。近年正為治不好的龜毛症所苦。
譯作有《啤酒世界紀行》、《大地的咆哮》、《日本外交史話》,小說譯作有《鹽之街》、《圖書館內亂》、《圖書館危機》、《熾熱之夢》、《打工族買屋記》等。
內容介紹:
布蘭登.山德森又一獨立鉅作
以神蹟與色彩渲染而成的奇幻舞台
哈蘭隼,一個充滿了鮮艷色彩的國度。市井中,識喚術士從他人處取得駐氣,一面吞噬周圍的色彩,一面以命令語施展奇蹟。廟堂上,死而復生的復歸者被視為神明,享盡榮華之餘,還靠著人民定期呈貢的駐氣延續生命。
義卓司,三百年前流亡皇室所建立的邊境小國。他們視取得他人駐氣為禁忌。為了防止識喚術的施展,義卓司人盡可能地辟除色彩,國境內不是灰色便是暗土色。
兩國大戰一觸即發。為了緩和緊張情勢,義卓司國王採取聯之計,叛逆活潑的小公主希麗,臨時取代信仰虔誠的大公主維溫娜,她將進入一個充滿死魂僕、識喚術士與異教徒的陌生國度,孤身面對汲取他人靈魂以延命的眾神、懷著敵意的祭司,以及高高在上、難以捉摸的「神君」。而從小接受嚴格訓練,如今頓失人生目標的維溫娜,則決定偷偷潛入哈蘭隼,伺機攪亂敵人並救出妹妹……
戰爭在即,擁有最大駐氣數量,高深莫測的神君修茲波朗、據稱因英勇死去而得以重返人世的復歸神萊聲,加上來歷成謎、能力強大的神祕破戰者法榭,成為開戰與否的關鍵。不管是人是神,此間所有的挑戰都代表他們各自所面對的不同考驗……他們將如何突破各自的困境?
繼出道作《伊嵐翠》和其後的轟動鉅作《迷霧之子》三部曲之後,布蘭登.山德森再創獨立鉅作,以細膩幽默的人物群相和穿插其中的曲折謀略,搭配縝密而周全的魔法及宗教系統,逐步揭開死後生命的奧祕,探討認知與命運、人性與政治,再次架構出一個驚奇非凡的世界。
.美國圖書館期刊09年最佳科奇幻小說
.美國B&N書店09年最佳科奇幻小說
.美國圖書館協會(ALA)09年最佳奇幻小說
.美國紐約時報暢銷榜
導讀:布蘭登.山德森——當今奇幻界的說故事天才
一口氣看完《破戰者》之後,我再次確認了一件事:布蘭登.山德森真是位可怕的變態魔人。
《破戰者》是一部獨立、完整的故事,背景設定與山德森之前的作品都無關。
在《破戰者》的世界中,每個人的體內都有一道生體彩息(又被稱為「駐氣」),失去駐氣雖然不會喪命,卻會變成褪色人,變得比常人麻木、遲鈍。在自願的情況下,人們可以把自己的駐氣獻給他人,得到多餘駐氣的人可以利用這些駐氣行使識喚術,藉由命令語並吞噬一定量的色彩,可以將駐氣注入物體甚至屍體之中加以操控。
作為故事主要舞台的哈蘭隼以染料聞名,是一個充滿了各種鮮艷色彩的國度。
自從皇室成員在「眾國大戰」之後流亡高原,國家便分裂成哈蘭隼與義卓司兩個國家。哈蘭隼的人民在神君的統治下拋棄了原本的奧斯太神信仰,轉而崇拜虹譜。死而復生的復歸者在這裡被視為神明,不僅享盡榮華富貴,還能夠定期從信徒身上取得生體彩息以維持生命。
與之相反,由流亡皇室建立的義卓司王國仍信仰著奧斯太神,並且把取得他人駐氣視為禁忌。為了防止識喚術的使用,義卓司人盡可能地辟除色彩,衣服不是灰色便是暗土色。無論如何,與擁有四萬名死魂兵的哈蘭隼相比,義卓司明顯地小國寡民,為了維護和平,國王多年前曾答應將公主嫁與哈蘭隼的神君。就在約定的期限到來時,兩國的關係卻惡化到瀕臨戰爭的邊緣……
《破戰者》的故事便是在這樣的狀況下,透過四位主角的視角進行開展。
法榭是一位來歷成謎、能力強大的識喚術士。他擁有一把喚作宵血的可怕魔劍,基於某種外人所不知的理由,他在哈蘭隼城內四處活動,一路留下眾多的屍體。
希麗是義卓司國王最小的小女兒,雖是皇室公主,卻沒有什麼職責壓力,自小活便潑慣了。在戰爭的威脅之下,希麗的命運突然一夕改變,取代了她一向尊敬的大姐維溫娜,被父王送往哈蘭隼,嫁給了哈蘭隼的神君為妻。
維溫娜是義卓司國王的長女,為了她與神君之間的婚約,維溫娜自小便接受嚴格的訓練,想不到父王卻在最後關頭將婚事改派給了希麗。眼看兩國可能發生戰事,失去人生目標的維溫娜決定潛入哈蘭隼城,準備在危急時救出希麗。
萊聲是哈蘭隼二十幾位復歸神當中的一員。表面上雖然一副吊兒郎當的輕鬆模樣,但與其他沉溺享樂的神相比,萊聲的內心其實充滿了矛盾與無奈。沒有任何生前記憶的他既不覺得自己具有神的資格,但也沒有自我犧牲的意願。萊聲對政治一向沒有興趣,但身為英勇之神,他卻掌握著一萬名死魂兵的指揮權。
由於故事幾乎都在哈蘭隼的首府特提勒城中發生,《破戰者》的格局不如大長篇的「迷霧之子」三部曲或「王者之路」系列巨大,但讓山德森之所以是山德森的要素,在《破戰者》裡可以說一樣不缺:具有強烈特色的世界觀與魔法設定、讓人一翻開書便欲罷不能的說故事功力、頗具魅力的角色(包括側寫的非視角人物)、還有「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最後真相。
打從《魔戒》的托爾金開始,史詩奇幻的創作者多少都有些設定狂的傾向,從上溯神話時代的歷史年表到整個世界的地理疆界,從令人目眩的魔法系統到繁瑣的貨幣購買力,更別提種族、語言、曆法、飲食……幾乎無所不包。然而有好設定並不等於有好作品,要成為一個好作家,需要能夠克制住內心的解說欲望,不露斧鑿之痕地把設定融入小說人物的活動之中,才不致於喧賓奪主。
在這方面,布蘭登.山德森絕對是當今奇幻界的一把好手。他不僅擅於利用設定來豐富他筆下的世界,更懂得把關鍵的部份留作伏筆,還狡猾地隱藏在我們的眼皮底下,每每要等到書中角色與我們一起摔個四腳朝天,才終於恍然大悟。
讓我更感敬畏的是,山德森在完成《諸神之城:伊嵐翠》這樣一部大受好評的出道作之後,不像其他人那樣接著寫續集、前傳,或是沿用伊嵐翠已經建構的背景設定,在留白與意猶未盡處構思新的作品……沒有,山德森居然就這樣放開了伊嵐翠人,毫不眷戀地另起爐灶,寫出了一個空中不斷落下灰燼、夜間瀰漫著可怕迷霧的迷人世界——「迷霧之子」三部曲!
當最後帝國的真相都揭露之後,山德森又把鎔金術、藏金術與血金術暫時拋開(後來有再續寫了一部番外篇《執法鎔金》),再一次開了新坑:《破戰者》。作為故事主要舞台的哈蘭隼是一個充滿了鮮艷色彩的國度。在市井之中,識喚術士憑藉著從他人處取得的駐氣,一面吞噬周圍的色彩,一面以命令語施展奇蹟。在廟堂之上,死而復生的復歸者被視為神明,享盡榮華富貴之餘,還靠著人民奉獻的生體彩息延續生命……
在代筆續寫了《時光之輪╱光之回憶1:風起雲湧》之後,山德森推出的是《颶光典籍首部曲:王者之路》,果然,這個變態又把《破戰者》的識喚術與生體彩息推開,寫出一個颳著可怕颶風、末日即將(或已經)到來的世界……
如果僅僅是喜歡開新坑,那也還沒有什麼,可山德森最可怕、最變態的地方,在於他填坑的速度之快,並不比開坑的速度慢多少。從《伊嵐翠》問市以來,山德森幾乎以一年一部的速度推出厚如磚頭的新作。在這當中,《伊嵐翠》與《破戰者》雖然都具有發展成一整個系列的潛力,但就作品本身來看,已經是完整的結束了。「迷霧之子」固然有番外篇及後續的寫作計劃,「三部曲」本身的完成度卻是無可挑剔的……
身為奇幻小說的愛好者,我衷心感謝老天給了咱們這麼一位變態魔人。
文╱王經意
本文作者為第四屆倪匡科幻獎並列首獎、第五屆溫世仁武俠獎短篇組首獎得主
書摘:◆序章◆
真好笑,法榭心想,我被丟進牢裡來,竟然也可以搞出這麼多事。
獄卒們相視而笑,重重地關上牢房的門,架上鐵閂。法榭站著拍去身上的灰塵,轉轉肩頸骨,讓全身舒鬆一下。牢房門的下半部是厚實木板,上半部是柵欄,所以他能看見那三個獄卒拿了他的粗呢大布袋,正開始翻看裡面的東西。
有個獄卒發現法榭正在看。那人是個光頭大隻佬,制服髒得不像樣,只能勉強看到一點亮黃藍相間的顏色,也就是特提勒城衛警的標誌配色。
鮮艷色系,法榭想,我得重新適應這裡的調調。換作別的國家,讓士兵穿這種配色的衣服會給人笑死。不過,這兒是哈蘭隼,是復歸神、死魂僕和生體色度研究的重鎮——當然,也是「色彩」的國度。
大塊頭獄卒懶懶地走向法榭的牢房,在他身後,他的同僚們正在拿呢布袋裡的東西笑鬧把玩。「聽說你很凶悍嘛。」那人說道,一面打量著法榭。
法榭沒應聲。
「酒保說你在亂鬥中撂倒了二十幾個人。」那獄卒撫著下巴。「我倒不覺得你有那麼厲害。不管怎麼說,你都不該去打那個祭司。別人犯這條罪,大概關一個晚上,但你這沒色彩的蠢貨嘛……會被吊死。」
法榭轉過身去。這間牢房有全套標準配備,包括滲水、長青苔的石牆,牆高處一道用來透光的小小細縫,角落有一堆腐爛的髒稻草。
「不理我?」獄卒說道,又向房門走近兩步。這時,他身上的制服顏色隱約變亮了一些,就像從暗處走進亮處那樣,只是那光源十分微弱。法榭所剩的駐氣不多,所以他自己的光氛沒有為周遭的物體增色,獄卒也就沒注意到自己身上起了變化——一如在酒吧裡他和弟兄們把法榭從地上拎起來往囚車裡扔的時候。當然,這變化極細微,除非有法術輔助,尋常人是絕對無法察覺的。
「喂,看這裡。」翻看呢布袋的其中一名獄卒喊道。「這是啥?」
法榭發現一個有趣的定律,那就是守牢房的人好像都不是什麼好東西,甚至往往比關在牢房內的囚徒還要差勁。也許上頭是故意這麼安排的。如此安置這種人,其實也跟安置囚徒差不多,還可以讓他們離真正老實善良的百姓們遠一點。
可笑的是,原來這種事真的存在。
獄卒從法榭的布袋裡掏出一支裹著白色亞麻布的長形物體。那人把布解開時吹了一聲口哨,因為裡頭是一把收在銀劍鞘裡的薄刃劍,劍柄漆黑。「你想他是從哪兒偷來的?」
來挑釁的那名獄卒朝法榭瞄了幾眼,可能在懷疑法榭是哪來的貴族。哈蘭隼沒有這種階級,鄰近的王國倒有,可是哪國的貴族會披這種又髒又破洞的土色斗篷跑來跑去?貴族豈會掛著一臉鬍碴、踩一雙舊得肯定飽經風霜的靴子,然後在酒吧裡跟人打得鼻青臉腫?獄卒轉身走開,顯然認定法榭不是貴族。
他是對的,但他也搞錯了。
「給我看看。」那人走回去道。他從同僚手中接過長劍,哼了兩聲,對它的重量感到訝異,又把劍翻過來看,發現劍鞘跟劍身是用鉤子扣在一起的,於是他脫開了鉤子。
室內的色彩變濃了,不是更加鮮明——不像獄卒接近法榭時那樣,而是變得強烈而飽滿。紅色系的物體轉成了酒紅色,黃色的散發出沉金光,而藍色的則趨近於藏青。
「老兄,小心點,」法榭慢條斯理地說,「那把劍很危險的。」
獄卒瞄了他一眼。這時,全場都靜了下來。但見那獄卒只是冷哼一聲,帶著劍自顧走出牢房,兩個同僚也跟著走了出去,同時把法榭的布袋一併帶走,進了長廊盡頭的守衛室。
守衛室的門重重關上。法榭立刻在那堆稻草旁蹲下,挑選較硬的草莖揀出一把,然後從綻了線的斗篷邊緣抽出一條線,將草莖紮成一只約三吋高、手腳粗壯的小人偶。接著,他拔了一根眉毛,插進稻草人的頭,再從靴子裡抽出一條紅色領巾。
然後他運氣調息。
一泓明亮透明的氣息立即從他身上溢散開來,迅速逸進空氣裡,有點兒像油浮在水面受陽光映顯出的色彩。法榭感覺到它的脫離:生體彩息,學者們是這麼稱呼的。大多數人只簡單稱之為駐氣。通常人人都有一道,或至少一道;一個人,一道氣。
法榭擁有的駐氣約有五十道,剛好夠達到第一級的彩息增化。想起自己曾經擁有的駐氣數量,現在的法榭覺得自己好落魄,但對大多數人而言,五十道已經很不得了了。更不幸的是,此刻就為了識喚一只以有機物質製成的小人偶——藉由取自他身上的一點點物質來作為辨識——都要消耗掉他將近一半的駐氣。
小小的稻草人扭了一下,將彩息吸了進去,而法榭手中的鮮紅色領巾,其半邊也在同時褪成了灰色。法榭傾身向前,一面在腦中揣摩著他要這人偶去做的事,一面說出命令語,完成這項法術的最後一個步驟。
「拿鑰匙來。」他說。
小草人站得定定的,對著他揚起一邊的眉毛。
法榭伸手指向守衛室。這時,他聽見守衛室爆出一陣驚恐的吼叫聲。
時間不多了。他想。
小草人向外跑,蹦地跳出柵欄。法榭脫掉身上的斗篷,放在地上;這斗篷恰恰是個完美的人型——上頭的幾道裂口,正與法榭身上的傷疤吻合,而用來蓋住頭部的帽兜上,也有兩個與眼睛相齊的洞。施術目標物的外形越像人,識喚時所需的駐氣就越少。
法榭彎下身子,盡量不去想自己當年擁有的駐氣數量曾經多到毋須在意受術物的形狀和辨識性。那都是從前了。咬咬牙,他從頭上扯下一撮頭髮,撒在斗篷的帽兜上。
然後重新運息。
他把剩下的駐氣用完。當彩息脫離——地上的斗篷微顫,他手中的紅領巾也完全失去色彩時——法榭感覺……有點兒虛。失去駐氣不會致死,甚至法榭之前擁有的大量駐氣原本也是屬於別人的,只是他從來不知道那些人是誰,因為那些駐氣不是他自己去收集而來,而是被賦予到他身上的。當然,駐氣不能用強奪來獲取,這是世間向來運作的道理。
如今他身上一道駐氣也沒有,這一點的確造成影響。從他的眼中看出去,周遭的色彩不再那麼鮮明,他也感覺不到人們在這城中熙來攘往的動靜了;在平常,這感應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連繫,存在得天經地義——也正是它會悄悄發出警告,讓人即使在房間裡小睡時也能察覺外人的潛入。特別是在法榭身上,當類似狀況發生時,他感應到的強度會是一般人的五十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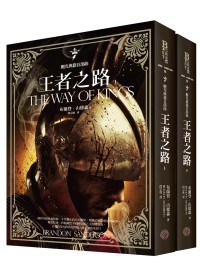
如今所有的駐氣都逸脫,注入斗篷和稻草人之中,賦予它們力量。
法榭低著頭向斗篷發令:「保護我。」便見斗篷靜止下來,於是他站直身子,重新將它披上。小草人回來了,帶著一大串鑰匙。人偶的雙腳泛著紅色。看在法榭的眼裡,那紅色暗澹得灰撲撲。
他拿起鑰匙,向草偶道了聲謝。他總是向它們道謝,自己也不明白為何這麼做,特別是想到他接下來要做的事。「你的駐氣為我所有。」他發令道,同時觸碰小草人的胸,小草人立刻仰倒在地,生命被汲走了;法榭也取回他的駐氣。
熟悉的感應度,以及對於連繫及存在的那種覺察力這才回來。他能取回駐氣,是因為這術偶是他親自識喚的。其實,識喚這一類的術偶,效力幾乎都不持久,所以他總是如此收收放放,就像有借有還。
和以前的數量相比,二十五道駐氣簡直少得可笑,但跟一無所有相比,又彷彿多得無所不能了。察覺心底的這一絲滿足,法榭打了個哆嗦。
守衛室傳來的嚎叫聲漸弱。牢房靜了下來。他得繼續行動。
法榭把手伸出柵欄外,用鑰匙開了門鎖。他留下那只草偶,推開厚重的門,飛快地奔進走廊,卻沒往連接出口的守衛室,而是朝南面的通道轉去,深入這座監獄的中心。
這是整個計畫中最不確定的部分。找一間虹譜祭司常去的酒館還容易些;打架滋事,再從那些看起來都一樣的祭司裡挑個倒楣的來痛毆,也同樣簡單。哈蘭隼的神職人員擁有崇高地位,因此法榭此舉掙來的可不只是普通的牢獄之災,而是一趟神君大牢之旅。
深知看守這種監獄的人會是什麼角色,法榭早料到他們會對他的劍——宵血有興趣。這倒讓他有機會拿到這串鑰匙。不過,接下來就得要見機行事了。
法榭停下腳步,身上的斗篷沙沙作響。他要找的牢房很容易辨認,因為那附近必定有大片失色的痕跡,就連牆壁、石地或門板都不例外——用來關識喚術士的地方就是這個樣子,好讓囚犯沒有顏色可以使用。法榭走到門邊,從柵欄之間探看,見到一個赤裸的男人被吊在天花板下,鎖鍊銬著他的雙臂。在法榭的眼中,那人的顏色極其鮮亮,皮膚是純正深棕色,斑斑瘀傷都散發著紫青的光輝。
男子的嘴是堵住的,這是另一重防範措施。識喚術的施展有三個要素:駐氣、顏色,以及命令語,也有人統稱為色相諧度。虹譜是一種顏色與聲音之間的關係。識喚術的命令語必須以術士本身的母語說出,發音要清楚且確實,不能有任何的結巴、含糊或口誤,否則就會導致法術失敗。一旦施術失敗,駐氣照樣逸脫,但術偶不會依令行動。
法榭用那串鑰匙打開牢房的門,走了進去。當他接近那男子時,男子的光氛令法榭身上的色彩驟然鮮艷起來。任何人都能看出這個犯人的光氛有多麼強,已達彩息增化第一級的人更能輕易判別。

法榭見過比這更強的生體光氛——來自於復歸者。在哈蘭隼,復歸者被視為神,而眼前這個囚犯的生體色度雖然不及他們,但仍可說是高得驚人,遠比法榭自身的還要強烈許多。不僅如此,此人也擁有大量駐氣,甚至可以千百計。
囚犯晃了一下,朝法榭打量,受箝堵的嘴唇因乾裂而淌血。法榭只遲疑了一會兒,便伸手替那人取下口銜。
「你……」囚犯輕聲說時,咳了幾聲。「你是來放我走的?」
「不,瓦爾,」法榭平靜地說,「我是來殺你的。」
瓦爾哼笑。他的囚禁生涯顯然不輕鬆。法榭最後一次見到瓦爾時,他還是個體型微胖的漢子,如今卻是瘦骨嶙峋,應該有好一陣子沒吃東西了;而那些刀傷、瘀青和燙傷的痕跡,看起來都是新近烙下的。
瓦爾的雙眼都被打得發黑腫脹,更顯得憔悴。如此慘痛的刑求痕跡更加突顯一個事實,那就是駐氣只能在持有者的自由意志及發令之下才可轉移;當然,意志是可以被煽動的。
「所以,」瓦爾的聲音低沉沙啞,「你也定我的罪,就像別人一樣。」
「你那失敗的叛變不關我的事,我只要你的駐氣。」
「哼,你跟那整個哈蘭隼宮廷都不是好東西。」
「對。不過,你不能把駐氣轉移給復歸者,而是要給我。這是殺你的交換條件。」
「什麼爛交易。」瓦爾說時,語氣裡只有嚴峻,不帶任何感情。幾年前,當他們分道揚鑣時,瓦爾不會這樣說話。
真奇怪,法榭心想,經過這麼多年,我竟然終於在這人身上找到了認同感。
法榭謹慎地與瓦爾保持著距離。如今瓦爾已能發出聲音,也就能夠發令,只是他現在碰不到任何東西,僅有鐵鍊鎖著他的手臂——金屬是很難識喚的,它們不曾有過生命,而且鎖鍊的外形與人型相差甚遠。縱使在駐氣最多的極盛時期,法榭自己也只在極難得的少數情況下成功地識喚過金屬。當然,某些非常強大的術士可以隔空用聲音識喚物體,但那可得到達第九級的彩息增化才能辦到,而法榭從未擁有過那麼多的駐氣。事實上,當今世上他只知道唯有一人能辦得到,就是神君。
基於以上條件,此刻的法榭還算安全,因為瓦爾徒有大量駐氣卻沒有可供識喚的物體。法榭繞著他走了兩圈,倒不覺得自己應該同情這人。瓦爾罪有應得,祭司們留他活口只是為了他所擁有的駐氣;他若是死了,駐氣只會白白逸脫,不可能追得回來。
哈蘭隼官方也不會允許這事發生。哈蘭隼訂有極嚴格的法律,規範駐氣的交易和轉移,因此官方迫切想要瓦爾的駐氣,甚至不惜擱置這位頭號要犯的處刑。要是他們知道大牢裡發生的這一切,大概會氣得半死,懊惱為何沒布下更嚴密的警衛。
對法榭而言,這可是他等了兩年的大好機會。
「怎樣?」瓦爾問。
「把駐氣給我,瓦爾。」法榭說道,向前走了一步。
瓦爾冷哼:「我倒懷疑你的刑求本領有沒有像神君那樣高竿呢,法榭。我都熬過兩個禮拜了。」
「保證教你大開眼界。不過那不重要,你的駐氣一定要移交給我。你很清楚,你只有兩個選擇:交給我,或是交給他們。」
瓦爾沒搭腔,吊在那兒慢慢轉了一小圈。
「沒時間讓你多想。」法榭又道,「隨時有人會發現守衛死在外頭。等到警報響起,我逃我的,你就留在這兒繼續受罪,而且遲早會屈服。到那時候,你收集到的力量都會被你誓言摧毀的人據為己有。」
瓦爾看著地板。法榭沒再催他,知道情勢瞭然,瓦爾別無選擇。

終於,瓦爾抬起頭,看著法榭:「那玩意兒……由你保管的。在嗎?在這城裡?」
法榭點頭。
「我剛才聽到的那陣叫聲就是它造成的?」
法榭又點頭。
「你會在特提勒待多久?」
「一陣子,搞不好一年。」
「你會用它來對付他們嗎?」
「我的目標從沒變過,瓦爾。你到底要不要接受我開的條件?用你的駐氣換一個俐落好死,這一點我能保證。你的敵人絕對得不到它們。」
瓦爾沉默良久。最後,他開口了。
「那就給你。」
法榭伸長手臂,把一隻手放在瓦爾的肩膀上,同時小心地不讓衣物觸碰到瓦爾的身體,免得他用上頭的色彩來施展識喚術。
瓦爾動也不動,好像在發呆。就在法榭猜想他是不是改變了心意時,瓦爾運起氣來。他的身體散放出色彩,周遭光氛也顯現出美麗的彩虹色調,驀地令這名傷痕累累的囚犯呈現出恢宏尊貴的氣勢。接著,色暈從他的嘴巴逸出,飄進空中,像一片閃爍著光芒的霧。法榭深吸一口,閉上眼睛。
「我的生命為你所有,」瓦爾發令,語調中似有一絲絕望。「我的駐氣歸你所有。」
大量的駐氣湧進法榭體內,周遭景物立刻鮮明起來:斗篷的褐色看起來既濃郁又飽和,地上的血跡紅得發亮,彷彿烈焰一般;就連瓦爾的皮膚都像是調色大師的傑作,妝點著毛髮的深黑、瘀傷的紫青、刀傷的銳紅。法榭已經有好多年沒感覺到如此活力,充滿生機。
在力量震懾之下,法榭喘著氣,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甚至得用一隻手支著地板才能免於仆倒,同時在心中想道:這幾年來,少了它們,我到底是怎麼活的?
他知道自己的感官還沒有隨之提升,卻開始覺得感應度更加靈敏,感受力也大大增強。當他觸碰石板地,地板的硬度令他感到驚奇;聽見風從窗縫吹進,那聲音竟有如旋律。風聲一向都是這麼悅耳的嗎?差異真有這麼大?
「你可要說話算話。」瓦爾說道。法榭聽著瓦爾的聲音,只覺得每個音節都變得格外動聽,近似諧韻。現在的他已能掌握精確音準,這是達到第二級彩息增化之後的附加能力。能夠重新擁有這項能力,真是太棒了。
當然,如果法榭想要,原本也可以隨時使自己提升到彩息增化的第五級,只是那得做出某些犧牲,而那是他不願意的,所以他只能用老方法,藉由像瓦爾這樣的人來獲取駐氣。
法榭站直,取下剛才用過的那條褪色領巾,拋過瓦爾的肩膀,然後運息。
毋須將領巾束成人型,也不必再擷取自己的身體髮膚以為辨識。不過,他仍得從自己的衣衫來汲取顏色。
對上瓦爾認命的眼神,法榭用手指觸碰領巾,說出了命令語。
「勒緊。」
微顫的領巾立刻扭結起來,同時汲走大量駐氣——所謂大量,如今也算不上什麼就是了。只見它迅速繞過瓦爾的頸子,束緊,令他窒息。瓦爾沒有掙扎,也沒有喘氣,只是用滿懷恨意的眼神看著法榭,直到他的雙眼暴突,氣絕身亡。
恨意。法榭當年見得多了。他靜靜地從領巾取回駐氣,留下瓦爾的屍首吊在原地,默默走出牢房,一路適應著木門和石板地的色調,不一會兒便在走道上看見一個新的顏色:血紅。
繞過那灘血,法榭走進守衛室。監獄的地面不平,血還在往低處漫流。那三名守衛早已斷氣,其中一個坐在椅子上,胸前橫過一道血痕。宵血的劍身大半入鞘,僅有約一吋的黑色劍刃露在銀色劍鞘外。
法榭小心地將它完全收進劍鞘,扣上鉤子。
我今天表現得很好——有個聲音在他的腦中說道。
法榭沒有回應它。
我把他們全殺了——宵血繼續說——你怎麼不為我感到驕傲?
法榭執起長劍,重新掂了掂那不尋常的重量,然後一手握著它,另一手抓起他的粗呢布袋,掛在肩上。
我就知道你會覺得我很厲害—— 宵血又說,語氣很是滿足。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