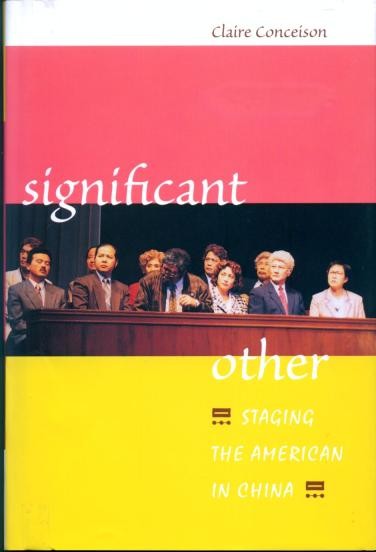
Claire Conceison. Significant Other: Staging the American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這本書探討在1987年至2002年期間,當代中國劇本中與舞台上的美國人形象,以及這些形象對種族與文化的刻板印象、政治策略、以及藝術創新如何發揮其影響力。作者Claire Conceison是位中國研究學者,同時也是劇場實踐工作者,她在北京及上海兩地做了大量的田野調查、資料蒐集,對當代中國戲劇文本進行細讀,同時更兼顧到演出文本、創作意圖、藝術整合與觀眾反應,進而對當代中國大陸的「話劇」提出做為一位西方學者的獨特觀點。
Conceison將美國定位為中國的「意味深長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簡介了中國與美國之間複雜的文化關係,並將其置放到長期以來的中美關係與後殖民論述之中,拓展進一步的批判思維。緊接著,她檢視「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論述,追索它的根源與其流佈的情形,並將它重新定位為剖析中國戲劇舞台上的美國(人)形象的論述策略。她堅信中國戲劇舞台上的美國(人)形象(通常都是由中國當地的演員經過妝扮來演出美國人角色,最近則越來越傾向外國人演他們自己)某種程度上揭露了中國看待美國的文化規範及文化態度,也指涉了中美兩國的政治關係,並且標舉了中國的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同時也象徵「話劇」的創新也是一種藝術形式。
以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與表演研究學為論述基礎的Significant Other: Staging the American in China一書當中,不僅論述了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的誤解與對話,探討的主題也包括了移民、流亡、離鄉背井、文化衝突、文化交流主義、反美主義、自我再現等,它更直接審慎地調查了那些將美國(人)形象搬上舞台的當代中國劇場藝術家們的創作過程。
除了謝辭、前言、後記、註解、書目、索引、黑白劇照之外,該書主體正文共分為八章,首章在重建中美關係的歷史、政治與文化舞台,第二章是西方主義的(再)斟酌;第三章至第八章,從分別從移民的文化交流主義、離鄉背井的荒謬、文化跨越的審問、美國的自我再現、反美主義、自我西方主義等六個角度,批判性地細讀了七個戲的劇本與舞台演出文本,包括《中國夢》(孫惠柱、費春放合編)、《大留洋》(王培公)、《鳥人》(過士行)、《陪讀夫人》(俞洛生根據王周生同名小說改編)、《尊嚴》(沙葉新)、《切‧革瓦拉》(黃紀蘇)和《鞦韆情人》(孫惠柱、費春放合編)。
東方主義的傳統相當悠久,而這的概念對Edward Said來說,主要是基於歐洲人的西方經驗中,東方的特殊位置而來的,因為對歐洲來說,東方具有多重文化功能與象徵,她既是歐洲最大、最富足且最古老的殖民地,又是歐洲文明和語言的來源,但同時卻也是文化競爭上的他者或異己,這一切針對東方的想像與界定,幾乎全是歐洲自我文化定位的心態在作祟,是歐洲物質文明和文化整合過程的一個重要部分,最重要的,這是一種由制度、字彙、學術、想像和教義,甚至是殖民行政官僚與文化風格所支持的一種論述模式。
Said也在他的學術奠基之作《東方主義》結論中提醒讀者「東方主義的解答並非西方主義」,就是「西方主義」這個最終警告,似乎只是點到為止,但事實上這個概念也已經在悄悄地在興起之中;對Conceison來說,她最介意的是,「西方主義」的詞義、語源、發展等都並未經過任何實際的討論,就已經被學界一廂情願地使用,且急於套用在他者再現的形象研究之中;她以遊走於中國與美國兩個文化實體之間的親身體驗,結合她在劇場實務工作的專業背景,對「西方主義」提出她再三斟酌的實證意義。對此,Conceison非常同意學者David Arkush關於「西方主義」的看法,他認為這個術語需要謹慎且可靠的定義,做為後東方主義話語一個有效的參與者。
關於Conceison如何修正東方主義與如何處理西方主義,其方法論幾乎都在第二章「西方主義的(再)斟酌」當中。她同意阿拉伯學者Sadik Jalal al-‘Azm對於《東方主義》的批判觀點,他們都認為Said的批評方法論只是不斷加強東方與西方的二元差異與對立,想要追溯東方主義的根源,卻在這過程中不斷地合法化;al-‘Azm還指出Said的另外一個悖論,Said既然知道沒有分類、簡化或變形是不可能再現「真實」的,因為所有的再現實際上都是失之偏頗的,那麼西方所做的也不過只是完全自然的行為罷了;真正有趣的問題應該是,如何達到文化再現中的他者形象分析。Conceison也同意另一位美國白人漢學家J. Timothy Wixted的看法,Wixted認為所有的東方學者似乎都是要將西方的學者和學術語言灌注到他們的文化當中,使東方可以被視為一種論述的客體,將東方對象化;Wixted在他的演講〈翻轉東方主義〉(Reverse Orientalism)中,花了許多力氣描述東方的中國和日本對於西學多半抱以否認與不信的態度,日本自戀地只對西方人如何看待他們有興趣,中國則是根本不予理會。
若干學者則提出東西文化雜匯的看法,像對西方主義採以否定態度的Frank Dikötter便指出1915到1949年間的中西文化關係,主要有三種:兩極對立(polarization)、投射(projection)、碎裂吸收(fragmental assimilation),經過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那個時期的西方成為現代中國國家認同組成很重要的成分,西方甚至成為中國的另類自我。相較而言,Xiaomei Chen對西方主義採以肯定的態度,這包括了將西方本質化與西方文化模式的制宜採納;Conceison則堅信中國的西方主義,有很大比例是出於維護總體的合法性與國家認同的需要,她是同意Xiaomei Chen的觀點的,但是她會針對Chen的學術力作《西方主義:後毛時期中國的反話語理論》(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做許多修正與補充,像是Chen在其論著當中並未論及劇本的舞台表現、中國搬演外國劇本只是為了主題意識上的政治目的、沒有再現異邦他者的本地劇作等缺漏。Conceison強調,她的研究興趣會聚焦在挖掘覆蓋在中國戲劇裡異邦(尤其是美國)他者的形象,以及這些形象的再現方式。
接著,Conceison還從人類學界尋找西方主義的同路人。第一位是James Carrier,他開始提醒「西方人自己再現西方」是有問題的,他認真思考由非西方來製造西方形象,其實並非是他者或仇外的,反倒會是自我的,這點和Said所謂的自我東方化並不相同,倒是和Chen的東西文化交融觀點比較接近,而Conceison所要著重的也就是西方他者自我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the Western Other themselves),以及實踐西方主義的構成元素,她揣度倘若東方主義是藉由相對的他者所組成的「東方」而形構的,那麼西方主義可否不要只是反向操作,也就是說,不要藉由相對的他者所組成的「西方」而形構了西方主義?她在這裡真正要強調的是,東方主義中「說話的主體」(speaking subject)和「他者化的客體」(othered object)的關聯性。
學/讀,然後知不足。是我看這本書最常想到的事情,這些年雖然也參與許多戲劇的教學、研討與評論的工作,但總覺得歷史、理論與實用之間,自己的貫穿能力還不足,細讀的功夫也不夠。從今年寒假以來,就一直斷斷續續讀著這本書,也盡量配合著書中所討論到的劇本來讀,尤其是對第三章至第八章,作者對於每一個作品重構與細讀的功夫,不單是令人值得欽佩與學習,其文字也優美流暢易讀,兼具理性與感性的論述能力。
拿第三章「移民的文化交流主義:《中國夢》」來說,一開始就介紹兩位中國當代的學者型劇作家孫惠柱與夫人費春放,提到他們在美國的留學、研究、教學與婚姻生活,藉此替文後即將進行的對照閱讀(指他們的美國生活與劇本內容若合符節,相互參照)做好前置作業;另外,也在該章開頭的第三段就引出黃佐臨、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布雷希特、梅蘭芳等劇場藝術家們的表演美學觀,為文後的討論埋下伏筆。等一切引頭都就緒之後,Conceison便大致依照劇本創作背景、劇情大綱、人物性格分析、舞台美術表現、觀眾與評論迴響等順序,將《中國夢》這齣戲當年的演出環境與討論的氛圍重構,並引出黃佐臨這位海派話劇導演(相對於北京人藝導演的焦菊隱)的「寫意戲劇觀」,以及他所倡議的「劇場藝術三角體系」: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體系、布雷希特的敘事劇理論、梅蘭芳的京劇寫意表演美學。文章的後半部至少保留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詳細討論《中國夢》這齣戲中,關於移民、文化交流主義、文化認同、東方主義、西方主義等理論議題,將作品、表演、理論、歷史等交錯複雜的關係梳理清楚。每讀完她所寫的一章個案研究(唯獨第六章,一次討論《尊嚴》與《切‧革瓦拉》兩個作品),就深覺腦袋清新,心裡舒暢,有一種閱讀的愉悅。
這種演出文本的重構寫作,講求的就是資料的掌握,可以看得出來,Conceison不僅懂中文,而且中、英文相關資料也鉅細靡遺地蒐集,最重要的是她與中國當代劇場許多院團及實踐藝術家、戲劇學者們都多有熟稔,同時也對西方劇場與文藝批評理論能夠掌握,案頭研究與田野調查並重,以致於寫出來的東西特別有「人」味。
不過也有學者對這本書提出不同角度的批判,如吳戈的《中美戲劇交流的文化解讀》對本書就有不少批評,比如:
她對種族問題十分敏感,對自己剛到中國時被好奇地圍觀充滿了痛苦和屈辱,在她「種族主義」的理解中,中國人的圍觀、盯著看不是因為好奇,而是看「他者」;她對舞台上扮演美國人的特型化妝表示了不滿和不屑,因為在她看來那是「他者」標誌甚至是醜化;她對意識形態問題轉化為文化表述的可能也格外自覺,站在美國政府意識形態保衛者、國家形象守護者的立場上,而不是以一個戲劇研究者、甚至也不是站在一個純粹文化學學者的立場上來描述當代中國戲劇。(頁200)
或者是:
預設一個「解構東方學、東方主義」的前提,把「西方主義的想像者」強加給中國戲劇,也來虛構一個東方也在想像西方,也有一個潛在的「西方學」,這就陷入了一個文化無法交流的「影射遊戲」或「隱喻儀式」的泥沼,分析戲劇演出文本難免牽強,力圖自圓其說時卻難免顧此失彼。關鍵是,在這樣的研究前提和視野下,中美戲劇交流,就絕少建設意義了。何況生活本身和戲劇發展的真實過程也不是這樣。(頁201)
由於兩人的文化背景、論述脈絡、研究方法、實際體驗、思維邏輯等都有許多主、客觀上的差異,會出現如此巨大的認知落差,也不足為奇了。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