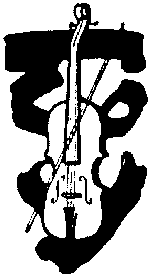
一個國家掙脫外來政權的魔掌之後,又能如何?
缺乏深度文明與文化的國家,脫離殖民帝國獨立之後,命運將會是如何?
後殖民時代,許多國家紛紛發展出帶有濃厚民族主義色彩的“本土化”運動,這些運動的成效如何?影響如何?
“民族自覺”的目的,是否能藉由“本土化”這樣的方式來達成?
思考上述這些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先來看看以下的範例。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因卡與“黑人特色”運動 】
“黑人特色”﹙Negritude﹚一詞﹐幾乎已經成為黑人世界與西方白人世界對抗的代名詞。它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聚集巴黎的黑人知識分子發起的一場意識形態運動。當時﹐西方殖民在全世界面臨退守之勢﹐接著是二戰烽煙四起﹑納粹種族清洗日益殘酷。與此同時﹐“黑人特色”運動不但深入非洲﹐而且影響了世界各地的黑人群體﹐引導他們拒絕西方的政治﹑社會和道德支配地位。
“黑人特色”的主要主張﹐簡言之大約有下述三個方面﹕
第一﹐必須抵制西方殖民主義和西化教育的日益滲透﹔
第二﹐黑人應當堅持自身的價值觀﹐讓非洲本土和散居世界各地的黑人抱成一團﹐形成對黑人種族的全方位認同﹔
第三﹐必須弘揚具有獨立意義不容同化的非洲傳統文化。
在這樣的理論主張下﹐“黑人特色”文學流派以熱情的筆調贊揚黑人種族。他們“為美麗的黑皮膚感到自豪”。這一運動的主要倡導者﹐是西印度群島詩人塞賽列﹙Aim Claire﹚和塞內加爾在法國軍隊服役的青年詩人森霍﹙L‧S‧Senghor﹐此人後來成為塞內加爾第一任總統﹚。前者有“黑人特色之父”之稱﹐最早以長詩《回故鄉》﹙1939﹚呼喚黑人種族意識的蘇醒﹔後者以詩歌進一步界定黑人特色﹐認為非洲文化的永恆價值觀在於其情感特徵﹑宗教精神和社群凝聚力﹐與西方的理性傳統﹑懷疑主義和個人主義形成對比和沖突。森霍相信傳統非洲價值觀的表達﹐但他並不希望恢複那些過時了的風俗﹐而僅僅力求恢複原初的黑人精神。他的觀點大受黑人作家的歡迎。
六十年代﹐當大多數非洲殖民地贏得民族獨立時﹐“黑人特色”運動遭到不少黑人作家的批評﹐其中持否定態度最強有力的﹐是著名黑人作家和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沃爾·索因卡﹙WOLE SOYINKA﹚。
【反種族主義的種族主義】
索因卡對“黑人特色”運動的深入思考﹐是六十年代末在他目擊了尼日利亞內戰之後。1966年9月﹐尼日利亞北部占多數的豪薩人屠殺了近三萬屬於少數民族的伊博人﹐一百多萬伊博人逃往東部成立獨立的比夫拉共和國﹐尼日利亞軍政府主席戈翁﹐在英國和蘇聯的支援下﹐殘酷鎮壓了比夫拉獨立運動。
在尼日利亞黑人自相殘殺的血泊中﹐索因卡出於對於本民族的暴政統治的切膚之痛﹐開始反思是否存在著統一的“黑人特色”問題﹐撰寫了《L·S·森霍與黑人特色》﹑《現代非洲國家的作家》等一系列論文﹐指出﹕不少非洲作家沒有為維護其自身的權利做過任何事情﹐他們完全失去了現實的眼光﹐“非洲作家滿足于把眼光及時地朝後看﹐勘探古老的荒野中那些被遺忘的瑰寶﹐那些足以迷惑現在使之無所適從的東西。他們從來沒有向內看﹐從來沒有真正地進入現在﹐從來沒有觸及諸多無聊的﹑值得警醒的﹑可以預料的現已顯露的種種弊端”。索因卡希望非洲作家從非洲歷史的迷戀中擺脫出來﹐所謂“黑人特色”運動﹐根源於後殖民初期不必要的“恐英症”﹐這一運動實質上並未超越殖民主義意識形態﹐因為其倡導者實際上大多是被前殖民主義同化的人物﹐他們反過來對非洲的任何思想和價值觀﹐一概採取全盤接受的簡單態度﹔他們甚至幻想通過這場運動為拯救白人的墮落﹑拯救世界而架橋鋪路。那些幻想者沈溺其中的世界性關注﹐是把膏藥塗在“抽象的傷口”上﹐而不是塗在黑人自身殘酷性的病態裂口上﹐“這種非理性的高貴和種族精髓的神話大限已至﹐……事實上這個神話從未存在過”﹐索因卡借用一句格言說﹕“醫生﹐先治好你自己吧。”他進而指出﹐作家和知識分子應當從歷史中吸取有益的教訓﹐應當“重新檢討全部人類現象”﹐當然也包括重估非洲的本土文化。在他眼裏﹐“黑人特色”論者不過是一群非洲沙文主義者﹐他給他們起了一個綽號﹕新人猿泰山﹙neo-tarzanists﹚。
在《獄中詩抄》﹙1969﹚中的某些詩篇中﹐索因卡以“陳腐的獻祭”﹐“陳腐的契約”等意象來嘲弄某些塵封的非洲思想﹐把那些懷舊的非洲作家﹐那些熱衷於“整理國故”的文人﹐那些不斷掀起“國學熱”的文人﹐喻為在“死氣沈沈的退場行列”中的“時代的幽靈”。他指出﹐迷戀歷史是他們不敢面對現實問題的避世的手段﹑尋歡的形式。在全世界最腐敗的國家中﹐尼日利亞這個黑非洲的“經濟巨人”名列榜首。索因卡早在長篇小說《解釋者》﹙1965﹚中﹐辛辣諷刺尼日利亞的政治腐敗和宗教上的自鳴得意﹐探索尼日利亞知識分子在民族歷史與西化的未來之間尋找認同的心路歷程﹐實際上﹐他們不敢面對尼日利亞的現實的經濟問題和政治弊端。
今天看來﹐“黑人特色”運動原本有其反對帝國主義﹑種族主義﹑要求人的平等的一面﹐但一走過頭﹐就成為另一極端。當年薩特在《黑人奧甫斯》﹙1948﹚這篇著名論文中﹐把這一運動形容為“反種族主義的種族主義”﹐也就是說﹐他們找不到新的思想資源。“黑人特色”論者把西方視為一天天爛下去的腐朽社會﹐把非洲視為一天天好起來的新世界﹐屬於第三世界知識分子以其種族或民族名義來發言的排外主義範疇﹐是潮起潮落的反西方思潮的一脈分支﹐其餘波至今仍然時起時伏。這種採取“非洲—西方”截然對峙的視點﹐把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權力不平等關系確定為第三世界人民普遍被壓迫的生存狀況﹐從而掩蓋了後殖民地內部的另一種壓迫形式﹐它造成了一種假像﹕第三世界的不同階級或階層﹑群體或社群﹐仿佛同樣遭受外來壓迫﹐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而索因卡的一系列文學作品﹐生動地揭示了尼日利亞獨立之後的更為殘酷的壓迫。
【抨擊“後殖民”暴政】
英國殖民者在撤退之前為尼日利亞制訂了聯邦體制新憲法﹐可是一紙空文﹐無法約束後殖民黑人統治者以共和之名行獨裁之實。早在尼日利亞剛剛獨立時﹐索因卡就預感到新的暴政迫在眉睫。他於獨立日搬上舞臺的《森林之舞》﹙1960﹚﹐展現了一種“反諷的慶典”﹐劇中毫無贊揚尼日利亞英雄歷史的場面﹐毫無黑人的民族自豪感﹐而是打發“永不停息的死神”來抱怨恐怖的受難﹐展現尼日利亞前殖民的醜陋﹐十六世紀血腥的宮廷鬥爭。劇中一個女幽靈懷胎三百年﹐在生產的劇痛中生下一個並未成熟的“半孩”﹐一落地就大叫﹕“我生下來就會死去”。這一大煞風景的象徵﹐似乎是在暗示尼日利亞的獨立是個早產兒﹐尚未具備健康發育的生存條件。新貴們對此感到尷尬﹑憤怒﹐“黑人特色”論者也甚為不滿﹐他們對索因卡的西方戲劇手法尤為反感。
索因卡反省黑人本土文化的悲劇《死神和土王的馭夫》﹙1975﹚﹐是根據真實事件創作的。王宮馭夫為土王陪葬的傳統習俗﹐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1946年由於一位英國官員出面干涉才得以終結﹐因此活命的一個馭夫卻受到社群的鄙夷﹐因為他違背了悠久的民族傳統。在索因卡的悲劇中﹐馭夫實際上甘願殉葬﹐原因之一在於他周圍世界的腐敗使他感到生不如死。馭夫的兒子難以蒙受他父親苟活下來的“家醜”﹐為了洗刷恥辱﹐他選擇了自殺。索因卡展示出悠久的約魯巴文化反人性的一面﹐其奴隸制傳統實際上很難因民族﹑國家“獨立”而告終。
索因卡的荒誕劇《路》﹙1973﹚﹐把約魯巴文化中兼具創造性和破壞性的神奧貢神喋血的一面在一個知識分子身上薪火相傳﹐劇中的主人公老教授“下海”開設“車貨﹙禍﹚商店”﹐他不但為人偽造駕駛執照謀取暴利﹐而且對車禍有特殊的嗜好﹐整天從血肉模糊的屍體和破紙碎片中尋找闡釋生命奧秘的“啟示”。的確﹐獨立後的尼日利亞﹐實際上毫無實質性變化﹐人民唯一可以炫耀的﹐是他們終于有了黑人自己的政權。在一夜暴富的黑人中﹐不少是軍政官員利用權錢交易和裙帶關系崛起的官僚資本家﹐大多為富不仁。索因卡以《慰藉》一詩抨擊戈翁政權﹕
當他
進餐和喝酒──無疑──也要娶妻──
多少人肉生面團被揉捏
繞著他的餐桌和庭園
繞著他的國家和榮光
詩中還化用了一個法國歷史典故﹕在十八世紀末葉﹐法國皇后安托尼蒂聽說飢餓的窮人沒有麵包吃時﹐說﹕“那就讓他們吃蛋糕﹗”讀到這樣的故事﹐你不能不驚嘆﹐在中國與西方歷史上﹐王公貴族對于民生疾苦茫然無知是如此酷似﹕錦衣玉食的晉惠帝也不明白那些飢民“何不食肉糜﹖”
暴君戈翁處死了一大批當年的獨立運動領導人﹐並且把索因卡這樣的異議人士投入監獄。戈翁的後任﹑軍頭阿巴卡﹐1993年殘酷鎮壓了尼日利亞東南部三十萬奧戈尼族人民的和平示威﹐示威者所反對的﹐僅僅是濫採石油帶來的環境污染。在持續四年的戒嚴中﹐一千多人被殺戮﹐無數人被監禁。阿巴卡的更“傑出的審判案例”﹐一是1995年判處作家肯·薩羅─維瓦﹙Ken Saro-WiWa﹚等九名異議人士的絞刑﹐並且不顧國際社會的強烈抗議將他們絞死﹔二是兩年之後﹐以叛國罪判處16名異議人士絞刑﹐其中四名被缺席審判的流亡者﹐就包括索因卡在內﹙六十年代流亡歐洲和加納﹚。索因卡的主要“罪証”﹐是因為他的《一個大陸的顯露的傷口》﹙1997﹚一書﹐以薩羅—維瓦案為例揭發尼日利亞暴政。尼日利亞乃至整個非洲前殖民的原始野蠻﹐就是這樣在二十世紀繼續著。索因卡在一系列作品中進行猛烈抨擊和辛辣嘲笑﹐矛頭直指阿明﹑博卡薩等非洲政治巨頭。索因卡也抨擊後殖民情境中的新精英統治論﹙neo-elitism﹚﹐將這種新精英論稱為“強人症候群”﹐他認為在冷戰中﹐東方陣營或第三世界﹐共產主義世界和資本主義世界﹐都青睞這種“強人症候群”。權力的濫用使得尼日利亞成為非洲有史以來最殘酷的暴政國家。索因卡認為﹐“自由的最大威脅就是批評的缺席。”在某種意義上﹐索因卡是個專揭本民族“家醜”的批評家。
索因卡也並不偏頗於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之間的差異﹐而是始終盯著第三世界內部﹑尤其尼日利亞內部的差異﹐對抗一切權力結構中的各種壓迫形式。《慰藉》一詩中的麵包﹐既是人們必須的食糧﹐也是基督肉身的象徵。在詩人筆下﹐戈翁拋棄麵包進入蛋糕時代﹐也可以視為一個隱喻﹕獨裁者拋棄了伴隨殖民主義傳入的基督教文明。索因卡從小在基督教濡染中長大﹐他的父母都篤信基督教。一方面﹐索因卡清醒地認識到歷史上包括基督教在內的“聖戰”的血腥﹔另一方面﹐他又一再指出基督教的博愛精神並未枯竭﹐在長篇小說《混亂歲月》﹙1973﹚中﹐他希望按照一個基督教社群的村莊國家的模式來改造尼日利亞﹐甚至改造整個非洲社會。索因卡認為﹐後殖民非洲處在一個幻滅階段﹐這種悲劇並不是孤立的﹐其原因在於“仁愛的崩潰”﹐而缺乏眼光的非洲作家不曾以任何形式呼喚仁愛。因此﹐在一次演講中﹐索因卡指出﹕如果要消解地域文化界限﹐就只能在人文主義意義創造一種“共同之愛”﹐“其目的就是趨向共同之愛﹐對於那些把自己看作人的人們來說﹐沒有什?更高目的。”
六十年代﹐索因卡為了反對內戰﹐不惜冒險占領廣播電台發表演說﹐羈獄後繼續抗爭﹐出獄後流亡歐洲和加納。1974年戈翁倒臺﹐索因卡回國後﹐教學﹑寫作之外﹐致力於推動尼日利亞民主進程。1993年尼日利亞第一次贏得民主選舉﹐可僅僅十天後軍頭阿巴卡就篡奪了政權﹐並且踐踏民意把民選總統阿比奧拉投入監獄。阿巴卡發動政變時﹐還特別派遣直升飛機跟蹤監視索因卡的行蹤。
當時﹐老百姓都說﹕“他們大概不會射殺我們的諾獎得主吧。”可索因卡不敢抱此幻想﹐他意識到尼日利亞已經倒退到黑暗中世紀﹐不得不告別妻女﹐巧妙逃脫監視再次流亡國外。索因卡在法國創立了以流亡者為主體的“尼日利亞民族民主聯盟”﹐並且協助創立了“尼日利亞民族解放政務會”﹐反對新獨裁政權﹐繼續為尼日利亞的民主和自由奮鬥不息﹐他自稱為“反對派的外交官”﹐經常忘記自己首先是一個作家。他主張以一切可行的必要手段﹐例如公民的不服從﹐反對官方的不合理法律。他認為尼日利亞問題應當交聯合國安理會討論﹐從外交﹑文化和經濟上施加國際壓力﹐孤立﹑搞垮阿巴卡獨裁政權。可是﹐1998年阿巴卡死後﹐尼日利亞的民主仍然前途渺茫﹐直到2001年尼日利亞民主改革提上議事日程﹐高層政界不斷有人直接或間接表示﹐歡迎流亡美國的索因卡回國競選從政﹐但索因卡無意成為哈維爾第二﹐他永遠是一個民間知識分子的獨立角色。
資料來源:【多維新聞社】電子雜誌《民主中國》7月號發表。作者:傅正明/2002年6月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