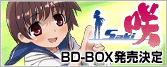史丹拋玉引磚,我的這塊磚頭就拿出來獻醜了。
這篇是慕大人的故事。
桐花詩
「那個慕祐祀,可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可不是麼,一個小小御史仗著皇上寵愛胡作非為、以下犯上,成何體統!」
慕祐祀兩年前被聖上拔擢入京,初授刑部主事,果然善辨疑獄,釋冤逾十餘人,一下聲名遠播,皇帝亦大為讚賞;後遷侍御史,掌糾舉百僚,推鞫獄訟。慕祐祀正直剛廉,又出身寒門,無世家背景束縛,自然搏擊不避權貴,一連參劾了好幾個惡名昭彰的大官,甫上任便『鋒芒畢露』,那些玩法舞弊的官員胥史莫不人人自危。雖他們自知該斂跡,亦不敢得罪皇帝的寵臣,但無不對其嫉恨在心,一時謠言四起,紛紛批評慕祐祀恃寵而驕,羅織罪名。
話聲傳到皇帝耳裡,聽說皇帝非但不怒,反而嬌媚一笑:「直諫不諱,唯有祐祀。」
眼看皇帝都表明了立場,更暗指接下來正是政風良窳的關鍵,在朝官員明白皇上決心整飭吏治,那些不愜於柏台的都老爺們個個風聲鶴唳,自相驚擾。果然不久後一個堂堂正三品的尚書又硬生生被慕祐祀打了下來,丟官出京。開缺事小,這一來非但傷了世家大族的顏面,也打壞了朝廷勢力的平衡;慕祐祀絲毫不為所動,筆挾風雷,一封摺子不只明劾政要,更暗批重臣,此舉令那些對慕祐祀深感不滿的朝中大老忍無可忍,聯名參奏,沒想到皇上竟順勢撤了三省長官,拉下那些徇庇欺罔的大臣,又將自個兒的親信安於三省,擴大中樞職權,以制門閥勢力。
慕祐祀一時名震朝野,一些更不好聽的傳言也更散播開來。
慕祐祀的廉潔奉公在任地方官時早已為民稱頌,朝中自然不乏矜名節、尚骨鯁,明辨是非的官員,對慕祐祀的不畏權勢無不欽佩,卻也不捨其犯眾怒,被世家大族盯上,怕她成為名門眼中的心腹大患,被諸多流言中傷、折其志節;另一方面,氏族也絕不會善罷干休,若犯了龍顏,朝廷官員不睦,亦非民之所望。
幸皇上聖明,選賢任能,從諫如流,天下之福也;但那些正直臣子們對於逾越君臣禮法一事便不多言,畢竟帝王對一兩個臣子特別寵愛,甚至擁有超越君臣之情誼並非未開先例。更何況皇上深知嬪妃爭寵之亂,至今未封后亦無納妃,對慕祐祀說得上是情有獨鍾;於禮雖有不合,於情卻不可謂之不通。
年輕貌美的英明帝王與俊俏有為的直諫忠臣之間的曖昧韻事,倒是被宮女們爭相讚頌,一時傳為美談。但有心人便於此大作文章,說是皇帝被近臣蠱惑,擾亂朝綱,流言紛擾,甚囂塵上。
「胡作非為,以下犯上?兩位大人可是指日前成祿一案?抑或是那違法亂紀的王尚書?」
禮部侍郎史君仲與吏部員外郎方維一驚,回頭發現來者正是慕祐祀,史君仲倒是裝模作樣地拱了拱手,「原來是聖眷正隆的慕大人,未有遠迎,慕大人不會因此參我一本吧?」
慕祐祀絳紅色的雙眼銳利地掃過兩人,淡然道:「成祿濫殺無辜,虛報戰功,理應當斬,聖上宅心仁厚,念其對我朝有功,革職流放便罷;而吏部王尚書行踰不檢,貪贓枉法,現值朝廷整飭紀綱之際,輦轂之下,豈容奸人藉勢招權?兩位大人居職不稱,在此道人長短,煽惑朝政,莫不是所云:胡作非為,以下犯上?」
資歷較輕的方員外郎沉不住氣,直指著慕祐祀,「妳不就仗著獨承恩寵,三天兩頭被召進宮,趁著耳鬢廝磨之際『枕上參奏』,否則一個從六品下的小御史怎能如此猖狂!」
慕祐祀聽了此等誣蔑之言不覺氣惱,只感到百般無奈,要是那人在床笫之間時肯聽她稟報公事就好了,那她也不必洋洋灑灑寫那麼多摺子,那人竟還嘲笑她:是不是該在妳家門外造個池,方便慕大人臨池洗硯?
史侍郎非但不多加勸阻,眼見慕祐祀沉默不語,以為機不可失,更加了句,「白天上朝,晚上……」話音未了,便與方維同聲大笑。
「只打蒼蠅不打老虎,則民心鬱積,未能疏導,反添不滿,而……」慕祐祀看也不看兩人,擺擺袖子翩然離去,只留下一句:「只打老虎不打蒼蠅,倒是擾人清夢了。」
「慕祐祀、妳、妳好!!」被這麼一調侃,史君仲也不禁滿面氣惱,對慕祐祀的背影大罵。
擾聲已遠,慕祐祀默然不語,清朗俊雅的面容比平常的面無表情又更覆上一層凝色,她朝著皇帝寢宮的方向望去,佇立良久。
「皇上,冉大人求見。」
正在批奏摺的上埜久一聽是來的是冉臻紫,便也不多擺皇帝架子,「進來吧,不必多禮。」
冉臻紫一身緋袍,面色沉靜地步入御書房,「臣參見皇上。」
「怎麼,平時妳不是躲朕躲得緊麼?怎麼今兒個自己送上門來?」上埜久閒適淡定地繼續批著奏章,一如往常地和冉臻紫話家常。
「皇上說笑了。」上埜久見冉臻紫的態度不似以往,她親自御賜的水晶鏡片下那鮮紅色的眼眸閃著些許思慮,便道:「有話就直說吧。」
「皇上,」冉臻紫抬起頭,與她的皇帝接上視線,「臣是為慕大人的事而來。」
「………」上埜久靜默不語,過了一陣才開口,「祐祀怎麼了?」
冉臻紫閉上眼,緩緩沉了口氣,才說道:「慕大人秉公無私、忠直敢言,以致得罪權貴,樹敵甚多,又優蒙聖眷,朝堂上擾擾紛紛,嘖有煩言。」
「嘖有煩言?」上埜久秀朗的細眉微微一皺,「論學問,祐祀才智突出,滿腹經綸,不開口則已,否則言談縱橫上下,鞭辟入裡;再論人品,持正清廉,耿介不阿,誰比得過祐祀?給她加官進爵,她不要,賞賜錢財,她更是不屑一顧,誰不知道慕御史府中堆滿文卷,只聞墨香,不沾侈靡,那些嘖有煩言的人,怎麼有臉?」上埜久越說越不高興,慕祐祀家中的唯一貴重器物,就是那年七夕她送給她的玉髮簪了。
上埜久知道慕祐祀從來不願接受任何自己的賞賜,她有一次甚至還在朝堂上當著文武百官的面故意捉弄她:聽說慕愛卿治獄仁恕,多所平反,釋冤多人,又不居其功,一時輦下獨頌尚書之明,這樣吧,朕來為妳做主,論功行賞,賜慕大人黃金二十萬兩,如何?
在朝百官都知道他們這位皇帝是個說一是一,獨斷果決的人,這句『如何』聽來可真是甚有轉圜,彷彿深知對方會拒絕,先給了人台階下似的,可天下誰又膽敢拒絕皇上呢?又有誰會拒絕聖上的賞賜呢?再也沒有誰比上埜久更瞭解慕祐祀的心思,她倒是想看看,這人會在眾人面前給她面子呢,亦或是直截了當地回絕她呢?皇帝高坐金鑾殿上,面帶和煦,朝中卻只有兩人看得出她眼中的玩樂意味。冉臻紫不禁在心裡嘆了口氣,慕大人,招惹到這人,算妳上輩子倒楣。
慕祐祀抬起頭,望向金碧輝煌的殿堂上真正耀眼奪目的那人,她雍容大方,眼中的媚意卻只有她看得出來。「皇上。」慕祐祀神色不動,語氣沉穩,「臣承蒙聖上恩澤而倍感不安,帝輦之下,尚多冤民,四海之廣,兆民之眾,豈無枉者?釋冤十人,則冤獄者千百,枉死者更甚。國家未安,冤案未平,臣奉職無狀,不予責難,已蒙聖上恩寵,何來功績?臣在其職,謀其事而矣。」後又引了一段訓儉示康: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把朝中頗有貪名的官員順道罵了一頓,最後再加了句,「皇上聖恩浩蕩,臣不願獨享,還請施恩予困苦不堪、衣食不飽的黎民百姓。」
朝中百官被慕祐祀的抗顏舉動嚇得不敢作聲,那些就只差沒被指名道姓,風尚日靡的世家大族們更覺刺耳,氣得牙癢癢,心中把慕祐祀的裝模作樣罵了個透,忿忿等著皇上降罪下來。殊不知朝堂上含笑端坐的那人聽到這裡,幾乎已經完全不行了,光聽到那句奉職無狀,上埜久就已因忍笑而費盡心力,若說慕祐祀奉職無狀,那麼天下還有誰敢說自己『奉職有狀』?好個慕祐祀,好個訓儉示康。上埜久清麗的面容仍是一片平和沉穩,只眉目帶笑,溫溫和和地說了句,「慕愛卿品性高潔,仁厚愛民,難能可貴,那麼朕便以慕大人的名義發放糧餉於天下,時三月,再減輕賦稅一年,可好?」
正當眾人被皇上的百般順從的舉動驚訝得嘴都闔不上,慕祐祀已淡然謝恩,「謝皇上。」
「那麼便退朝吧。」冉臻紫望著那沉著狡詐的當今天子面帶從容卻急著離開的身影,很輕易地便可以想像上埜久一步入後殿就忍不住捧腹大笑的景象。
「皇上…」冉臻紫的叫喚將上埜久從回憶中喚醒。
「妳要說的我明白,」上埜久聲色不動,心裡卻早有打算,「下去吧,臻紫。」
冉臻紫明白上埜久心思,便不再多言,「微臣告退。」
數日後,海城下四郡因大雨決堤,南犯德清,西決內黃,東淤梁村,北出闞村,漫溢成患,災情嚴重,經徹查後發現為前年奉命修渠的工部尚書減工受賄,侵吞公款,營私舞弊。皇帝怒不可遏,在朝堂上大發雷霆,厲聲喝道:「民為國本,民力困竭則為國之困頓。我朝以農立國,民生要務首重治河,修渠築堤涉牽萬千百姓生計,本應嚴剔弊端,慎重職守,今工部尚書劉繹及其諸僚屬減料偷工,剋扣抑留公款,中飽私囊,視人命為草芥,罪不可恕,一干人等著即革職拿問,朕要親自治罪!!」
皇帝性子溫文柔和,自登基以來從未見她如此盛怒,就連侍立在兩側的宮女也難掩訝色,眾臣驚恐不已。皇帝上位已四、五年,臣子們大約也摸透了這新主子的性情。上埜久向來喜怒不形於色,縱然是當年太傅直犯龍顏,結黨營私,意圖架空皇權,也未見性情冷靜的皇帝大動肝火。朝堂之上,皇上向來是微微帶笑,不怒自威,音聲平穩卻清澈懾人,而如今竟如此勃然大怒,諸位大臣心裡便明白皇帝對治河一事何其重視,而一干忠直老臣則備感欣慰,這位年輕的皇帝愛民如子、憂國憂民,社稷之幸也;甚且在盛怒之下還能冷靜直斷,毋枉毋縱,實德比顓頊。
劉繹是門下侍中趙寧的姪子,當初治河修渠的人選也是他薦舉的,如今出了紕漏,皇上親自治罪,劉繹怕要小命不保,趙寧為北方鎮守頤親王的親臣,即使是皇上也要看他三分情面,顧不得龍顏正怒,往前一站,「皇上…」
沒想到趙寧話一出口,更惹得皇帝拍桌大怒,龍案上一個紫砂茶壺應聲落地碎裂,「趙寧!你好大的膽子!劉繹褻瀆職守,溺職辜恩,你本逃不了連帶責任,朕念你曾侍奉先帝、亦為輔國重臣,不願多加追究,你竟還敢出言維護!可是非要朕斬立決,以儆效尤?還是你想陪著你那欺君犯上的姪兒一起掉腦袋?!」
皇帝這一席話讓趙寧震駭非常,撲通一聲就跪了下去,「皇上恕罪!」
上埜久怫然退朝,朝上也沒人敢多說一個字,這些重話直責趙寧,又暗指如此重大的職務,誰任誰倒楣,更沒人再敢引薦推舉,深怕禍及自身。只有冉臻紫惋惜地嘆了口氣,暗想:真是可惜了那珍貴的宜興紫砂胎呀。
朝堂上除了唉聲嘆氣的冉臻紫以外,還有一人對皇上的怒氣絲毫無動於衷。慕祐祀望著上殿空蕩的龍椅,定如止水的表情讓人摸不透心思。
一連過了幾天,皇上都沒對任命治河的事開口,只下令讓海城縣令親自巡視,儘速救災,就地賑濟。再傳令於臨近諸城協助應變,收容災民。
皇帝寢宮之後穿過長廊便是御池。晚膳後,上埜久反覆閱看海城縣令稟報災情的奏摺,幾經思量,往旁一擺便往御池走去。一旁隨侍的侍女上前服侍脫衣,她們除去她的藍江綢面青白袍、外衣與單衣…直至上埜久脫下身上最後一件罩衣時,她正好踏進煙霧繚繞的大浴池。四位侍浴的侍女馬上以瓢汲溫水,澆淋在上埜久的身上,浴池內有一座白玉石造的石床,上埜久便躺入浴池內,讓兩位侍女伺候澡浴。泉水中芝蘭馥馥、芍藥清香,侍女們將香泉輕拍在上埜久身上,再用鈍口的墨玉刀緩緩刮著她白皙柔滑的肌膚;另一名侍女捧著裝盛茶紫枯、地烏桃的琉璃碗伺候上埜久沐髮,仔細地用翡翠梳梳理她赤墨色的柔順長髮。最後一位侍女則在身後替她按摩,在按摩時,侍女也不斷地將逐漸溫熱的水淋在上埜久身上。花瓣片片,水光瀲灩,上埜久若有所思地閉上眼,無聲地舒了口氣。
御池門外傳來腳步聲,上埜久的貼身侍女跪伏在門口,輕輕細細地稟報,「皇上。」
上埜久還沉浸在沐浴的紓緩及自己的思緒之中,慵慵懶懶回了聲,「怎麼了?」
「慕大人求見。」
當上埜久回到寢宮時,慕祐祀身著一襲素淨長衫,已在門邊等著她。她並不高大,就這麼凜凜斂斂地站著,頎長的身影看來比誰都要挺拔。
而上埜久全身上下只披著一件絲質色淺的外袍,雪白的肌膚春雨點點,正逐漸浸濕著那柔滑服貼的袍子。那浴袍看起來似乎才剛被披上,連腰帶都還沒繫好,幾個侍女一臉著急地追著上來要幫她擦拭身子,緋紅濕濡的長髮沾粘在她的後頸,水珠聚集,自深色髮稍不斷滴落,水跡一路從御池跟著來到寢宮。
侍女們拿著浴巾圍著她急得團團轉,上埜久卻只是一臉從容地望著慕祐祀,一滴帶著香氣的泉水順著她的臉頰滑落而下,嫣然巧笑,「真是難得啊。」
這是慕祐祀第一次在夜裡主動來找她。
平時慕祐祀若主動晉見,絕不會是為了私事。這人公私分明得很,除非她用盡手段,否則慕祐祀從不在白天多跟她調笑一句。只有兩人在夜晚相見時,她才願意退去臣子的束縛。至於商議政務,繾綣纏綿時刻,上埜久自然不會讓她提到一個字。
慕祐祀深潭般的絳紅眸子徐徐緩緩地將眼前的上埜久繞了一圈,才將長衫下襬撩起,重重跪下。她說,「臣,參見皇上。」
在夜裡,在朝政以外,上埜久向來都是禁止她們君臣相稱的。她低垂著目光,凝視著慕祐祀垂下的淡色眼睫,「……有事麼。」上埜久手輕輕一抬,侍女們便退到一旁。
慕祐祀低著頭,她沉靜地開口,「皇上,臣有一事相求。」
「妳從不向朕求任何東西。」上埜久苦澀地笑了笑,彷彿早知道慕祐祀會向她提出什麼樣的請求,她張了張嘴,好一陣子才講出這兩個字,「說吧。」
慕祐祀終於將頭抬了起。她是這麼樣一個平靜淡然的人,卻擁有一雙足以灼傷人的瞳色。她低沈悠渾的嗓音清晰地傳入上埜久耳裡,「請派臣出任治河。」
「現海城百姓困苦,哀鴻遍野,賑濟救災除疫,善後而矣。河若不治,內憂未除,則民不聊生,國將不國。治河之弊,在於吏貪,故臣以為,治河須先治人,人不治則洪患永難除。」慕祐祀吸了口氣,最後才一字一句地說道,「此事唯有臣可勝任。」
上埜久抿了抿唇,她覺得有一股酸氣難受地衝上胸腔,她望著慕祐祀那與她瞳色完全相反的、冷靜到幾乎令人覺得可恨的無波眼神,一時思緒紊亂,百端交集。她只能費力張著眼,阻止她的眼眶繼續發熱。最後上埜久轉過身子,「朕正有此意,明朝朕就會正式下旨,妳回去吧。」她深深吸了口氣,以她最輕的聲音說,「送慕大人。」
她屏住氣息,等待著慕祐祀起身離去的聲音,卻突覺身子一緊, 耳邊傳來侍女們的抽氣聲,慕祐祀身上的氣味已包裹住她。
「久。」
紫桐花香。
「………放開我。」上埜久抿著唇,好不容易才吐出這句話。現在的她正處於完全無法承受任何溫柔對待的狀態。慕祐祀的體溫透過絲料直接滲入她的肌膚,幾乎是慕祐祀一碰觸到她,她的淚便掉了下來。
「這是下旨麼?」慕祐祀在她耳邊溫溫軟軟地說著,上埜久心裡最脆弱的部分,一直只有她觸碰得到。
「如果我說是,妳要如何?」她的身體再沒法支撐,鬆散散地癱在慕祐祀身上。
「那麼臣只好………」慕祐祀低低地笑了,溫熱的氣息噴在她頸項上。
「冒死抗旨了。」
慕祐祀親吻著早已軟倒在自己身上的上埜久,拉下了帳中帷幔。寢宮內一個較機靈的侍女已拉著其他幾個看呆了的往外跑,緊緊閉上門,發現帷外的值夜侍女早已推推搡搡地偷聽著,相對默笑。
月下何所有?一樹紫桐花。桐花半落時,複道正相思。
二月,慕祐祀改任都水監奉命治河,以御使的身分前往督辦河工,總管海城洪災治理工程,朝中嫉恨者皆竊然欣喜。
慕祐祀治河有成,立功回京,詔封為工部尚書,則已是一年後的事了。
--
我實在不懂為什麼很會寫古裝文的人那麼愛叫人寫古裝文給她看orz
這是我人生第二篇古裝
第一篇是黑歷史
寫完這篇
大概耗費了我寫半年現代文的腦汁
我從來不會看輕我自己努力完成的作品
就算並沒有到達一定水準
我也不會過度自謙說:抱歉傷眼
之類的話
不過我真的要老實說
古裝真是我的罩門
我從來不會主動去寫
也不會有自信想PO出來
今天如果沒有史丹
我絕對寫不成這篇
真的很感謝她的指導參與
經過了大概一個多禮拜的琢磨
終於熬出這篇
算是達成了一個本以為達不到的願望
就是寫部加治的古裝文
還是昏君臣戀
不過我本來要先寫的並不是這篇囧
所以我還有得熬orz
寫古裝文真的是會對這句話感受深刻:詞窮可恥
還有趙寧同學真是躺著也中槍
我一開始看九月時問史丹:趙寧是誰?
她回:今天上課時點名聽到的名字
趙寧同學對不起/口\
最後感謝友情客串的某兩人
若想知道史君仲是誰
請看這
方維的話
有機會再介紹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