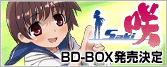史丹的戴威威爆字數,
本來以為只分上下,結果現在分五集還不知道寫不寫的完。
本篇永水女子到齊wwwwwwwwwwwwwwwwwwww
「那便是祁連山麼?」戴篠蒔一襲玄色綢緞長衫,外頭還罩著件狐襖,看上去就似個商賈之家。她騎著匹刺史送的高大黑駿馬,因為天冷的關係雙頰微微泛紅,卻無損她的英姿煥發。商隊自燕州出發時已過秋分,入了季秋,廣大草原也早已轉黃,西風揚起陣陣塵沙。戴篠蒔瞇起眼,只隱約見到一座高聳入雲的山隱沒於一片霜白中。
狩宿巴腰間配著一炳長劍,穿著短掛皮裘,一副武人打扮。狩宿巴雖是文官,可畢竟是胡人,自然有些功夫底子,她戰戰兢兢地守在戴篠蒔身邊,生怕這位主子有了什麼萬一。「是啊,約一盞茶時間就能到。」他們一行越接近祁連山就越能感覺到一股肅殺之氣,有道是:金河秋半虜弦開,雲外驚飛四散哀。狩宿巴與那批馬賊交手過幾次,自然不敢小看他們。一行人裡,也就戴篠蒔還一副面色沉穩的模樣,讓狩宿巴不住苦笑。「此地已入馬賊勢力,咱們還是當心點好。」
戴篠蒔微微一笑,眼睛卻盯著她背後。「看來是晚了。」
遠方塵土飛揚,馬群嘶,一支響箭破空而來,直直射在被牢牢護在中心的那只箱子上。戴篠蒔被狩宿巴護在身後,看著遠方一隊人馬踏著滾滾黃沙而來。她忍不住在心裡歎息,活了十九年,今日才總算知道何謂:鳴骹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聲更干。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若我璟朝有如此兵力,準葛爾部又何患之。
領首的是個年紀與戴篠蒔相仿的少女,她穿著皮製短衣,雙手束著皮護腕,腳下一雙黑亮的皮靴,寬腰帶繫著長刀,一頭墨綠長髮裹在絨皮帽裡,手上舉著還未放下的大弓。這大漠兒女,果然與眾不同。戴篠蒔忍不住心想。這少女實是比她看過的任何男子都還要來的豪放雄邁。
「打擾諸位。」少女的漢語說得極好,只是音調有些怪異。她淺蔥色的眼在眾人間轉了一圈,自然便落到了錦衣華服的戴篠蒔身上。「這位便是領頭的麼?」
戴篠蒔也不多說廢話,她越過狩宿巴,毫不畏懼地直視少女。「正是。」
少女見戴篠蒔毫無懼色,心裡覺得有些疑惑。可這商隊上下也才五十餘人,剛才跟了幾里,也不見有埋伏。莫非這人是單純膽子大麼?她偏著頭,笑道。「我不想為難你們,把值錢的東西放下,我便留你們一命。」
戴篠蒔朝她眨了眨眼,也跟著笑。「這本就是要送各位的。不過,我向來不做賠本生意,更何況是將千兩黃金拱手送人?」
「閣下言下之意,是不要命了?」少女刷地抽出腰間長刀,身後眾人見了她動作,也跟著拔刀怒目而視。那刀鋒在正午日光下亮晃晃的,刺眼得很,狩宿巴也握住劍柄,雙方一觸即發。
戴篠蒔卻對這樣緊張的氣氛恍若未覺,她依舊淺笑著,對少女道。「墨少主,在下與妳談筆大生意可好?」她擺了擺手,守在一旁的人立即開了那只箱子。箱內裝著黃澄澄的金子,燦爛奪目。饒是縱橫漠北數年的馬賊們,也沒見過這麼多的黃金,一個個全都看直了眼,目光滿是貪婪。「這就作為給各位的見面禮。」
墨見春瞇起眼打量她。戴篠蒔雖然入朝不久,但畢竟也在朝中歷練過,兼之出身世家,自然比別人來的冷靜穩重。墨見春看她一襲錦衣卻隱隱透著官家派頭,心裡也有了底,於是戒慎道。「你們漢人素來狡詐,何況我族與妳大璟有血海深仇,無話可談。」
戴篠蒔聽她如此直接,也不氣惱,只是笑道。「墨少主聽聽又有何妨?更何況,若是少主不願意合作,也請收下這黃金。」她手一揮,身後眾人立即散去,只留下駝著一口紅箱的馬車。「這樣吧,為表誠意,我願孤身隨少主回營,與少主詳談。」
墨見春還未答話,一旁狩宿巴搶先喊了聲主子。語氣中盡是責怪,又是懊惱,她狠狠地瞪著戴篠蒔,彷彿恨不得馬上把她綁了帶回燕州。
「我信墨少主。」戴篠蒔卻毫不理會她焦急的目光,仍是一派從容。她望著墨見春,見對方眼中閃過一絲猶豫,於是又道。「不然,你們可將我綑起來,如何?」
「主子!」
「好,我答應妳,也不綁妳。」墨見春爽朗一笑。她可不怕戴篠蒔玩什麼花樣,那傢伙看上去就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模樣,怎麼樣也抵不過他們驍勇善戰的根尾谷部。可她看上去自信滿滿的模樣,倒是大大引起了墨見春的興趣。馬賊向來重利,更何況還是黃金與人質兼得的無本生意。當下便分了大半人護黃金,自個兒領著一小部人與戴篠蒔揚長而去。
狩宿巴卻在原地望著戴篠蒔離去的身影,氣急敗壞地領著眾人回燕州。她長鞭一揚,打得那可憐的馬兒不住嘶叫。狩宿巴轉回頭去,只見戴篠蒔的身影迅速隱沒在翻痕似浪的塵沙中,只能長歎,心裡祈求自家主子能平安歸來。
草原上向來弱肉強食。根尾谷部曾經稱霸漠北,可後來卻被崛起的草原之狼準葛爾部給取代,最終走向滅族。強者為王,敗者為寇,根尾谷部殘族流竄到祁連山,原來的墨氏貴族失勢,由旁系的哈氏掌權。墨見春是族長女兒,在戰爭中被幾個族長親信護著逃了出來,隨著族人遷徙到祁連山。墨見春一直等著,像老虎盯著獵物般伏在原地苦守,等到實力壯大時機成熟之際,便殺了哈氏,奪回大權。
墨見春認為要想活著本來就是這樣的。我不殺人,人必殺我。這世上便是如此殘酷。戴篠蒔想和她談事,姿態擺得很低,墨見春明白她是求自個來了,於是也不設防,在大帳裡設宴款待她。
中原人素來詭計多端,還有句話說,『無事獻殷勤,非奸即盜。』。可戴篠蒔看上去是個很乾淨的人,墨見春看著她覺得挺順眼的,所以才有可談之機。換別人來,大概一刀就讓墨見春給砍了。
「那麼,閣下現在可以詳說了吧。」
「自然。」戴篠蒔落落大方,即使身在敵帳,也未見懼色。她先向墨見春拱手,斂色道。「在下乃是燕州錄事參軍戴篠蒔,此行前來,是想與少主商議招安一事。」
墨見春狠狠瞪著她,冷笑道。「招安?妳可真敢說。」
戴篠蒔微微一笑,神色從容,她先細細觀察了墨家兩姊妹的反應,然後才續道。「漢人有句話說,『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可在下想,墨少主胸懷大志,肩負根尾谷部上千條人命,自然不會輕率做決。」
「閉嘴,奸詐的中原人!!!」墨見春身邊那嬌小的女孩從位置上跳了起來,舉起手邊大弓,彎弓搭箭,長箭離弦飛出,劃過戴篠蒔白淨的臉龐。泊泊鮮血順著臉頰滑下,戴篠蒔卻渾然不覺疼痛,仍是微微笑著。
「要射,就對準點。」戴篠蒔淺笑,伸手指著自個心臟位置,她環顧帳內眾人,朗聲道。「真要,就一箭射穿我的胸膛。可我告訴妳們,我戴篠蒔代表的是大璟皇帝,我身後的是強盛的大璟皇朝。妳們今日殺了一個戴篠蒔,那就是將整個部族推向絕路。」她語氣凜然,擲地有聲,聽得根尾谷部眾人忍不住肅然。這人看上去嬌弱,可沒想到竟是一身傲骨。
墨見春握住了少女執弓的手,沉聲道。「姐姐,住手。」
墨初美狠狠地瞪了戴篠蒔一眼,悻悻然地收手。墨初美雖為墨見春長姐,但生性魯莽衝動,因此族中大小事物向來都是交由墨見春定奪。如今墨見春既然發話了,墨初美也不好在眾人面前與她爭執,於是退回墨見春身後,讓墨見春全權處理。
「我根尾谷部雖弱小,但也不輕易降伏,戴參軍請回吧。」
戴篠蒔見墨見春似乎有服軟的趨勢,於是趕緊道。「少主先聽過我方條件,再決定也不遲。」墨見春仍是沉吟不語,戴篠蒔知道這是可以商議的意思,於是也顧不得臉上傷口仍在泛血,抓緊機會說道。「我既代表大璟皇帝前來,自然不會虧待貴部。皇上有旨,若少主願臣服我大璟,即便是想復興根尾谷部,我方亦當傾力相助。可在下有一言,不知少主願不願聽?」
墨見春似乎有些動搖,於是擺了擺手,說道。「請說。」
「在下以為,如今情勢,不宜重建。我大璟疆域遼闊,願收納貴部,於燕州劃區予貴族千人定居,封諸位為官,享衣錦榮華。」戴篠蒔看根尾谷部的其餘貴族似乎有些心動,可墨見春一聽了不宜重建就沉下臉色,於是又道。「在下自然不是說諸位乃貪圖安逸富貴之人,可我以為,如此才是貴部久安之策。恕在下直言,就算我朝襄助復興,那便如何?稱霸草原?先不說我璟朝正是強盛繁榮之時,漠北亦有準葛爾部虎視眈眈。如今復族,不過是在縫中求生。況且,準葛爾部宮永照雄才偉略、野心勃勃,覬覦祁連山以久,諸位不會不察。難道少主以為,此時復族,能逃過準葛爾部鐵騎嗎?」
帳內寂靜無聲。墨見春瞇起眼,細細打量這個看上去弱不禁風卻氣勢凌人的傢伙。戴篠蒔這人她是知道的,墨見春雖是馬賊,可也不是只會劫掠的無謀莽夫。她在燕州裡買通了幾個低下官員,把燕州城裡的形勢與大小事務都摸得一清二楚。戴篠蒔一來她便收到消息,這人是得罪皇帝被外放的,可璟朝右相卻是她表親,故而才在燕州備受禮遇。
本以為這人只是紈絝子弟,不足為患。可她孤身入敵帳,對墨初美的威脅面不改色,還表現出視死如歸的氣魄。適才一席話又說得頭頭是道,一字一句都敲在她心上。此人絕非池中物。墨見春心裡早被說動,可想起戴篠蒔是犯了罪外放的,還是忍不住懷疑道。「戴參軍龍困淺灘,叫我如何信妳?」
戴篠蒔卻早料到她會有此一問,於是笑道。「我還有一事欲與少主商議,若少主有意詳談,但請屏退眾人。」
「好。」墨見春於是讓眾人退出大帳,只留下姐姐墨初美。眾人雖有微詞,卻也不敢多說。墨見春不是性子暴烈的人,可卻也不是個能容人忤逆的主子。在根尾谷部,向來說一不二,眾人見她發話,也明白她心裡有了打算。戴篠蒔從眾人神情中也知道,自己成功了一半,於是暗自鬆了口氣。「這下戴參軍可說了吧。」
戴篠蒔一放鬆下來,便覺得臉上一股火辣辣的刺痛感襲來,她雖是沒落豪族,但畢竟是大戶人家,哪裡受過這種苦。可墨見春與墨初美兩姐妹仍直直望著自己,她也只好咬著牙苦撐,裝作不疾不徐的樣子,自寬大袖中拿出一只玉牌。那玉牌晶瑩透亮,翠綠如葉,近看還可見細微如葉脈的紋路。玉牌正面書上埜二字,反面刻有璟朝國章。
「以此為證,我今日前來,非以燕州錄事參軍身分,而是皇上欽點御使。在下赴燕之前,曾得聖旨,將今次談判全權交付與我。故適才所說,皆是我個人的意思,若少主願意,自然還可商議。」戴篠蒔將玉牌放在桌上,態度落落大方。「我大璟皇帝登基五年,掌權三年。貴部血海深仇,乃頤親王一手主導。當然,同為大璟朝臣,我如今並非要卸責,而是想告知少主,頤親王乃一介臣子,不代表我朝皇上,更足以不代表大璟。」
墨見春拿起那玉牌仔細打量。她們做馬賊也有四、五年時間,自然是有些辨別的眼光,這玉質地溫潤,一看便知是皇家才用得起的上等好玉。她與墨初美互視一眼,心裡也信了半分,於是又道。「那麼,戴御使還有什麼條件欲說服我拋下深仇,臣服貴國。」
戴篠蒔微微一笑,語氣輕緩平穩,一字一句地說。「頤親王的首級。」
「可頤親王不是…」
「墨少主。」戴篠蒔直直地望著墨見春,面色沉靜,如夜般漆黑幽暗的雙眸裡隱隱含著氣吞山河的氣概。她的嘴角若有似無地含著一抹笑,彷彿看盡了一切,自信昂揚,似乎形勢盡握在她指掌間。「皇上旨意,付權與在下,那麼,」她聲音清脆悅耳,婉轉動聽,卻不知怎地,挾著一抹令人心驚的狠絕。「頤親王的首級,自然也是任我處置。」
墨見春也不是傻瓜,一細想便知她話中深意,於是嘲諷。「都說你們漢人重倫理,可想不到連皇家也手足相殘。」
戴篠蒔揚起頭,義正凜然地笑道。「此言差矣。皇上英明果決,比起手足情誼,更懂得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既然對方已經把話說到了這份上,墨見春不多囉嗦,只是舉起桌上酒杯,一飲而盡。「先乾為敬。」
「請。」主人都這麼說,戴篠蒔也沒有推辭的意思。她知道,喝過這酒,就等於大局已定。她學著墨見春一口飲盡杯中酒,只覺得喉嚨被熱辣嗆得難受,於是忍不住咳了出來。這一咳,又牽動了頰上傷口,痛得她嘶牙裂嘴,讓墨家姐妹看得哭笑不得。
事已成,戴篠蒔也放下心裡重擔,便於祁連山待了三天,才於墨家姐妹護送下返回燕州。招撫根尾谷部原就是大功一件,何況還領族長歸來,讓刺史章立瞠目結舌。戴篠蒔立下奇功,除一干同僚對她刮目相看外,自然也是燕州人人傳頌的對象。這事傳到了頤親王那,不日後便派人遞了請帖,說是戴參軍勞苦功高,三日之後,於王府為其設宴慰勞。
親王親自設宴,在不明就裡的人眼中可是一大殊榮,可看在明白箇中道理的人眼裡,卻又是一回鴻門宴來了。身為主角的戴篠蒔倒是一點也沒放在心上,她自祁連山歸來,被石戶霞發現臉上掛了彩後,就讓她一副泫然欲泣的模樣心疼得差點沒指天發誓絕無下次。人還沒安撫好,這頤親王的請柬馬上就到了府上。石戶霞比任何人都清楚這次會面的重要性,也不再鬧脾氣,趕忙去替戴篠蒔準備與宴禮服。
戴篠蒔讓人領到王府廳裡時,頤親王椅端坐主位,陪席的還有頤親王府上參軍戴權。戴篠蒔今日頭戴介幘,一襲對襟大袖衫,襯著玉珮組綬,儀表堂堂,氣度瀟灑自若,讓頤親王也忍不住稱道:這戴篠蒔果然是一表人才。
「下官戴篠蒔,拜見親王。」
「免禮,戴大人快請入座。」頤親王長得與皇帝頗為相像,因鎮守邊關,臉龐上帶著久征沙場的風霜。他不若上埜久的柔美俊雅,眉眼間卻透著狠戾,讓五官端正的頤親王看上去有些陰鸞深沉。「本王與戴大人表親符穗也算是點頭之交,妳事於燕州,本王早應設宴接風,可惜政務繁忙,耽誤時日。篠蒔莫要怪罪本王。」
「豈敢豈敢。」一聽見頤親王喚自個名字,神情親熱,戴篠蒔立馬在心裡打了個冷顫,可臉上仍是笑容可掬。「下官一介犯臣,怎敢擾煩親王。」
頤親王微微一笑,可那眼神卻意外凌厲,彷彿想把戴篠蒔的心臟都掏出來好好細看一般。戴篠蒔也不迴避,坦然回視。「篠蒔,本王給妳引見。戴權乃王府參軍,數年來,出謀劃策,立功無數。戴參軍算來是妳父親堂弟,可長居關外,不知篠蒔對這位長輩可否有印象?」
戴篠蒔是知道這位叔父的,可只見過兩次,一次是父親被貶職,一次是父親逝世。兩次都不是什麼好事,自然對這位叔父沒什麼好印象,可礙於頤親王面子,也只好笑道。「當然記得。幼時見過叔父幾次,若干年後再會,叔父英挺如昔。可篠蒔不知叔父仕於王府,今日才得以拜會,望叔父莫怪姪女失了禮數。」
「哪兒的話。」戴權言笑晏晏。他雖已年屆不惑,但仍舊偉岸挺拔,眉眼間看得出來與戴篠蒔有幾分相似,只是多了份滄桑世故。「姪女多年不見,未想到出落得如此亭亭玉立。日前聽人談起招安馬賊立下大功的戴參軍時,可真沒想到是姪女妳。」他暗暗瞟了頤親王一眼,話鋒一轉,語氣中滿是惋惜。「姪女在朝中之事,叔父亦略知一二,可歎我心有餘而力不足啊。這些年,皇上對門閥處處制肘,視世家如眼中釘。我本有意回鄉探望姪女,可又擔心此舉會落人口實。如今姪女任于燕州,叔父自當頃力相助,妳有何困難,但說便是。」
這兩隻老狐狸還真沉不住氣。戴篠蒔心裡暗笑,可還是露出鬱鬱寡歡的模樣,她輕歎一聲,執觴的手頓在半空,斂眉低目,有苦難言似地苦笑著。「姪女早置生死於度外,如今牽掛,唯有母親而已。可歎表姐韜光養晦,卻受牽連,篠蒔實在難辭其咎。」
頤親王微微挑眉,神色驚訝地問道。「符大人官運亨通,近日高升右相,何來牽連之說?」他見戴篠蒔神色愁苦,似乎真有什麼心事,於是放柔聲調,好聲勸道。「戴權與本王相識甚久,乃刎頸之交。他的事便是本王的事,篠蒔在京受了委屈,不必在意本王身分,但說無妨。」
戴篠蒔沉吟半晌,猶豫地來回看著面容慈藹的戴權與神色溫和的頤親王,然後才下定決心道。「不就是慕祐祀那亂臣賊子麼。」她語帶憤懣,可看上去仍有些不安,她躊躇了一會兒,才又續道。「那慕賊迷惑皇上,擾亂朝紀,危言聳聽,使朝中一等官員自危,諸臣噤若寒蟬。眼見皇上受奸賊蒙蔽,我大璟數百年基業岌岌可危,於是冒死進諫,豈知皇上竟不辯忠奸,不明我一片赤膽忠心。」
「慕祐祀這人本王也略知一二,可皇上她…」頤親王憂心忡忡,他低頭長歎,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模樣。「皇上說了什麼,篠蒔不妨直說。」
「還能說什麼呢。」戴篠蒔憤憤不平,委屈地抱怨著。「皇上下旨編史,事關體大,流傳百世,自當公正詳實。我將慕祐祀之事照實撰寫,皇上得知,卻連夜宣召。見到我劈頭便罵,戴篠蒔妳好大膽,平日於人前亂嚼舌根也罷,可卻在璟史裡將慕大人寫得猶如惑國妖姬,如此莫不是讓後世子孫笑話朕是昏君麼?皇上龍顏大怒,幸得表姐求情,才免一死,外放燕州。可皇上畢竟忌憚符家勢力,降罪於我,又以右僕射一職安撫符家。」
頤親王聞言,拍桌怒罵道。「竟有此事。」他高舉羽觴,抬頭望天,裝做悲痛欲絕的樣子。「先皇曾囑咐本王擔起撫國重責,而今慕賊禍國殃民,汙衊忠臣,我上埜遠竟恕手無策,愧對父皇。」他仰頭飲盡,大有借酒澆愁之意。
戴權見狀,連忙勸道。「親王何須自責?親王鎮守邊關,抵禦外族,實為我大璟門戶,京師遙遠,鞭長莫及,皇上受奸人蒙蔽,豈是親王責任。」
眼見兩人配合的天衣無縫,戴篠蒔忍不住在心裡翻了個白眼。這兩個亂臣賊子在這哭天搶地,憂國憂民,還真演得入木三分啊。她雖然如此想,卻表現出無比贊同的模樣,面容誠摯地道。「親王如此明理,憂心國事,乃我大璟之福。而今國難當前,下官有一不情之請,懇請親王答允。」
「戴大人請說。」
戴篠蒔連忙起身,拜伏在地,直視頤親王,大義凜然地朗聲道。「下官懇請親王進京勤王,誅慕賊,清君側。」
頤親王趕忙扶起她,面有難色地歎息。「可本王若如此做,便是無視君臣倫理,以下犯上,這、本王怎擔得起如此罪名?」
「想不到親王竟如此貪生怕事。」戴篠蒔隨即沉下臉,神色冷凝地望著頤親王,厲聲斥責。「食君之祿,分君之憂。我戴家歷代,世受皇恩,如今奸臣當道,生靈塗炭,若不除賊,愧對祖上。親王身為皇上兄長,人言道,長兄如父。而今皇上誤信奸臣,親王當負勸諫之責,怎是以下犯上?倘若親王真如此怕事,我戴篠蒔只好冒死除奸,血濺三尺,在所不惜。」
此話正中頤親王下懷,他臉上不動聲色,沉吟半响,才終於毅然決然地道。「是本王愚昧,戴大人恕罪。未知戴大人有何妙策,還請賜教。」
戴篠蒔見頤親王答允,破顏微笑,向頤親王與戴權拱手說道。「下官以為,親王舉兵,是為仁義之師,可為師出有名,當裡應外合。下官願修書一封,請符大人做為內應,更願往準葛爾部,說服宮永照成為此次勤王的最大助力。」
頤親王與準葛爾部不和是眾所皆知的事,宮永照更因此讓妹妹迎娶元春公主。戴權細思,捻鬚笑道。「可宮永照此人心高氣傲,不知姪女有何妙計?」
戴篠蒔微微一笑。「誘之以利,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脅之以威。」
「那就勞煩大人了。」頤親王喜出望外,拱手回禮,別有深意地向戴權望了一眼。戴權心領神會,也跟著說道。「姪女辛苦。」戴篠蒔眉歡眼笑,連忙推辭。三人勤王之事商議一番,才又談起戴篠蒔招安墨家姐妹的事蹟。一場宴席下來,賓主盡歡,水到渠成,雙方都稱得上各有斬獲。
三日之後,戴篠蒔以頤親王密使身分,出使準葛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