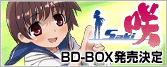算是我跟史丹共同創作的一篇。是慕大人治水的故事。
後半有出現Saki新角色,前半多為原創角色。
天剛破曉,位於海縣西南那條寬敞筆直石板道兩側的宅院便響起了些人聲。海縣位於四郡最北,路運樞紐,商貿必經之地,是河南最為繁盛的一縣。雖說這幾年來四郡洪災四起,災情頻傳,可海縣地勢偏高,物產豐饒,雖有災情,但也無法動搖其經貿地位。若說整個河南的富貴人家全聚在了海縣,那也是一點也不誇張。這些富商豪門中自然有些在朝中的人脈,於是前幾任縣令為了迎合這些大老爺們,便在本縣選個靜謐之處鋪了條大道,建得比官道還要更平坦寬敞,讓這些富貴人家住得安心舒適。
上官蕁牽著匹瘦馬,左右瞧了下,確認無誤才放膽敲響那道楮紅色的宅門。過了半响,那門才開了個縫,只見一個十來歲的小廝小心翼翼地探出頭來。「爺,哪找呢?」
「宛縣,上官蕁。」
這宅邸主人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往來之客自然皆非泛泛之輩。那小廝也是有眼色的人,見上官蕁一襲深色布衣,風塵僕僕,也不敢看輕,連忙招呼。「幾位老爺都在廳上,就差您一席。」
上官蕁拍了拍衣袖上塵土,笑道。「就差在下?哎,那我可是誤了你家老爺大事。」
小廝弓身哈腰,謹慎地栓了門領在前頭。這座府邸不大,跟其餘幾座院落比起來,那可是不起眼的多了。宅子裡只有簡單的假石山水,看上去挺質樸,可門柱窗櫺上都蓋了層灰,看來是久未有人居。從正門至前廳只有十來步的路程,主廳不大,約莫能容十來人左右,可這席宴卻來了二十多人。發言盈庭,二十幾個爺們湊在一塊高聲闊論,這邊談的是風流軼事,那邊談的是淫言穢語,一股酸臭的汗味和酒味混在一塊,使素愛整潔的上官蕁忍不住皺了皺鼻子。
「這不是上官麼?」
席末一人笑嘻嘻地朝她招手,那人身形瘦小,一襲海色直裾,頭帶軟巾,面色白皙,一雙劍眉透著凜然正氣,目光炯然有神,上官蕁一眼便認出這人是去年一甲狀元,派任海城縣令的辛沅。上官蕁與辛沅只有一面之緣,可放眼整個河南也就她倆女官,自然覺得有股親切感,於是也笑容滿面地迎了上去。「辛大人近來可好?」
「忙著呢,要不是這請柬,這時辰早該忙上了。」
「哎,整河南的縣令全來啦,就不知道司徒大老爺這回又有甚麼事兒。」上官蕁知道辛沅這人向來嚴謹,也不設防,見四下無人注意她倆,便低聲抱怨。「上頭派了個硬底子的人來治河,我想,說不準是為了這事。」
辛沅搖頭苦笑。「來的不就是慕大人麼。慕御使奉旨南下,首站海縣,這可教我這幾日忙得夠嗆的了。」
「原來是為這事。」
「可不是麼。」
兩人談得正歡,卻聽得席首一人高聲喊了句,司徒大人。廳上一時間全靜了下來,二十餘名縣令刷地一聲全站起身來,整齊劃一,七嘴八舌地說了些好聽的場面話。那司徒大人身著緋色排袍,身長八尺,虎體狼腰,濃眉大眼,看上去頗有威嚴,他大手一擺,廳內眾人立馬禁聲。
「我司徒道明今日請諸位前來不為別的,正是為御使奉旨而來一事。」他聲如洪鐘,佩上那燕頷虎鬚,讓他看起來不大像是朝廷命官,反而較像江湖人士。「前些日子,劉繹因慕祐祀而丟了腦袋大夥是知道。本來嘛,朝堂上的事輪不到我們這些個駐外文員說嘴,可這回辦的可是築堤的事兒。席上諸位都是河南官員,海城上下四郡築堤工事,雖然沒啥關係可也都牽連一二,御使此番南下,怕是來者不善。」
這司徒道明雖然是從三品的河南尹,可出身綠林,一身草莽氣。司徒家原姓石,祖父石軍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草莽英雄,救了當時仍是太子的先皇一命,因而賜姓司徒,還封了個軍職。司徒道明父親司徒元長與先皇情同手足,還和當今聖上生母筑妃攀上姻親關係,在朝廷裡也算得上是有些人脈。司徒道明年輕時在江湖打滾過一段時日,說起來也是交遊廣闊,後來因父親關係才硬是頂了個河南尹的官位。司徒道明這人雖不是個魚肉鄉民橫行霸道的惡官,可卻是個中飽私囊奢侈糜爛的貪官。在場縣令都知道他脾性,也知道他是怕這慕祐祀辦貪來了,於是紛紛說道。
「有司徒大人在,這小小一個慕祐祀,咱們還怕她不成。」
「就是,慕祐祀又怎地。河南這天高皇帝遠,別說是慕祐祀,就是天皇老子也管不著。」
「所謂御使還不就是狐假虎威麼?咱們司徒大人如此武藝,活脫脫就是個打老虎的好漢。更何況還只是隻紙老虎。」
逢迎拍馬,官場百態。席末的辛沅與上官蕁看著平日裡這些滿口聖人道理的官老爺們個個溜鬚拍馬、阿諛奉承的小人樣,默默端坐不語。辛沅生性耿直,自然是不喜歡這種曲辭諂媚、官官相護的骯髒事,上官蕁為官說不上多麼清正廉明,可也明辨是非曲直,有些士子骨氣,看不起這等巴結權貴的行為。她目光在與會官員裡轉了一圈,忍著笑意道。「今兒個可總算長了見識,看這滿屋子鼠輩,還真是教人噁心得寒毛直豎。」
「說甚麼呢,人家可是武松來的。」
「哎呀。」上官蕁側著身子,對辛沅擠眉弄眼。「我可不知道這打虎英雄還有養孌童這等癖好。」
辛沅抬頭望去,果見司徒道明身後站著一少年,脣紅齒白,面貌俊秀,楚楚可憐地像個大姑娘似的。她一時忍俊不住,哧笑出聲。「上官大人遠在宛縣,想不到連這等市井傳聞也知曉。」
上官蕁輕輕哼了聲。「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席上眾人還在高聲稱頌司徒道明,連大人英明神武天縱英才,萬夫莫敵無所不能這種話都說了出來,說得司徒道明臉上一陣青一陣紅。他輕咳兩聲,不耐煩地擺了擺手。「我找你們來,可不是來聽你們說這些個渾話的。這話平時說說也罷,如今真有要緊事談了,還盡說些廢話來耽誤老子時間,一群不中用的龜孫子。」
一夥人馬屁拍到馬腿上,又被他罵得面上無光,只能低著頭不敢說話。司徒道明看他們一個個低著頭的窩囊樣,更是氣不打一處來。「說啊,怎麼不說了,剛才不是說得挺歡的麼?怎麼老子要你們開口就個個像啞巴似的。你們這群豬腦袋,慕祐祀是誰?說穿了不就是皇上女人。人家那是你們得罪得起的麼?慕祐祀這女人骨硬,背後有人撐腰,氣燄正盛,一聽她要來,爺我急得頭髮都白了大半。就你們這些龜孫子還在那悠悠哉哉。」
他罵得解氣,才順了口氣,沉聲道。「你們這些狗娘養的做過些甚麼自個兒心裡明明白白,咱們都是同一條船上的人,老子這掌舵的倒了,你們也別想上岸。」眾人讓他罵得心虛,個個低著頭噤若寒蟬,只有辛沅、上官蕁和少數人仍面不改色。司徒道明環顧眾人,銳利的目光在幾個看上去無動於衷的人身上停了一停,才冷冷一笑。「今天要大夥來,是想讓大夥有個底,別給慕祐祀那毛丫頭給嚇住。強龍不壓地頭蛇,爺我怎會怕她一個慕祐祀?海城縣令呢?在哪?」
辛沅不疾不徐地站起身,朗聲道。「回河南尹大人,下官在這。」
「喔,原來是妳啊。」司徒道明臉色不耐地擺了擺手,隨口說道。「妳可得好好伺候著慕大人啊,這不用我教了吧。伺候人這事兒,娘們不就最會了麼?」席上除了上官蕁與辛沅二人外,皆是三、四十歲的大男人,他們聽了司徒道明拿辛沅開玩笑,也跟著百無禁忌地說起黃話來了。
辛沅氣得全身發顫,一股氣哽在喉頭,正想跳起來跟司徒道明這無恥之徒叫板,卻讓一旁的上官蕁給按住。「辛大人,忍人所不能忍,才能為人所不能為啊。」辛沅咬著下唇,臉色發白,看來真是氣得不輕。她狠狠地瞪了眼還在和旁人說些淫穢之詞的司徒道明,拂袖而去。
辛沅一走,上官蕁自然也待不下,她趕忙拉了馬追上去,苦笑道。「女子為官便是如此,辛大人還沒有自覺麼?」
「可我堂堂一甲狀元…」
「一甲狀元又怎地?」上官蕁微微嘆氣,見辛沅仍是滿臉憤慨,於是正色道。「在下早辛大人幾年入官場,也就厚著臉皮自認前輩。官場向來以男子為主,雖說我大璟開國百年,民風開放,女帝輩出,女子任官亦時有所聞,其中更不乏治世良臣。可漢人向來男尊女卑,根深蒂固,豈是幾個女官便可扭轉?聖上繼位以來,積極提拔女子,冉臻紫、慕祐祀入朝任要職,使女子地位大有改善,也都只是這一兩年間的事。司徒道明這人出身綠林,靠著家族關係撿了個三品官員,驕矜自傲,向來就瞧不起女子。更別說妳這硬脾氣,看來他是將妳視作眼中釘肉中刺了,辛大人,妳自個兒得小心點。」
「多謝上官大人關心。」辛沅誠摯地笑道。她年紀尚輕,於海城任職才一年餘,不僅人生地不熟,亦舉目無親。難得有人如此關懷自己,自然覺得心裡一軟,於是問道。「宛縣路途遙遠,上官大人剛到,想來也是疲乏得很。我府上不大,可空房是有的,上官大人如果不嫌棄,不如到府上暫且休息如河?」
上官蕁微微搖頭,面色愁苦。「我還得連夜趕回,宛縣災情嚴重,不可一日無人坐鎮。更何況,我也掛心宛縣情況,前些日子幾個村還爆發了瘟疫,幸得神醫傳人相救,病情才控制下來。哎,不說了,說了我便頭痛得很。改日有空我必當拜訪,今日就此別過。」
辛沅拱手道。「既然如此我也不強留,上官大人保重了。」
「保重。」
辛沅送走上官蕁後,不禁陷入了深思。縱觀大璟百年歷史,若要後世為當今聖上治下的璟朝下一個註解,辛沅想,那大概就是女人的天下。她曾有幸見過皇帝幾次,對於這位權傾天下的女子,辛沅不知道除了絕世無雙外,還能用甚麼詞語來形容。殿試那日,當今聖上身著金黃袞龍袍,腰纏碧玉帶,一十二旒平天冠下的豔美容貌,讓幾位士子忍不住看直了眼。辛沅紅著臉低下頭,望著案上試題,滿腦子裡卻想著,這皇上還真是欲綻似含雙靨笑,不醉花前為誰醉?如此美麗的女子,制政不出閨閣,而使天下晏然,行文修治,興邦安國,不讓鬚眉。辛沅當時初離家鄉,天大地大,不知該往何方,是這位用人唯才,不問出身的女皇帝給了她一線希望。慕祐祀時歷七品縣令,任期間寬厚愛民,治績顯著,後受聖上拔擢進京。入刑部,明察辨誣,釋冤無數,遷侍御史,敢言無諱,不攀附權貴,早被視為當朝傳奇人物。辛沅那年進京趕考,可說全是衝著對慕祐祀的那份敬仰,更望助聖上還民太平盛世。如今慕大人奉旨南下,要她如何不期待。
「大人!」一道尖銳焦躁的喊聲亂了辛沅思緒,她微微皺著眉,略帶不悅地喝道。「府衙重地,妳吵甚麼?」縣主簿祝小涓站在門外,委屈地扁著嘴。「人家是真有急事要稟報大人。」
祝小涓今年才一十八歲,少時喪父,幸得辛家救濟才能念書考秀才。辛沅自辛家出走時,祝小涓也跟著她離鄉背土上京赴考。辛沅任海城縣令,她也頂了個縣主簿的職。祝小涓這孩子秉性良善,聰明伶俐,生得也是眉細目秀,面貌清俊,可惜平時做事莽莽撞撞,糊里糊塗。就像現在,她早知辛沅最忌諱有人在縣衙大聲嚷嚷,衙內大夥知道辛沅脾性,也不敢犯她諱。這祝小涓被罰過三、四次才好不容易學乖,可這回,又犯忌來了。
辛沅見她那副委屈樣,也不心軟,只淡淡說了句,「有話快說,別在那嚷嚷。」
這平時就愛囉哩叭唆,吵吵鬧鬧的祝小涓此時卻扯著袖子,支支吾吾,嘴張得大大的甚麼也說不出來,最後好不容易才吐出了句。「慕御使正在堂上,說是要見您。」
辛沅愣了愣,一時間也反應不過來。「啊,慕大人。」她突然間瞪大眼,從椅上跳了起來往門外飛奔,嘴裡一邊嚷著。「妳平時冒冒失失我也不怪妳了,可慕大人…哎,妳怎麼能讓慕大人等呢這。」她氣急敗壞地奔向外堂,祝小涓平日甚少見自家大人如此失態,既覺得有趣又被罵得無辜,只好低著頭,緊緊跟在後頭。
辛沅匆匆奔到外堂,抬頭一望便愣了在那久久無法回神。只見堂上一人巋然屹立,直挺挺的背影光是望上去便覺孤高百尋。辛沅從來沒見慕祐祀本人,只聽過市井傳聞,而如今這位天下為之稱頌的慕大人就近在眼前,讓辛沅不由得抿了抿唇,屏住氣息。
辛沅尚未走近,那人便緩緩地轉過身來。慕祐祀白衣灼灼,一雙眸子艷艷如火,望得辛沅心裡一陣雷聲轟隆,驚天震耳。她瞪大眼,心裡愕然,想不到這慕大人竟如此年輕!慕祐祀容顏明澈,一雙眉目卻冰霜如雪,光只是站在那兒就如此威武凜嚴,讓辛沅忍不住激動起來,暗地捉緊袖子。這就是那淩霄不屈的慕大人啊!
辛沅敬仰慕祐祀已久,今日得以見本人,又為其氣度所折,只覺一陣手足無措,活像個沒見過世面的小毛頭。她故作鎮定,清了清喉嚨,朗聲拜道。「下官辛沅拜見慕御使。」
「我記得妳。」慕祐祀垂下眼簾,稍稍掩去那炙人的瞳色,略一思索,便朝辛沅輕淺一笑。「上屆一甲狀元辛沅。」
這一笑又讓辛沅結結巴巴了起來,彷彿一瞬冰雪漸融、乍暖還寒。初見本以為這慕大人是個不苟言笑,冷靜淡漠之人,卻沒想到這人貴為御使,竟沒甚麼官架子。又想到慕祐祀知道自己,心裡更又是緊張又是感動。敬仰的慕大人記得她,對辛沅來說就是一種莫大的肯定。她突然間便覺得自己這一年在海城受司徒道明打壓制肘,看遍官場百態,嘗盡各種苦處,都算不上甚麼了。她低垂著眼,輕聲道。「下官、下官想不到慕大人遠在京師,政務繁忙,竟然會記得一個小小的海城縣令,我真是、真是不知該怎麼說才好。」
「我看過妳的卷子。」慕祐祀卻沒有回答,她微微偏過頭,像是正回憶些甚麼似地說著。「妳頗有文才,空有抱負,卻缺乏眼界。」她頓了一頓,才續道。「那時皇上還提起過要提拔妳,可我說,還是讓妳先派任海城縣令去歷練一番。」
辛沅訝然,她猛然間想起上官蕁向她提過的,關於慕祐祀和皇上之間那些風風火火的傳聞來。可當她抬頭望見慕祐祀正望著她,神色自若,正氣凜然,便又覺得就算慕大人與皇上真有些曖昧那又如何?慕大人惠政恤民,為人正直,就是如此氣度才幹,便讓人不得不為之傾心。轉個念頭又想,若說當今聖上天下無雙豔,那這慕大人可就是願斫五弦琴了。
於是辛沅拱手說道。「下官當時年輕氣盛,一心為國,可眼界狹隘,不知官場險惡,人心難測。若不是任了海城縣令,怎會懂得百姓之苦,為官之難。」
「辛沅。」慕祐祀表情淡然,緩道。「妳可知我大璟開國至今,有幾任海城縣令因貪污受賄而鋃鐺入獄?」
「這……」辛沅似乎知曉慕祐祀想說甚麼,但還是低著頭道。「請慕大人賜教。」
「我告訴妳。前後共一十八任縣令因貪污而被抄家。」慕祐祀語氣平緩,卻字字鏗鏘,眉眼間正氣浩然,讓辛沅忍不住為之肅然起敬。「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辛沅,妳任職一年有餘,看到了些甚麼?」
辛沅明白慕祐祀話中深意,她噗通一聲跪倒在地,朗聲道。「下官於海城任職以來,眼見河南尹司徒道明以權謀私,隻手遮天,徇私舞弊,荼毒百姓,多少廉潔奉公的清官受到其打壓迫害,卻無處可申。當今聖上繼位以來,勵精圖治,整飭吏治,可我大璟盛世竟還有如此貪得無饜的狗官位居高位,實在令人憂心。下官懇求慕大人為民除害,滅此狗賊。」
「辛大人請起。」慕祐祀神色稍緩,淺笑道。「我正是為此而來。」
辛沅一聽,喜不自禁,又聽慕祐祀開口,「我特意來早,便是為了司徒道明這狗官。這幾日我會暗中探訪,希望辛大人可以多加配合。」
辛沅深深一揖。「下官自然鼎力相助。」
是日正午,慕祐祀換上棕色麻布長衫,淺紫色長髮用髮袋盤了起來,帶著輕便的行李離開了府衙。位於府衙不遠處的東大街是海縣最熱鬧的地頭,慕祐祀轉進巷弄,尋到一間茶館。館裡的客人不多,慕祐祀剛婉拒小二殷勤的招待,就看角落有位女子正對她招手。待慕祐祀坐定,那面容稍嫌病白,卻也目秀眉清的黑髮女子便不掩喜色地低低喊了聲姐姐。
慕祐祀也含笑回道,「好久不見了,慕月。叔父近來可好?」
慕月是慕祐祀的堂妹,慕祐祀自幼失怙,是慕月的父親將她一手帶大,與慕月情同姐妹。慕月的父親是蒲氏商號的帳房,蒲家世代為商,尤其武帝廢階級制度後,蒲家聲望扶搖直上,成為江南赫赫有名的商號。這當家的位子傳到蒲垣手上時,蒲垣膽大心細、目光深遠,更使蒲家成了江南第一大商家。蒲垣與慕家兩姐妹年紀相仿,自小一起長大,情同手足。當年慕月的父親拿出積蓄讓慕祐祀進京趕考,蒲家也幫了不少。這次慕祐祀南下查貪,本想託蒲垣從旁協助,但蒲垣在河南一帶也是頗有名望的人物,和地方官府多有往來,蒲家大喜又甫過,諸多不便,便請也在蒲家工作的慕月幫忙。
「父親身子硬朗,一直念著妳呢。」
「如此便好。那蒲垣有沒有說些甚麼?」
「有,她要我問妳,跟皇上還好麼?」
「……唉,這蒲垣。」早知道就別問了,慕祐祀嘆了口氣,默默拿起茶杯喝了口茶。
「她說這次修渠出紕漏,早想過會是妳下來,就擔心皇上不願放人。後來聽說真是妳,又說一定是妳這木頭自告奮勇說要來治河,一點都不管人家心情。」
慕祐祀差點被噎到,只能放下茶杯呵呵乾笑兩聲。這蒲垣,必定是還在對她沒能去參加她與佳織妹子的喜宴這事兒耿耿於懷。
「她還要我提醒妳,這次離京不要忙壞了,偶爾要給皇上捎個信,否則…」
「好了好了,咱們談正事罷。」天下能讓這鐵面無私的慕祐祀無奈嘆息的,除了遠在京城那人,也就只有那跟她自小一起長大的損友了罷。
「放心,我都準備好了。」慕月淡淡一笑,拿出個布包放在桌上。
原來蒲家正有在海縣開分號的打算,先前也曾以蒲氏商號名義發糧賑災,以打響名號。慕月此次便是以負責人的身份來海城探探狀況,讓慕祐祀扮作下人,跟進跟出,出入各式宴席。
商家在地方上做生意,自然得拜拜碼頭。蒲家雖然稱霸江南,可海縣畢竟是別人的地頭,慕月來開商號,不可避免得與官府通通聲氣。蒲家富可敵國,今次於海縣廣邀河南上下官員,自是少不得海城縣令辛沅,辛沅不知慕月目的,以為又是商家遊說,請了幾次,皆稱病不往,使慕祐祀不免又對辛沅這人多了幾分好印象。
慕祐祀與慕月還以瞭解海縣民情與買賣情況為名,請海縣各商號話事人吃了幾頓飯,席間不免談起一些官員秉性,聽來聽去,果然還是這司徒道明帶頭收賄。慕祐祀心裡有了點底,也想聽聽民情,於是與慕月二人特意扮作外地旅客,到街市酒館去探問這百姓對司徒道明評價。這一探聽可不得了,原來這司徒道明非但貪贓受賄,還挾勢弄權,勾結權要,明裡暗裡整掉不少清廉正直的父母官。餘下的官員人單勢孤,又讓司徒道明壓著,求訴無門,連百姓也對這情勢無奈的很。
明察暗訪數日,慕祐祀也對河南形勢掌握了個大概,她決意拿司徒道明開刀,於是心裡也有了些盤算。慕祐祀先是趁著大清早離城,直到午時才以御使身份風光入城。負責接待的海城縣令辛沅親自於城門口迎接,特地在府衙設宴為御使接風,順帶宴請江南各級官員,這其中自然是少不了河南尹司徒道明。
--
雖說是我和史丹共同創作,
但能者多勞,主要也還是她寫的,
她寫一寫不想寫就換我寫,她寫完我修,
我修完再給她修,大概就是這樣出來的。
其中的辛沅,祝小涓兩角,
早安放應該都看出來是新垣里沙和久住小春了,
史丹將此系列與她家裡那篇胡不歸連結在一起,
其他就都是自創角色了。
之前就覺得新垣在同人裡的角色跟加治很像,
現在能以這種形式讓她們Collabo真的很妙XDDDD
現在看來辛沅簡直就是個小慕祐祀wwwwww
最後慕月這名字我也很滿意>3<
還有哇哈哈和初心也出來了X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