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文藝節在中大中文系演講熱身的《作文解憂法寶店》,終於在教師節這天正式上市了!寫作解憂,是最簡單的生活法寶。發行前編輯問我,有沒有特別想要邀約的推薦人?我直覺跳出指導教授「林文寶」,好像透過一本又一本書,彎下腰,深沉地向老師說謝謝。
從文藝節在中大中文系演講熱身的《作文解憂法寶店》,終於在教師節這天正式上市了!寫作解憂,是最簡單的生活法寶。發行前編輯問我,有沒有特別想要邀約的推薦人?我直覺跳出指導教授「林文寶」,好像透過一本又一本書,彎下腰,深沉地向老師說謝謝。
正想為這本書和阿寶老師寫幾句感恩小文時,接到國樑老師電話。在台大中文系讀書時,我沒上過老師的課,我們卻因為共同受惠於裴溥言老師,結下一生情緣,可以在教師節這天,一起遙想師恩,有一種帶著古風的溫暖。
在我心中,國樑老師治學嚴謹,為人謙卑,卻又在教師節這天,感念教過他文選的啟方老師、教過他詩選的永義老師。寫於2月13日的悼念文,周年忌前正式面世;曾永義院士8卷、約270萬字的《戲曲演進史》全卷發表會,也在周年後的2023/10/14上午十點,在台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舉辦。準備和師母一起上山祭奠的國樑老師說:「10/10和12/25,曾老師和朱老師離開,那是一輩子都忘不掉的日子。」
每一次聽國樑老師講話,都像在巍巍高山中享受著柔軟清新的風。他這一生,給了很多學生恩惠;可卻總記著更多給予恩惠的老師。
珍惜和感恩,讓我們的生命,永遠滲出被珍愛的甜美。(秋芳,教師節小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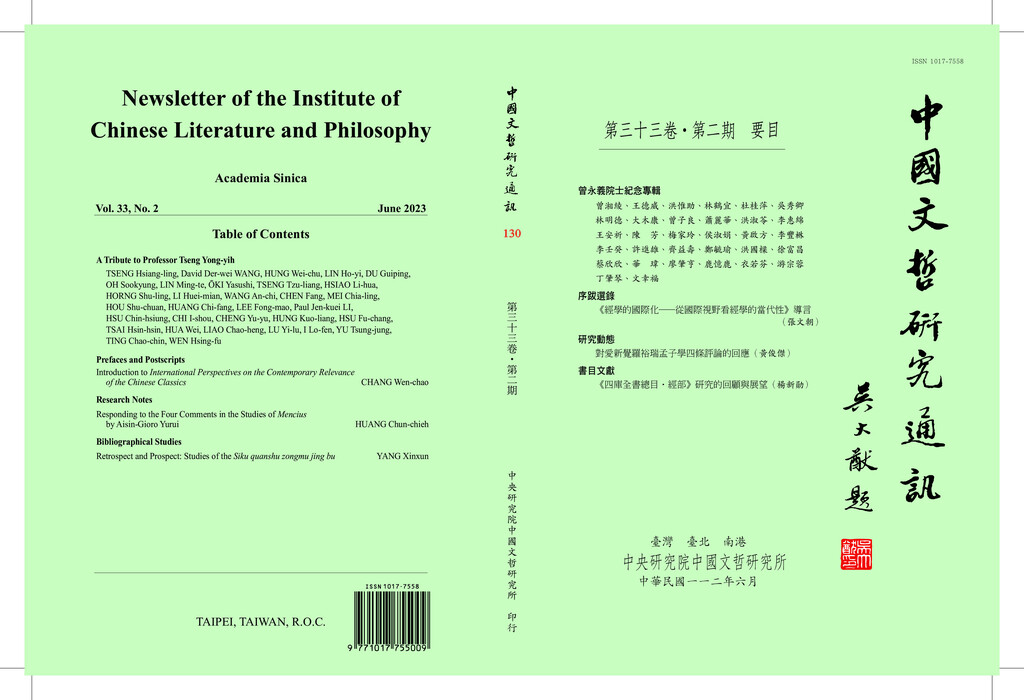 1.腹中書萬卷
1.腹中書萬卷
標題的首二句,是取自杜牧的〈送張判官歸兼謁鄂州大夫〉;後二句,是化用龔自珍的〈己亥雜詩〉。我覺得,這四詩句,恰可作為曾永義老師學問、生活、節操、為人的最佳寫照。
好多年前,有人問我說:「曾老師是酒党党魁,既要號令天下,又要教書、治學。他飯局那麼多,又必盡興而後返。照理說,應該沒時間做學問,而居然著作等身。我很納悶,不知他是怎麼做到的?」我說:「曾老師雖然喝酒,但也做學問。有些人雖然不喝酒,但也不做學問;其實也不是不做學問,是做不出學問。就如同李白斗酒詩百篇,但很多人一篇也做不出來。這固然是他天賦異稟,但也是後天努力。別人只看到他天天喝酒的表象,但沒看到他清晨三四點就在微弱的燈光下埋首苦讀、寫作。」
他又不解地說:「曾老師雖不至每喝必醉,但也幾乎到了醺醺然,清晨三四點怎麼起得來?」其實,這又是曾老師的另一種天賦異稟,他只要闔起眼來,就睡著了,所以能得充分休息。甚至搭乘電梯時,經常一進電梯就呼呼大睡,直到同行者說:「曾老師,△樓到了。」才猛然驚醒。在學術研討會上當主席,只聽發表人宣讀論文幾句,就鼾聲大作。發表人宣讀完畢,講評人也做了講評,他就即刻醒來,接著就對論文內容的得失,一一指陳,讓與會學者驚訝、讚嘆不已。其實,他是先把握住論文的幾個要點,然後就安心地夢周公去了。
曾老師性格豪爽又幽默。二十多年前,時任副總統兼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暨夫人連方瑀女士宴請學者。曾老師在宴席中乘著幾分酒興,對連先生說:「你是國民黨主席,我是酒党党魁,咱們平起平坐。貴黨有三民主義,本党有四酒主義;貴黨有五權憲法,本党有五拳憲法;本党還有飲酒八要、酒品中正,這是貴黨所沒有的。除外,貴黨有些制度還是跟本党學的。」
連夫人用質疑的口氣說:「學什麼?」
「本党有副党魁,而貴黨有副主席,就是跟本党學的。」曾老師一說,連夫人回:「我們有四個副主席!」
「本党有十四個副党魁!」曾老師接著又說:「說著好玩啦!來!來!來!喝酒吧!」
曾老師自三十四歲起即以党魁自居,因其深得飲酒三昧,又個性豪爽,胸次坦蕩,好結交天下英雄好漢,是以党員眾多,皆誠心擁戴。党魁每酒酣耳熱,即封官賜爵,因所封甚多,往往隨封隨忘。有人若得党魁封賜,就覺得無比光彩,酒友相聚,每以誇稱於酒党中之地位為榮。
2.身外酒千杯
某年,世新大學梁世武教授宴客,吳敦義副總統、党魁、陳學聖立委、成天明教授和我等人都受邀。党魁當場封吳先生為第十二副党魁,吳先生大樂。離席時,吳先生以手掌輕拍党魁肩膀說:「党魁,下次請你吃飯。」
又某年,党魁赴北京開會,會畢召集党員餐聚。党魁興起,對某先生說:「封你為北京總督。」旁座另一位先生說:「報告党魁,你不是封過我當北京總督嗎?」党魁一時愣住,略顯尷尬,隨即又說:「你已升為中常委了!」該先生唯唯稱謝說:「謝謝党魁!」
曾老師才華橫溢,常即席賦詩,不假思索。2008年某日,曾老師宴請世新大學牟宗燦校長,陪客有齊益壽先生和我等人。宴畢,曾老師、齊先生和我,轉至台大交誼廳「筑軒」唱歌同樂。巧遇黃仁清先生及林錫龍、周美華、周美美、王美玉等人。
黃先生是越南僑生,與前教育部長毛高文先生為台大化工系同學,畢業後隨當時經濟部長趙耀東先生至越南,擔任紡織廠工程師,後因眼睛病變而慢慢失明,遂放棄越南事業,返台定居,因喜愛音樂,轉而從事歌詞歌曲創作,遂成大師。其創作歌曲達千餘首,皆為膾炙人口的名曲,如〈財神到〉、〈情緣〉、〈小詩〉、〈夏之旅〉、〈鄉愁〉、〈情書團〉、〈長江水〉、〈君無愁〉、〈煉獄兒女〉、〈期待再相會〉、〈原野牧歌〉、〈碧雲天〉、〈燃燒吧火鳥〉、〈蝸牛的話〉、〈躍馬中原〉、〈又見阿郎〉、〈異鄉人〉、〈父與子〉等。毛先生在公開場合若應邀唱歌,必唱〈小詩〉,也是其唯一歌曲。
我擔任世新中文系主任時,開設「應用中文講座」課程,含「新聞寫作」、「編輯與採訪」、「廣告文案」、「歌詞歌曲創作」等單元,其中「歌詞歌曲創作」即由黃先生擔任,每次上課皆由其女兒黃雅慧女士陪同,並擔任教學助理。當曾老師、齊先生和我轉至「筑軒」後,巧遇黃先生,與之閒聊。黃先生說:「曾老師,你來寫一首詩,我可以為它譜曲。」曾老師說:「真的嗎?」黃先生說:「沒問題!」曾老師目光掃過旁座的美華、美美、美玉三人一眼,因三位的名字裡都有一個「美」字,於是突發靈感,即席寫了一首〈三美圖詠〉:
美人圖,美如花,美美、美玉、美華。三美瑤台畫,三美欲何家。
春來秋去風滾沙,落日黃昏尚彩霞。青山綠水三分酒,明月清風幾盞茶。
成敗英雄多少話,古今如夢何所差。愉快人間有爾我,何如相顧笑哈哈。
歌聲高亢繞梁柱,世事管他亂如麻。但將三美作良伴,劉阮不辭到天涯。
美人圖,美如花,美美、美玉、美華。鼻如梁玉,唇恰合歡,眼中有他。
有煙有夢不須假,展翅大鵬意轉加。直到九霄雲霧裡,方識三美美如花。
詩後題記:「2008‧8‧6夜十時半酒酣於台大筑軒。」又附記:「是夜,宴牟校長宗燦於寧福樓,偕益壽、國樑至筑軒,遇美美、美玉、美華、錫龍,酒酣歌暢,油然賦〈三美〉。」同時寫了兩張,一張交予黃先生,另一張由錫龍收存。幾個月後,曾老師、黃先生和我又於筑軒巧遇,黃先生說:「曾老師,你寫的詩太難太難了,我實在譜不出來!」
3.肝膽照明月
曾老師的為人,豁然大度,豪氣干雲,又深情重義,溫婉細膩。十多年前某天,曾老師到台大福利社理髮,當時有位鄭姓校車司機阿富也在該處理髮,當他先理完髮後付賬,連同曾老師的部分也付了。事後,曾老師對我說:「阿富為我付了理髮費,真不好意思!我要請他吃飯,你找一些朋友作陪。」
他素有一諾千金、言出必行的性格,過若干天後,又問我:「請阿富吃飯的事,安排得怎樣?」後來在水源會館請了一桌,場面溫馨。阿富付的理髮費200元,曾老師請的一桌5000元。就曾老師看來,200元和5000元的重量是一樣的,都是滿滿的情義。阿富雖然只是個校車司機,但曾老師認為人品、格調有高低,身分、職業無貴賤,教授和司機是平起平坐的。他的戲曲創作達十八種之多,其重要創作主題之一,即是「情義無價」,而這也是他奉守不渝的為人、處事原則。
曾老師對事物的思考,多半「務舉大綱,簡略苛細」,但對有些事,也往往能明察秋毫、深思熟慮。他有位素所尊敬的「朱大哥」朱炎先生,曾任中央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後改名為「歐美研究所」)、台大文學院長、國科會副主任委員等職,是位風骨凜然、剛正不阿又極為感性的學者。朱先生與我在台大共事時,因性格相近,故而相知相惜,每週總要聚會兩三次。
一九九九年,我在台大中文系申請退休,朱先生知道後感到不捨,不准我退,我說:「我二月就已提出申請,不可能改變了。」朱先生說:「那我留在台大還有什麼意思?」也就跟著在六月赴波蘭華沙參加國際筆會第六十七屆大會前匆匆提出退休申請,後來轉任逢甲大學講座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二○○三年某天,朱先生對曾老師說:「我想寫一篇文章〈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國樑抱我情〉。」曾老師問說:「怎麼回事?」朱先生娓娓敘說始末。事情是這樣的:二○○三年九月,朱先生因腰椎壓迫性裂折,我開車載他去讓一位摯友謝先生幫忙處置。謝先生是祖傳四代的傷科名醫,有「神醫」之稱,為人溫厚而有俠義之氣,又雅好文學,久聞朱先生大名,貼藥膏堅持不收分文,且從此之後,均於三節送禮,直到朱先生過世為止。
朱先生的臥室在二樓,看完診後,我載他回家,並抱著他上狹窄的樓梯到臥室。我們相互配合得天衣無縫,他雙手環繞住我的脖子,我一手勾住他的腋下,一手托住他的大腿,一階階走上二樓,如此前後兩個月之久。朱先生對沒有服藥而能迅速恢復,亦覺神奇。曾老師聽過之後,深受感動,但他說:「國樑在學校頗遭人忌。你的名氣大,如果寫了這篇文章,反使國樑增加困擾,愛之適足以害之!」朱先生覺得言之有理,也就作罷。
數十年來,朱先生和曾老師都對我呵護備至,是進入我生命中,讓我感念不已的師長。我從台大退休轉任世新中文系後兩年接任系主任,再兩年成立研究所,曾老師為助我一臂之力,從台大提早退休轉至世新,使世新中文系聲譽鵲起。
4.亦俠亦溫文
曾老師對人物的評騭,是揚善但不隱惡。他秉持知識分子的良知和風骨,具有嫉惡如仇、直言不諱的性格,常於詩文中諷諭時政,褒貶人物,雖達官貴人,亦不稍假辭色。我曾寫過一篇〈酒党党魁外傳〉,原載於《國文天地》,裡面有這樣一段話:
台灣當年某政黨執政時,曾努力推動「去中國化」,由某單位召集學者研議。党魁當場慷慨陳詞:「文化是延續的,不是你想要,它就來了,你想不要,它就去了。如果要去中國化,除非叫某某人不姓某,民間不拜關公、媽祖。不學無術的人還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不學而有術。你們就是一群不學而有術的人。」
發言既畢,會場有某官員,走近党魁身旁,說:「曾教授,你能把你的意見寫下來嗎?」党魁說:「有何不可?拿紙來!」於是振筆疾書,寫畢,把紙丟給官員,接著說:「我要喝酒去了。」
這是何等膽識!其言詞又何等嚴厲!我在文中寫說「除非叫某某人不姓某」,是考慮曾老師多年來頗受「党魁」盛名之累,所以含蓄其人。後來曾老師把它收入《酒党党魁經眼錄》中,改成「除非叫陳水扁不姓陳」,原汁原味,還原當時場景,這已是孔子《春秋》「一字之貶,嚴於斧鉞」的筆法了。該文又接著說:
又某年,屏東東港舉辦「鮪魚季」宣傳活動,敦請當時最高權貴致詞,党魁與若干友人亦應邀出席,並比鄰坐於前排。党魁告諸友人:「兄弟們!稍後若有情況,請聽我『向左看』之口令行事。」眾皆允諾。當最高權貴致詞畢,走下講台,自右起,與前排來賓一一握手致意,依次將至党魁,党魁即以軍中執行官之口吻發令:「向左──看!」全排友人隨即掉頭左顧,該權貴自覺無趣,迅即轉離。
所謂「當時最高權貴」,其人為誰,不言自喻。党魁之所以敢如此對待「當時最高權貴」,當今之世,不知還有何人?
方今世道陵夷,是非淆亂,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小人當道,群魔亂舞,曾老師所樹立的典範,不知還存在天壤之間否?望風懷想,不禁悵然!
----2023年2月13日於士林劍潭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