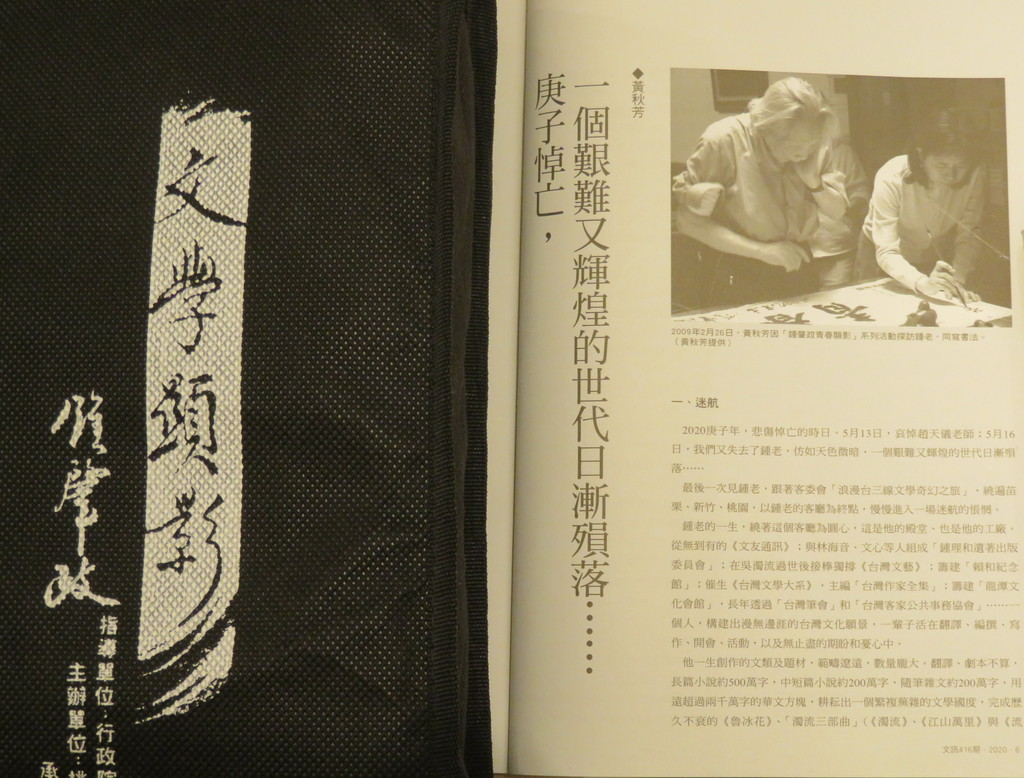 ☆發表於《文訊》416期,2020年6月號☆
☆發表於《文訊》416期,2020年6月號☆
1. 迷航
2020庚子,悲傷悼亡的時日。5月13日,哀悼趙天儀老師;5月16日,我們又失去了鍾老,仿如天色微暗,一個艱難又輝煌的世代日漸殞落……
最後一次見鍾老,跟著客委會「浪漫台三線文學奇幻之旅」,繞遍苗栗、新竹、桃園,以鍾老的客廳為終點,慢慢進入一場迷航的悵惘。
鍾老的一生,繞著這個客廳為圓心,這是他的殿堂、也是他的工廠。從無到有的《文友通訊》;與林海音、文心等人組成「鍾理和遺著出版委員會」;在吳濁流過世後接棒獨撐《台灣文藝》;籌建「賴和紀念館」;催生《台灣文學大系》,主編「台灣作家全集」;籌建「龍潭文化會館」,長年透過「台灣筆會」和「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一個人,構建出漫無邊涯的台灣文化願景,一輩子活在翻譯、編撰、寫作、開會、活動,以及無止盡的期盼和憂心中。
他一生創作的文類及題材,範疇遼遠,數量龐大。翻譯、劇本不算,長篇小說約500萬字,中短篇小說約200萬字,隨筆雜文約200萬字,用遠超過兩千萬字的華文方塊,耕耘出一個繁複蕪雜的文學國度,完成歷久不衰的《魯冰花》,「濁流三部曲」《濁流》、《江山萬里》、《流雲》,「台灣人三部曲」《沉淪》、《滄溟行》、《插天山之歌》,以及從《川中島》、《戰火》到最後成為懸念的「高山三部曲」,透過大河小說體系,透露出黝暗的歷史壓抑中,無法折曲的生命信仰。
出入這個客廳,很多年了,鍾老在這裡等待、在這裡張望,在這裡經歷過悲傷憔悴、也收納過燦爛輝煌。一本又一本會客簿,記錄著只有他才能深刻擁抱的記憶。曾經,在這棟房子改建時的短短時光,他借居女兒家,我們在那迥異於古老生活風情的現代大樓裡,談起客家兒歌中的純真,腦子裡還旋起他閉上眼睛、張開翅膀,模仿著「目睡鳥」的頑童神情,日子過著過著,重新回到這個客廳,會客簿沒了,記憶地圖慢慢糊去,他能夠依循的細路,不知道分歧到哪裡去了?
深受台灣文學南北兩大重鎮葉石濤和鍾肇政親自引領的彭瑞金,率先進入客廳,像陽光瞬間照進陰暗,鍾老一聲輕喚「瑞金」,就耗盡了「現實能」,然後就迷失在黝暗昏色中,一下子對著瑞金老師喚:「你是陳萬益?」、一下子又對著紙張上大大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反覆:「彭瑞金」、「陳萬益」,這是台灣文學史上,分別從不同視角深入整理過他的人生成績的人。 2. 設色
2. 設色
當鍾老看著我的名字,迷航在模糊歲月中,萬益老師曾聽鍾老讚許過那個「比客家妹仔還要客家的福佬妹仔」,用閩南式的「小妹」替代客家式的「妹仔」,刻意提醒他的記憶:「就是小妹啦!」
「噢,噢!」他開心地笑了起來,其實,我知道他沒有想起來,只是因為衰老之後,他特別眷戀起青春鮮嫩時所有的美好。
他在相親第七次時,終於「成功」地與同鄉三坑村張九妹結婚。鍾肇政27歲,應《自由談》「我的另一半」徵文寫出生平第一篇散文〈婚後〉,九妹成為他文學生命的起點;九妹為他生養五個子女,養大豬公,盼著賣掉大豬公為他打造一個書房,成為他文學的支柱;而後在九妹的溫柔又堅強的照顧中,活出他自己喜歡的生命樣貌,我很難忘卻九妹那美麗的側影,輕輕吐露著一生的牽掛:「佢哦,冇管別樣,脈介都冇要緊。吃飯看字,痾屎看字,落大水,屋肚漏水,佢脈介都不識愁。」
最初只能偷偷藏著吳濁流文稿的鍾老,應該想像不到,這條寂寞的文學路,一直走一直走,竟然走出一條康莊大道。長年奔波的鍾老,慢慢成為聚光焦點,同時也越加感受到體能崩解的悲哀,千百年前杜牧題寫的「無媒徑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的惆悵,罩向鍾老身在「市朝」卻擋不住雲林蕭草的荒疏衰頹,2003年,借由書寫《歌德激情書》的親密熾烈,成為他對青春的著魔召喚,宛如一輩子埋在書案,真實人間的紅塵煙火,他都來不及參透。
他一生的愛情,都悶燒在寧靜的生活裡。九妹晚年坐在輪椅上,等著鍾老為她熱餐時,又感激又心疼,紅著臉,說不出多少纏綿和悵惘:「佢就愛看HBO,哪會煮食?」
鍾老八十歲以後才進廚房,如果能夠,九妹應該希望自己可以照顧這個大孩子一輩子吧?2011年,九妹離開後,地方講座和導覽,開始著墨這個浪漫文青從小到大的暗戀、初戀,和各種來得及或來不及開始的「朋友超過,戀人未滿」的粉色樂章。在我看來,鍾老的粉色,只在幻異世界編織揮霍;真實的人生,只剩下黑色,在晦暗黏稠中奮鬥;因為各種文學嘗試的安慰和文友間的相重相惜,慢慢抹出這樣憂鬱、又這樣深邃寬闊的藍色;隨著解嚴,台灣的民主運動風起雲湧,怒張的紅,成為他的主色;也因為爭取到的位置變寬了,可以做的事也變多了,鍾老的生命,轉化成無邊無涯的暖黃,匍匐在「台灣」、「文學」、「客家」這每一條岔路上的每一個人,幾乎都受到他的庇蔭;最後,變成白色,一如曙色羽翼,領著我們張望天際,翱翔,我們將一起看見,島嶼天光。 3. 焰彩
3. 焰彩
回想起鍾老最後一抹淡淡的灰,還是在這個他一輩子旋著轉著的客廳。瑞金老師低聲吩咐我,把書名寫下來,提醒已然聽不見的鍾老,我寫了他特別喜歡的《台灣客家生活紀事》,延威拿出《鍾肇政的台灣塑像》,鍾老捧著書,認真看了看,竟誠懇向我道謝:「你為我寫了一本書,是嗎?感恩,感恩,我會好好拜讀。」
他反覆看著我的名字,慢慢念著「黃,秋,芳」三個字,每一抬頭看到我,就嚇了一大跳,拼命搖著頭:「不像,不像。」;再唸名字,又嚇了一跳,這樣反覆搖頭說:「不像,不像。」;直到愛亞姐忽然發現:「秋芳一直是長頭髮,現在剪成短頭髮,他不認得了。」
這就是鍾老啊!一直活在自己的想像世界。「浪漫台三線」輕旅行的尾聲,在抵達三坑生態公園前路過老街,想起師母講了近十年,想回三坑娘家看看,山路曲折,我不敢開車,後來找了個超強的朋友當司機,陪著鍾老和師母靜靜走了一下午。
那是多麼簡單卻又不易完成的願望啊!像鍾老這一生,蓬勃生氣,卻又窘促不安。
生命的負載,為他們這一代加上太多綑縛。現實是一張拼圖,文學是一張拼圖,過去,現在,未來,糾纏著好多拼圖,不同的形像、不同的渴望,反覆糾纏著,遠在二十年前,鍾老就常常陷入記憶中,反覆重述一件又一件往事,慢慢在重建人生劇本,有太多悲傷,他需要遁逃,需要改寫,九妹說,晚年沒事,他習慣埋在HBO舊片裡,讓自己從太多混亂的現實拼圖中抽離。
在很多年很多年不涉現實生活、完全由妻子打理的安穩人生裡,忽然又活進一個素樸純粹的淡灰人生。談著說著,他突然以手摀臉嘆:「目汁在眼睛打轉,我不讓它滾下來。恁多老朋友來看我,我忍都忍不住啊……」
「鍾老為什麼流目汁呢?」我在紙面寫字問。有人笑著說:「說不定一寫好,他已經忘記他哭了。」
鍾老的眼淚來得快去得更快,大家都被逗笑了,我卻特別的悲傷。想起鍾老以前常問我:「我同年有來嗎?」
父親和鍾老同是1925年生,他們互稱「同年」。父親一直到離開前都神識清楚,儼然一生都是我家的國王;鍾老卻活在悲傷的人生劇本:「我被丟在這裡,一直都沒有人來看我。」
他用客家話反覆對不同的人叫「阿板仔」;對小野的名字思之再三,好像沒有印象,卻在看到小野微微白髮時,吃了一驚:「你長大了!」
客廳的笑聲炒至高峰,我卻悲歡交纏。傷心的是,我在鍾老身上,不斷拼貼對著他和父親同年一路走來的辛酸艱難;微微歡喜的是,終於,他也卸下負擔,只有靜靜流淚,不再需要扛著台灣文學龐大的恐懼和驚惶。
那時的我們都沒想到,不到半年,他就永遠卸下負擔了。再也不需憂心,再也不會流淚,再也用不著戰戰兢兢,艱難的,一步一步突圍。就在這抹淡灰背景裡,還會有更多年輕的孩子們接棒,在「台灣」、在「文學」、在「客家」的每一條岔路上,即使天色微暗,仍然堅持,塗抹出艱難又輝煌的的焰彩。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