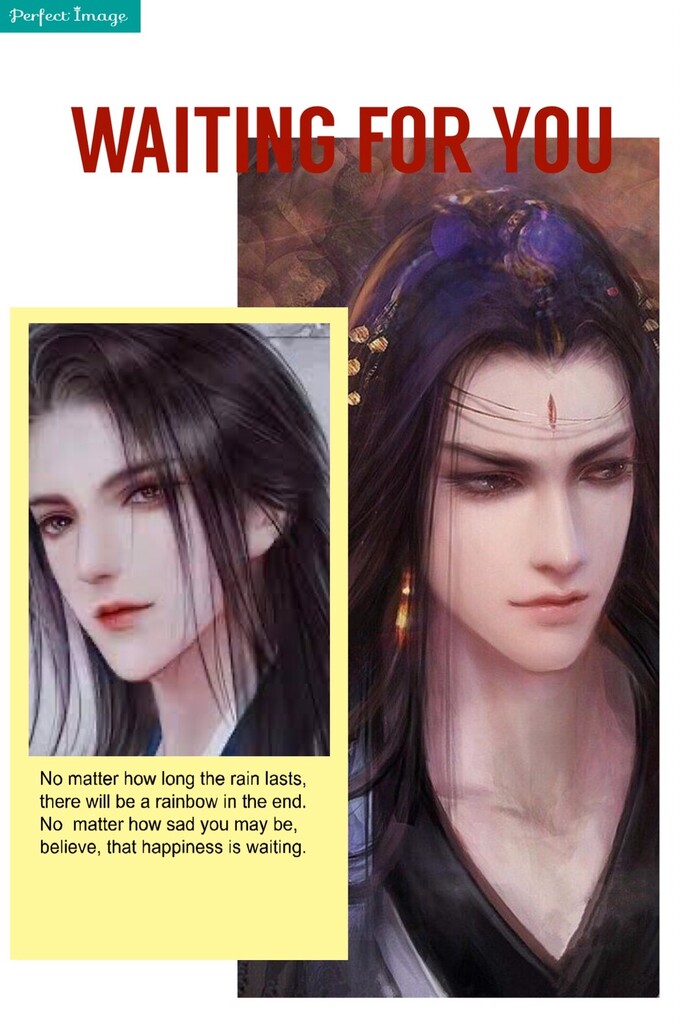
三個月煉獄般的囚禁,阿言拖著殘破的身體,重獲自由。
他的狀況太慘,不敢馬上回到癸深身邊,找個隱密的地方將養了三個月,才回到城主殿。
因為時不時發作的噬心散,還有身上諸多傷疤,擔心癸深發現,拒絕了癸深兩人住在一起的安排。
這件事,讓癸深不快意了許久。
然而,阿言人微言輕,也沒有自己的人脈,他所能依靠的只有癸深一人,再這樣下去,他沒法查出癸深身邊的奸細究竟是誰。
不得已,阿言誘惑了癸深,兩人重修舊好。
癸深曾在兩人溫存後的深夜裡,一次次疼惜地,撫過阿言身上的傷疤,問過他身上的傷是怎麼來的。難道寂海的勞役真的如此兇險?受傷的當下,不知疼成什麼樣子。
阿言在寂海時,捕鯨的工作雖然累,受傷的機率卻不大,他身上的傷都是癸辰的爪牙們搞出來的,然而阿言隱瞞了這點,只說是捕鯨時,被水下的礁岩割傷的。
問了幾次,都是同樣的說詞,癸深便信了,也不再追問。只說要找全忘土最好的大夫,替阿言去除傷疤。
阿言笑著搖搖頭。癸深的身上也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創痕,兵器造成的,那是戰士從戰場上得來的徽章。阿言說我疼過,少爺疼過,咱倆就扯平了。
癸深笑說,這種事哪有扯不扯平的,然後便熱情地擁抱了阿言。
帶著人生際遇的傷,他們都已不是當初白紙一樣的懵懂少年。
阿言的思緒拉回現實。在黑暗中,有一陣腳步聲破風而來。
在已失去門扉的門前,背著月光而立的暗影,那是癸安。
「癸安大人,您終於來了......」
阿言不及待地想拿到解藥,扶著牆站起來,朝癸安蹣跚走去。
「解藥呢?快給我吧。」
「給你?為什麼要給你?你又給了癸辰大人什麼?」
「我......我上次殺了癸濯後,少爺就不大信任我,就連侍衛的職位也丟了......沒法接近少爺......」
「那是你的事。不要忘了你當初答應了什麼。像你這種什麼都查不出來的蠢貨,還妄想癸辰大人給你什麼?」
說完,癸安拂袖便要走。
「等等,癸安大人......」
阿言不知道錯過了這回,會不會再也見不到癸安。能捨才能得,一咬牙,他決定告訴癸安一件無關緊要的,關於癸深的事實。
癸珞是他的朋友,就算癸深疏遠他,他還是能從癸珞身上得到癸深的消息。
「兩天後,少爺會前往玄武城西南五十里處的景山陽坡視察。」
「景山?去那裏做什麼?」
「興築城寨,景山可以眺望南荒邊界。」
「這樣一來,玄武城就能獲得南荒動向的第一手資料。知道了。」
癸安笑道。
「景山那裏山道兇險,保不定從山上滾落巨石,或者腳下棧道陷落,這都是可能的事。」
「你說的可是真的?你知道我是有方法驗證真假的。」
癸安說的驗證真假,大概就是去問癸冽吧?
阿言冒險告訴他這樁無關緊要卻可以好好利用的訊息,就是想先騙得解藥後,再去勸癸深改變行程。
這樣不管他們想在景山上對癸深做什麼,都只能落空。
這本是雙全之策。
本來不想拿出解藥的癸安,覺得這次的阿言還算上道,把手伸進了襟前內袋裡,看樣子是想掏東西。
阿言專注地與癸安虛與尾蛇,卻沒注意有其他腳步聲,也朝這幢廢屋慢慢靠近。
「阿言。」
一陣熟悉的聲音,從癸安背後響起。
阿言瞪大了雙眼,難以置信,站在門外的,不是癸深卻又是誰?
癸深派了兩支人馬,去監視癸冽和阿言。
癸冽那裏一直沒有動靜。可下屬通傳,今晚阿言行跡有異。
癸深不願意相信,也不想冤枉了阿言,他要親自看見。
幾名侍衛領著癸深到時,正好聽見阿言,向癸安洩漏了癸深兩天後的行蹤。
癸安發現不對,當下使出行雲術,從廢屋的縫隙裡跑了!
一名侍衛追了上去!
癸深和阿言,隔著門框相對。
癸深背對著月光,阿言竟看不清楚他的表情。
「為什麼?」
癸深的聲音顫抖。背叛的人,是阿言,他無法自持。
阿言面色慘白。癸深親自撞見他和癸安聯絡,還有沒拿到解藥這件事,讓他心裡亂成一團!只能一直語無倫次地為自己辯解!
「少......少爺......您聽我說,不是您想的那樣,我是有苦衷的!」
「就像我之前跟您說的,我不是叛徒,癸冽才是!您一定要相信我!」
以他今晚所見的人,還有談話的內容,阿言是奸細,就是板上釘釘的事。
但在此關頭,阿言還在繼續栽贓癸冽。
就像癸冽說的,除掉了他,就能削弱自己的勢力。
他沒有辦法再相信阿言。
「你這麼說,是還想讓我殺了癸冽,好自斷雙臂,是嗎?」
癸深紅著眼。
「阿言,我已經知道了,你不必再說這些,上趕著證明你是奸細......」
可阿言知道大勢已去,他大概沒有辦法除去癸冽了,他一己之身不要緊,死就死了,可癸冽不能留!
「少爺......我向你保證......我用性命向您保證,癸冽是奸細.....一定要殺了癸冽!」
「您可以不相信我.....但您真的不可以相信癸冽......」
阿言不斷地重申癸冽是奸細的事實,然而今晚的一幕幕,讓癸深已經無法再相信他,甚至連癸深身邊的侍衛們,聽見阿言對癸冽大人「莫須有」的指責,都感到憤怒!
癸冽大人無數次和他們一起出生入死時,阿言人在哪?
憤怒的侍衛們,建議將妖言惑眾的阿言就地正法。但癸深雖然寒心,要讓他殺了阿言卻也不忍,他一時想不到該怎麼處置阿言。
「把他帶回地牢關起來!」
癸深令下,拂袖而去。
基於眼前的事證,癸深對阿言已是輕判。
可對阿言來說,他全身全心忠於癸深,就算失去生命也毫不在意,癸深怎能這樣對他,怎能不信他?
看著癸深決絕的背影,阿言眼眶一熱,模糊了視線。
那個他死也要去的地方,終究是到不了了啊!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