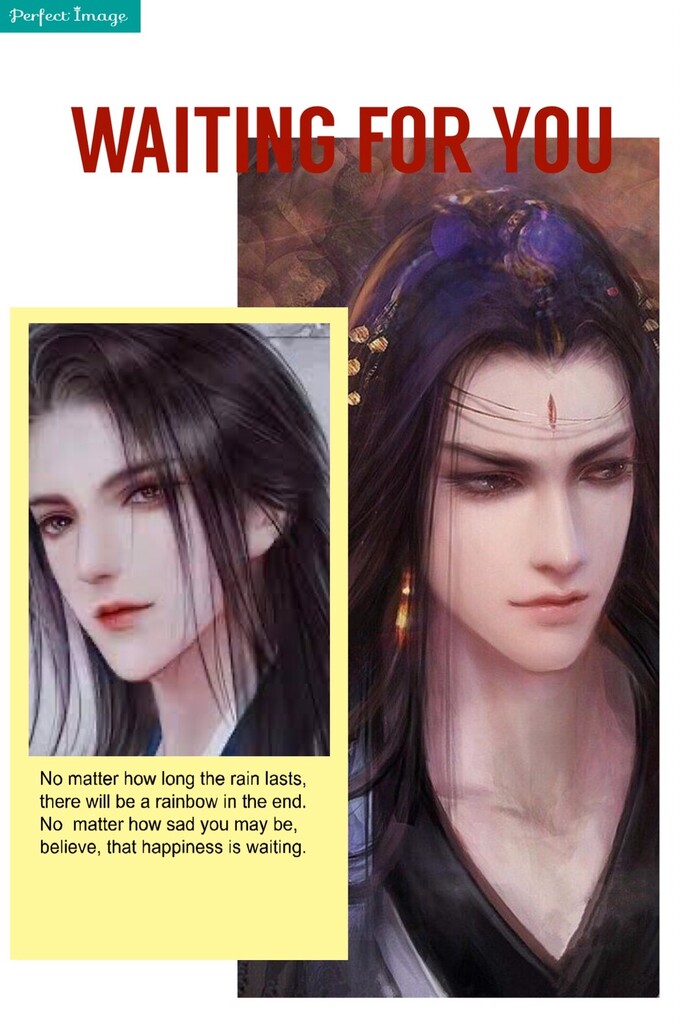
從阿言的房間裡出來的時候,癸珞的思考一片空白。
她沒想到睽違的這半年來,阿言遭遇了那麼慘烈的事。
她想把阿言對她說的一切,找機會告訴癸深。她相信癸深一定會幫阿言解決的。
但阿言阻止了她。
「現在最重要的,是找出少爺身邊的奸細。癸珞,玄武城歷代城主,除了任期未滿就辭官遠去的癸明大人,其餘幾乎都死於非命。我真的很擔心。」
阿言說的是實話。葬在共工之柱下的癸氏歷代當主,沒有一個人是壽終正寢的。
忘土貴族都來自神州四凶之後,血液中暴戾好鬥的因子不曾安生過。
「我身上中的噬心散,放眼忘土群醫束手,只能壓抑,無法根治。所幸有藥,我現在還能撐下去,在我倒下之前,一定要確保少爺的安全。如果讓少爺知道我的事,他一定會分心自責,更會給那些野心分子可趁之機。癸珞,別跟少爺說,就算是幫我,好嗎?」
阿言說這些性命攸關的事時很冷靜,彷彿他已沙盤推演過無數次該怎麼做。
「珞總管。」
恍神地行至前院,一陣熟悉的聲音,將癸珞的思緒喚了回來。癸珞一看,是伺候癸深茶水的霧兒。
「是妳啊霧兒。貴客都安置好了嗎?」
「是啊,我正給貴客送酒水去。珞總管看上去不大開心,是有什麼事嗎?」
霧兒端著酒盞,問。
「沒什麼……」
正要與霧兒擦身而過,想到什麼似地,癸珞又回頭道。
「對了霧兒,妳說過,把妳昏迷在床三年的哥哥治好的……那位神醫,叫什麼名字,住哪,妳可以告訴我嗎?」
癸珞想起閒聊時,霧兒曾經說過,她哥哥打獵時,從山崖上摔下,失去意識臥床了三年,那位大夫施了三次針,開了十帖藥,她哥哥竟能下床走動了,街坊鄰居都覺得這簡直是神蹟。
「喔,他叫杜仲子,我是知道他的醫廬,就在禺京園東北方的半里坡上,不過,他常常出去雲遊,專程上門,不一定能遇到他。珞總管身體不適嗎?我請哥哥去他的醫廬看看。」
霧兒倒很熱心。
「好,麻煩妳了。」
雖然知道噬心散這種毒目前還沒法根治,但凡事無絕對,自從癸潤死後,阿言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就算只有萬分之一的機會,她都要試試。
第二天早上是阿言的班,陪著癸深送走北辰殿使者後,少將府來了人,說癸冽在府中擺下筵席,今晚宴請癸深和阿言,希望城主能賞光。
癸深對阿言笑說,我這兄弟就是實心腸,說了要為你設宴洗塵便真的擺下筵席了,晚上咱們一起去。
阿言微笑點點頭。
今天癸深要去城郊旱田視察寒害的農損,阿言陪著他去。
其實北原很冷,哪裡都不適合耕作,但癸深找人從山上引了地下溫泉水前來灌溉,他興高采烈地告訴阿言他是怎麼施工的,阿言對癸深的點子很是欽佩,覺得不愧是我的少爺啊,眼中都要冒星星了。
那些農民看到癸深都很高興,城主長城主短的歌功頌德,又說癸深大人是最關心他們農民的城主了,不像其他城主都只知道打仗。
「北原剛剛復國,重要的是休養生息,讓百姓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比南征北討重要多了。」
癸深春風得意地對阿言道。
「在城郊南方,我還開闢了溫泉魚池,讓南荒的魚種在咱們北原都能生存。」
「嗯,少爺喜歡吃魚。」
阿言想起他親手熬的鱸魚粥,癸深每次都吃光。
「阿言還記得。」
不顧他人眼光,癸深拉住阿言的手,登上他的雪熊坐駕。
「走,咱們去溫泉池看看,順便撈兩條魚,明早我要吃阿言的魚粥。」
「好。」
如果可以,他願意一輩子替癸深熬粥。
但願他能有這個福分。
「但是現在……我想先吃你。」
雪熊車艙隱蔽,昨晚癸深又沒去陪阿言,心中想念得緊,癸深身子壓了過來,將阿言從自己的思考中喚醒。
心中一動,阿言回應了癸深一個長吻。
當晚,城主座駕移至少將府,換上便服的癸深和阿言走進府邸大門,到達正堂的一路上燃起巨燭,照得此夜如白晝般溫暖明亮。
正堂上那張圓桌上頭,擺下了近十道色香味俱全的料理,規模不大,卻看得出用心。癸冽沒有請閒雜人等,一桌子菜就真的只他們弟兄三人,癸冽請癸深和阿言入座,三人聊著少微時的經歷,彷彿回到了朏明苑的時代。
癸冽問阿言,聽說他消失的半年去旅行了,不知道去了哪裡,想請阿言分享一下,癸深和癸冽一輩子都在訓練和打仗,根本沒出門遊歷過,因此好奇。
這個問題其實癸深也問過阿言,但阿言沒有回答,只一個吻便結束這個話題。
但阿言不能吻癸冽,看來這話題逃不掉了。不過,因為小時候曾經流浪過很長一段時間,阿言急中生智,就小時候的印象加油添醋,盡挑庶民階層的事來講,癸深癸冽這兩個公子與民間疾苦有段距離,便也被他這樣忽悠過去了。
這晚三人聚得盡興,散席時盡皆微醺。癸冽問癸深和阿言要不要先在少將府過一晚,明天再回去。
阿言並不想在少將府待下來,他沒有把藥帶出來,萬一噬心散發作就慘了。幸而癸深和他心有靈犀似地拒絕了癸冽,他就想回城主殿和阿言待著。
癸冽知道癸深的想法也沒堅持,盛意拳拳地將主僕二人送了出來,目送他們的雪熊車離開。
癸深和阿言就在車裡待著,癸深總是忘了他把音羽靈珠給了阿言,不懼冷熱,擔心阿言覺得冷,想把身上的大氅脫下給阿言穿,卻突然發現他的大氅不翼而飛。
肯定是忘在少將府了。
阿言記得那件大氅不是一般的大氅,通體素白的它鑲了金邊,那是專屬於城主的用色,只有城主能穿,若被盜用或冒用就不好了。
「不急,癸冽發現後,他會替我送回去的。」
阿言說要去拿回來,癸深說不用了。
「還是去拿回來比較穩妥。雖然癸冽少爺值得信任,但若被那些整理正堂筵席的僕婢拿到手就不好了。少爺先回去吧,我拿到東西便也回去了。」
說完,阿言準備下車。
癸深也覺得阿言說得有理,便讓車外的隨從,騰出了一頭雪熊給阿言,讓阿言早去早回。
阿言回到少將府,將雪熊繫在府側一株合抱粗的樹下,走向大門。那門口侍衛剛送走城主和阿言,又看見阿言回來,招呼道。
「夜深了,言侍衛怎麼回來了?城主有事交待嗎?」
「城主大氅落在了正堂裡,命我回來拿取。」
阿言和門口侍衛攀談了起來。
「兄弟行個方便吧。」
「那有什麼問題?城主大人和我們少將是什麼交情,言侍衛你快進去取吧,讓城主著了寒可不好。」
阿言客套了一下,便邁步走進了府邸。
穿過一路暖光來到正堂,方才的筵席已經收拾乾淨,那大氅方才一進門,阿言就替癸深隨手掛在了牆上。阿言取了大氅要走,卻在走出正堂時,看見前院邊緣的迴廊裡,有個身影走了過去。
少將府僕婢不少,夜半巡邏什麼的也不是問題,不過阿言發現那人穿著白色長袍。
整個少將府有資格穿白色長袍的,只有癸冽。其他侍衛僕婢都不能穿象徵癸氏貴族的白色。
但那人不是癸冽。
而且,身形看上去有些眼熟。
阿言放輕腳步跟了過去。他在寂海時武功也沒落下,蓄意跟蹤一名癸氏高手,竟也能不被查覺。
那人去到迴廊盡處的少將府書齋。齋前的侍衛替他開了門。
在那人邁步走進去的同時,阿言看見書齋裡的燭光映亮了他的側臉。
果然是熟人。
那是朏明苑總教頭,癸江。
別人也就算了,那癸江是癸鴻的父親,癸鴻死在阿言手上,癸冽搬出前城主癸潺阻止癸江為難癸深和阿言。
癸江可以說是他們三個人共同的仇人。他怎麼會出現在這裡?
尤其是癸冽。當年癸江利用癸冽幫助癸鴻上位,讓癸鴻冒領癸冽的功績,癸冽有多恨癸江,阿言是知道的。
再怎麼想,癸江都不可能是會出現在這裡的人。
書齋門口有侍衛,阿言無法靠太近,他潛伏在一旁的造景巨石後頭,等癸江出來。
他是不是又要威脅癸冽什麼?
癸江的背後,是少爺最大的政敵,癸辰。
也許他是來威脅癸冽少爺的,一定是這樣。
這麼一來,他更不能走了。有什麼變局,他可以直接出手幫助癸冽。
只可惜不能靠太近,不知道他們在裡面說些什麼。
等了約莫兩刻鐘的時間,癸江才從書齋出來。
癸冽送他出來。
還送他出來?癸冽都是少將了難道還怕他?
癸江逕自走了,身影消失在黑暗裡。
「癸冽少爺。」
癸冽轉身要回書齋,聽到背後那一陣熟悉的聲音響起,他有一瞬間的斷片。
他知道那是阿言的聲音。
阿言怎麼會在這裡?他們不是離開很久了?
阿言又叫了癸冽一次。癸冽才恍然回神,深深吸了一口氣,整理好情緒,轉身朝阿言。
「是你啊阿言,你和城主不是回去了嗎?」
「少爺大氅落在府上,我回來取了。」
阿言憂心忡忡地道。
「癸冽少爺,癸江怎麼會出現在這裡?他威脅你什麼嗎?」
癸冽盯著阿言看,半晌。想分辨阿言表情裡的擔憂,到底是真是假。
「癸冽少爺?」
阿言叫了幾聲,癸冽都不說話,有些陰沉。
他從沒看過這樣的癸冽。
「朏明苑裡有個他很器重的弟子,想讓我幫他安插好一點的職位,最好是城主侍衛。」
半晌過後,癸冽才又恢復了一派和煦的微笑。
「你知道癸江那個人就是喜歡攀關係,為人不太正派。但他畢竟是朏明苑總教頭,好歹帶過我和城主,我也不好趕他走。城主油鹽不進,他覺得我還好說話,便來找我了。」
「我跟他打哈哈而已,他的人,我哪敢安排在城主身邊?」
癸江的確是這樣的人。而癸冽也是那種顧全大局,不到不得已絕不會跟人撕破臉的人。
他的說詞很合理。
「辛苦癸冽大人了。他曾讓自己的兒子冒領癸冽大人之功,還敢來找癸冽大人你,這臉皮也真是夠厚了。」
也不知道阿言信了沒有。但他刻意提當年癸江對不起癸冽之事,癸冽是癸深的人,阿言不希望他和癸江走得太近,對癸深不利。
「是啊,但這官場本來就有很多身不由己。不過所幸阿言你不必經歷這些,城主大人如今已經有能力護著你了。」
癸冽走向阿言,拍拍他的肩膀。
「好好待在他身邊,別再搞失蹤了,城主大人會瘋掉的。」
說完,癸冽依舊和方才一樣,禮數周到地送阿言到門口,目送他離開。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