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年5月,二次大戰已進入尾聲。美軍收復菲律賓後,下一個目標是台灣還是琉球(沖繩),兩個島上都是風聲鶴唳,殖民政府也不再拐彎抹角的搞什麼「志願兵」了,直接「日台一體」的徵召台灣人入伍。
這時的台灣也已完全喪失了制空與制海權,美軍的轟炸機光天化日就在台灣上空,肆無忌憚的轟炸起來。地面上偶爾零星的防空炮火,反而就像癌末病人的呻吟。台灣人民都在為這個殖民統治半世紀,眼看即將結束的帝國算命,看是自己先死在空襲裡,還是號稱「萬世一系」的帝國先滅亡。
阿姨當時讀小學五年級,他們從入學起就已經實行「日台同校」,班上有日本同學,也有本島同學。那天下午空襲警報一響起,平常很嚴厲的日本導師,就用軍事化的口令,讓學生很有秩序的進入防空洞。因為平日訓練有素,沒多久全校學生就集合在燈光灰暗的防空洞裡。
忽然間防空洞裡有了一點騷動,原來他們班上有一個智障生,常常在課堂間去上廁所,而廁所在校園的另一角落,離教室有一段距離。這個智障生顯然不懂得應變,無法自己進入防空洞。阿姨看到平常嚴厲的日籍導師,跟隔壁班老師交頭接耳,再向日本校長報告後,竟然推開鐵門,衝了出去。
過了一會,警報仍未停止,日本校長把老師都集合,由他自己帶隊,所有日本男老師與他一起出去,留下女老師與台灣老師在防空洞裡照顧孩子。直到警報結束,全校在操場點名,大家都到齊後,才看到那個平日很嚴肅的日本老師,背著一個哭的已經不成人形的孩子走回隊伍中,阿姨的淚水在大家的掌聲裡滴了下來。
。。。。。。。。。。。。。。。。。。。。

五、六○年代出生的台灣孩子,成長中一定與我有共同經驗,就是我們讀書當兵時,身邊一定有一個以上叫「台生」的同學或同袍。這些「台生」的父親保證是外省人,因為本省人絕無可能給孩子取名叫「台生」。
大家想一想,外省人來台灣五十年,現在外省人都到了第二、第三代,他們去大陸照樣要拿「台胞證」,大陸政府也視這些人為「台灣人」了。日本人在台灣也是五十年啊!有幾十萬個「台生」(不過他們給孩子取名是叫「灣生」),各位有沒有想過他們與台灣人怎麼相處嗎?日本人有可能像魔戒裡「半獸人」一樣,天天拿鞭子在後面鞭打台灣人嗎?
阿姨回憶他們的小學的日本老師、校長被老蔣掃地出門時,是所有台灣學生哭著送到火車站,家境好一點的台灣同學還送到基隆碼頭。然後這些「台生」回去後,還是和台灣的同學保持聯絡,退休以後幾乎每年開一次「同窗會」(日本人比我們更愛開同學會)。
還有一些「灣生」歐吉桑,回日本以後始終不能適應自己祖國那種虛偽的禮節規範,老了退休以後,又回台灣買了房子。因為簽證的關係,他們必須像候鳥一樣,半年往返一次。他們會說台語,也許還吃檳榔、簽六合彩。不告訴你,你還以為那就是鄰居的阿伯,誰會猜到她是日本人。
日本統治台灣有很多面向,有棒子,當然也有胡蘿蔔,還有更多超越政治、種族的單純人際交往。但老蔣的課本只教棒子的故事,用意就在和中國人的仇日恨日意識做一個連結,讓自己的「低效率獨裁」不被人民看穿。所以日本政府的胡蘿蔔很少提,至於俗民歷史方面,更是草繩穿豆腐--提也不敢提。
可是即使教科書不提,這種集體記憶還是會傳下來。阿輝不是笨蛋,否則當過皇民,又當過共產黨的他,戒嚴時代早該被老蔣槍斃好幾次了,怎麼最後反而當了12年總統與主席?他領導的台聯去東京的靖國神社參拜,搞親日當然是政治上的自保動作,動員基本教義派保護自己不被阿扁清算。可是如果台灣沒有那個社會環境,這種政治動作又怎麼會發酵?
大家只看到大陸媒體一片叫囂之聲,卻看不到台灣俗民社會的發酵情緒。就好像阿扁的兩次大選一樣,選前都說泛藍光憑基本盤就一定當選,民調也一直領先很多,可是一到投票揭曉,大批沈默的艦隊卻突然浮出水面,讓戰局勝負逆轉。日本統治台灣時,究竟在人民當中做了些什麼,讓半世紀之後還有人在唱「何日君(軍)再來」,這其中有太多大陸人,甚至很多台灣人都不懂的歷史。
。。。。。。。。。。。。。。。。。。。。

因為我是基督徒,一向不願意去介紹台灣那些非佛非道的「民間信仰」。可是為了說明台灣歷史上真實的一面,讓那些愛台或恨台的網友,認識一下日本統治台灣時,到底是怎樣一個「警察國家」,就不得不用台灣各族群把日本軍警當神明來膜拜的事實略提一二。
台灣的族群除1949年開始移民的外省人外,可以粗分為說福佬人、客家人與原住民。要分析任何的台灣現象,也都不能忽略族群的差異。
很多人有個錯覺,以為日本日本統治台灣時是一個「警察國家」,警察人數一定很多。其實不然,日本領台時只派有憲兵3,400人、警察3,100人。後來人口增加,憲警合計也增加到一萬上下。但這麼少數的警察,就讓台灣當時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而且能快速現代化,這當中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實在很多。
原住民是台灣社會最強悍的族群,抗日情緒也是最高昂的。到了二○年代,日本已經有效統治台灣很久了,漢民族都已經放棄武力對抗,但原住民裡還是爆發了「霧社事件」。擔任山地警察非常危險,隨時都可能被原住民出草(砍頭)。
但日本與清朝或老蔣大不一樣,漢民族的傳統是將犯了錯或操守不佳的警察調到邊疆,用貪官去治理化外之民。可是日本剛好相反,他們的警察考試很嚴格,尤其是在山地或離島服務的警員,治安以外還必須擔起原住民的教化與醫療工作,所以還要先學習當地語言。
在無水無電的環境裡,還必須忍受瘧疾等風土病的侵襲,日本警察對台灣山區的貢獻,實在是讓許多原住民感動,因此常被原住民當神明來膜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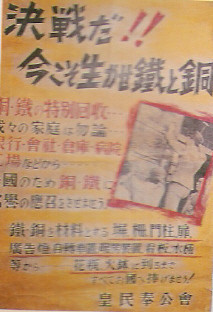
1924年出生於花蓮吉野村的山口政治,在他所著的《東台灣開發史》裡,提到在花蓮太魯閣的「托波克」蕃社,有一位被原住民奉為神明的日本警察武富榮藏。
武富榮藏生於佐賀縣大和町,1914年單身來到太魯閣的托波克蕃社上任。他服務期間看到原住民生活貧困,就將自己的薪水全數用在收養孤兒上。
當時原住民的衛生條件很差,尤其在鼠疫爆發之後,患者與日俱增。武富與其他同僚們,立刻用竹子為柱、樹葉為屋頂,建造了簡陋的隔離病房收容患者。偏偏禍不單行,颱風又侵襲部落,夜裡狂風一起,豪雨不斷。臨時搭建的隔離病房,經不起強烈的風雨吹打,好像小舟般的搖晃,屋頂破損,雨水不斷漏下。
當夜值勤的武富急忙爬上屋頂,全身淋濕卻仍堅持要補修破損之處,被收容的原住民害怕地哭叫:「既然要死,就死在自己的家裡,大人!你別管我們了,讓我們回家,你也趕緊回去吧!」
這時有些病患步履蹣跚地要逃出去了,照料人員不知所措慌張喊著:「大人!大人!」武富從屋頂跳下來,抱住帶頭要逃跑的病患說:「大家千萬要鎮定下來。像現在這樣的風雨如果出去,一定死在半路上,你們放心,我絕不會離開的。」
但是恐懼的原住民們根本聽不進去,還是哭喊著:「大人,無論如何要讓我們回去吧!」武富無奈,只好把自己的配槍交給那位帶頭的原住民說:「我是奉命來這裡保護你們的警察,誰堅持一定要離開,就請先殺了我再出去!」
武富的話終於讓騷動的病患們安靜下來。「大人!我們錯了!請原諒我們吧!」病患們終於回到自己的床位。武富修理好房舍,繼續照顧病患,直到自己也被傳染後致死,他的照片被掛在托波克社的神壇,成為當地人心中的守護神,定期由頭目帶領族人膜拜。
。。。。。。。。。。。。。。。。。。。。

興建於1901年的獅頭山勸化堂,位於苗栗縣南莊鄉,居民都是客家人。勸化堂裡供奉著一位日本警察廣枝音右衛門。
廣枝音右衛門1905年出生於神奈縣小田原,本來就讀日大預科,1928年以候補生幹部進入佐倉步兵第五連隊。退伍後當過小學教師,再來台灣擔任巡查,再升任警部。1943年他擔任海軍巡查隊隊長,率領2000名台灣人志願兵赴馬尼拉。
1945年2月23日,美軍已經登陸呂宋島,日軍司令部在戰前已分發巡查隊隊員手榴彈,表達「玉碎」的決心。但美軍登陸後,廣枝違背了軍方全員玉碎的命令,與美軍交涉後,召集了2,000名巡查隊隊員說:
「原本這是大家為國盡忠的時候,但你們都是台灣人,這場戰爭與你們無關,你們的家人都還在等你們回去,所以無論如何你們都要活著回去台灣。至於我是日本人,所以責任應該由我來來承擔!」
廣枝說完後舉槍自盡,保住了2,000名巡查隊隊員的生命,讓他們有機會回台灣。1983年台灣解嚴前,白色恐怖的氣氛逐漸淡薄,當年的台灣人小隊長劉維添,專程去當年廣枝隊長自殺的地方抓了一把泥土,送到日本茨城縣的廣枝夫人手上,並將廣枝奉祀在獅頭山的勸化堂。當年受惠於廣枝的部屬及其後人,也都會去定期參拜。
。。。。。。。。。。。。。。。。。。。。

位在嘉義縣東石鄉副瀨村57號的富安宮,這座福佬人興建的廟宇,供奉的就是俗稱「日本王爺」的「義愛公」--森川清治郎。
森川1861年生於橫濱市,他身高約155公分,體型微胖,下顎蓄鬚。1892年,娶妻樂木千代,1893年生子真一,原本任職於橫濱監獄。1895年日本領台後,隔年森川志願隻身渡台,任職巡查,配屬於台南州州知事官尾邦太郎麾下,後任職於鰲鼓﹙東石鄉﹚派出所。
1900年,森川調派至副瀨派出所,並接妻小來台同住。這時台灣各地盜匪叢出、治安敗壞,衛生條件也不佳,瘧疾、痢疾、霍亂等傳染病盛行,加上教育水平低落,幾乎全是文盲。尤其副瀨是靠海的窮鄉僻壤,生活困苦可想而知。
森川於是利用當地廟宇富安宮,創辦簡易教室以普及教育,不但自費聘請教師,公餘還親自教授五十音、單字、日用語;甚至自費購買紙、筆、墨作為成績優良者的獎勵。後來獨子真一到了入學年齡,也不進總督府為日本小孩設立的小學,而是與鄉民一起就讀。每次考試,除真一之外的同學都有獎賞,真一當然心中難平,長大後他才明白父親的苦心。
森川發現這個半漁半農的村落,農業技術落後,所以每月集合部落人民講習,改善村內環境衛生與農業技術,指導村民於住屋四周挖掘排水溝,疏濬污水;改良含鹽農地之土質,對於貧病者,則援助照顧。凡是勤勉者,即把鋤、鍬等送到他們手上作為獎賞,這些獎品都是自費。
偏僻的副瀨村常有土匪肇事,森川有一次乘竹筏剿匪後回來,聽說副瀨村的蔡稠因袒護土匪而被捕,關在朴子辨務署的留置場,可能會被處死刑。森川覺得可疑,於是展開各項調查,才發現是歹徒誣告。他找了東石區長吳踏與民眾,去見朴子支署長新井及東石支署長園部,為蔡稠做證,才洗刷冤屈,救回一命。
後來台灣總督府為了確立財政制度,實施了台灣特別會計辦法。嚴格規定煙、鹽、樟腦等的專賣化,而漁業稅也是必繳的稅賦之一,即使是沿海捕魚的小竹筏,也必須繳納稅金。所以森川巡查除了要執行警察的基本職務外,也要負責催繳當地村民的稅金。
但貧窮的村民要維持溫飽已不容易,所以請森川向上級請求減免賦稅,森川於是就向東石支廳長陳情,但長官則認為森川討好村民、煽動村民抗稅,就申戒處懲;並下令森川必須在剩餘期限內執行強制徵收之任物。
森川既憂憤上級忽視民生疾苦,對貧困的副瀨村民又不知該如何催繳。1903年4月7日上午9時,村中正在拜拜,森川巡查了港墘厝部落後,在部落中的慶福堂廟內,留下「苛政擾民」的遺書後,以村田步槍自盡,留下10歲的獨子。
副瀨村民聞此惡耗,深痛不已,除了舉行隆重盛大葬儀,還將他安葬在村外東南公墓。1923年,森川已去世二十年,副瀨近鄰一帶腦膜炎開始流行,疫情蔓延,民心惶惶,當時擔任保正的李九於睡夢中,見森川顯靈,身著警察制服,指著李九說:「鄰村正蔓延著傳染病惡疾,要注意全村的環境與飲食衛生,則可確保平安無事。」
李九醒後,就將夢中森川的叮嚀轉達全村,村民也整理打掃排水溝、注意飲時衛生,因而得以避過腦膜炎的肆虐。村民在感激之餘,決議敦請雕刻師雕刻一尊身著警察制服的森川坐像,高一尺八寸,供奉於富安宮內,遵奉為「義愛公」。並訂每年農曆的四月八日,為其大祭之日,舉行盛大祭典。
。。。。。。。。。。。。。。。。。。。。

台南市安南區的海尾寮,地址同安路127號的「鎮安堂」,鎮安堂俗稱「飛虎將軍廟」,供奉的「日本王爺」,就是二次大戰時喪生的日本飛行員杉浦茂峰。
根據《安南區志》與《鎮安堂將軍府緣起》所載,1944年10月12日早上十點,台南地區空襲警報響起,防空壕的上空有大量的美軍機群盤旋。日本海軍飛行少尉杉浦茂峰﹙死後晉升為中尉﹚駕著戰鬥機升空牽制敵機。
說是「牽制」敵機,一點也不誇張。當時日軍已敗象明顯,飛機無論質量都已不是美軍敵手。杉浦的飛機中彈引發尾翼起火,瀕臨爆炸的危機。如果立刻跳傘,這樣的高度降落後生還機率還很高。
然而當時飛機正在「海尾寮」上空,杉浦若是跳傘,雖然自己可以獲救,但是上千戶的村屋也可能受到波及。尤其當時台灣農村都是竹搭或木造的屋子,一旦著火馬上就會延燒,飛散的火星也會四處延燒,消防設備缺乏的村落會整村燒起來。
杉浦為了不讓無辜的台灣人民受害,於是決定將飛機轉為上昇,衝向台灣海峽。在海岸防風林躲避的村民,驚懼地看著一團火球直衝入海,轟隆爆炸一聲的同時,瞬間火球激烈地向四面八方飛濺,杉浦的犧牲保住了千百位台灣人民的命財產。
戰後,海尾寮村落到處流出不可思議的傳言,有人夢見睡覺的枕頭邊,有一位穿著飛行服的日本年輕飛行員,醒了後查出這位為了不讓村落引燒戰火,因而犧牲自己的飛行員叫杉浦茂峰。於是地方上有心人士聚集討論,決議建廟以表現台灣人最大的感恩與謝意。
杉浦茂峰的生日是11月11日﹙農曆10月16日﹚,其墜機地點在飛虎將軍廟旁約20公尺處,現在「旺晟香店」,這一帶戰後還都是魚溫,今已是商店林立的街道。日本皇室六條有康親王,曾於1995年7月來此參詣過,杉浦茂峰的姊姊,還有同期的飛行員,也專程從日本帶和尚來台唸經超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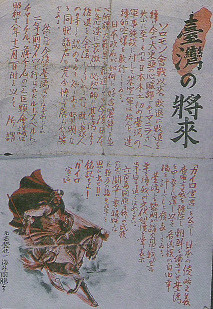
我們現在談的國族(甚至我們自我認同的民族),在人類文明上,都是很晚才出現的東東。以前的農民,都只是土地上面的孳息或是附著物,領主說你是什麼人,你就是什麼人。一直到啟蒙運動以後,承認人都是平等的,人都是有理性的,有理性就表示,自己會管理自己,自己可以決定自己的意志,我們才知道自己是誰。
所以,陝北黃土地農夫的孩子,為什麼要關心遠在萬里之外的台灣人呢?這並不是寫在DNA裡面,也不是因為這些孩子天生就會認出同胞,而是經由一連串很綿密、很精細的社會教育認同程式。這套程式,現在看起來很理所當然的東東,對日治時代台灣各族群的農漁民,就沒有那麼理所當然了。
所以政府需要一再地提醒和教化這些,例如老蔣教我們的「中華錦繡江山誰是主人翁,我們四萬萬同胞」,就是因為四萬萬同胞還沒有一個現代的「中國人意識」,他們可能只有宗法意識、只有尊君意識、只有鄉土莊園意識,所以老蔣才要不停的在思想上動員我們。但動員了半天,頂多只有一半的台灣人認同,另外一半就是頑抗。
島內有一部份住民有抗日的歷史記憶,可是另一部份則有日治時代參軍的歷史記憶,而且長期被壓在社會陰暗的角落裡。你不能說,因為會惹的另一群人不快、不舒服,我們就只能乖乖留在歷史的陰暗角落裡面。
所以,台灣在解嚴後經過辯論和衝突,即使泛藍或外省人,大概也可以接受,台籍日本兵是時代的悲劇。台聯不要去東京的靖國神社拜,去新竹參拜就沒人抗議了,這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歷史是從個人出發,不先走這一點,永遠不能明白,為什麼有人那條同胞與異族界線劃的與你不一樣。台灣人對日本的感情是很複雜的,那條同胞與異族的線,絕對不是直線,而是一條彎曲的曲線。
台灣除了外省人以外的福、客、原各族群,都還還有人在唱「何日君(軍)再來」,甚至就堂而皇之的將日本軍警拿來當神明膜拜,這種俗民記憶,歷經老蔣與小蔣40年的白色恐怖依然存在。要認識台灣,除了紅藍綠這些政治有色眼鏡外,是不是也該試戴一下我用的這種「小民無色眼鏡」?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