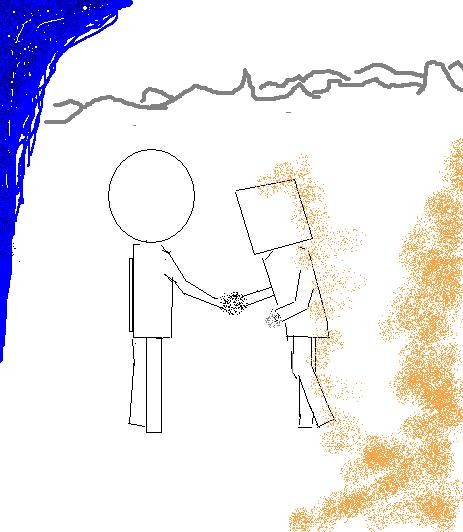
我到底在幹什麼?
看著毫無異狀的季雨,再想起昨晚華松翊的態度。我突然覺得一切都不怎麼真實了起來-包括了每個談話之間的笑容、敘述時的肢體動作、小事大事的默契。
糟糕的虛假。
*
「很失望吧。」
媛琳盤腿坐在社團教室的桌子上(今天穿的是運動衫和運動長褲),在我練習【Dear Cherry】到一半時,突然冒出了這句話。
我停下動作、茫然的回望著她。
「嘖。俺開玩笑的。」
*
昨晚,先將媛琳送回家之後,松翊和我走在詩織與柏豪的身後。
氣氛有些尷尬之際,松翊卻語氣熱切的開了口:
「你跟陳媛琳很熟嗎?」
「還…不算-」
我腦中突然閃過許多解說畫面:至少一起去看過電影、談過許多私人的話題。「不算不熟。」
「那你怎麼跟她搭上話題的呀?」
「就剛好有話題…」我發現這句話是多餘的。
「陳媛琳在我國中的時候,是滿有名的一個人。」柏豪回頭插了句話。
「聽說她小學原本是非常外向、好動,跟個小男生沒兩樣的女生。」
「恩恩。」我開始想像那個小男生的模樣。
「你們在說什麼啊?」詩織好奇的湊了進來。
「在說陳媛琳~她國中時-」柏豪停下嘴巴,猶豫著該不該繼續說下去。
「怎麼了?」她說。
「妳不會吃醋吧!」松翊補充說。
「不會-這跟我沒關係。說。」命令的語氣。
「她一轉學過來,就講了口流利的英文。恩…運動有擅長的項目,同時好像也很擅長美術。啊啊另外,外型各方面也…恩…你知道意思。」
面對松翊的傻笑,我想正常男生大概都是知道意思的。
我看了詩織一眼。「在我們學校,反倒是你弟比較有名。」
柏豪出乎我意料的,不好意思的抓了抓頭。
*
媛琳當作沒聽見我所轉述的那些評論,只不以為意的問:「妳考試準備的怎麼樣了?」
「打擾我念書、把我抓來彈鋼琴的人,居然問我考試準備怎麼樣了。」
話雖然這麼說,但今天我根本也無法專心念書。
六月接近中旬的時刻,除了玩心較重的學生外,整個學期只剩下「考試」這個盛大的活動。以我們這所中上程度的高中來說,考前的校園氣氛都有些緊繃(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就是了)。
而此刻,社團教室裡的悠閒氣氛,活像是片綠洲似的令人輕鬆。
在這氣氛下的社團教室裡,我感覺自己跟小時後去音樂教室一樣,有著期待、困惑與輕鬆的心情。然而,對於那位老師說的「把心按壓在琴鍵上」,對目前的我來說還是太抽象了。
也許,她是希望我能更專注在彈琴這個活動上,從鋼琴裡得到比純粹彈奏還要更多的靈感。那麼,我該如何去定位我的工具-也就是鋼琴呢?
(「你知道嗎?我覺得重要的是,樂器就像是伴侶一樣經常在接觸,所以應該給他取個異性的名字。」-阿人生日那天,季雨所說的話。)
【潔思蒂】雖然有個人性化的名字,但終究只是個不常使用的舊鋼琴。
在這個逐漸數位化的時代,類比似的人物從故事裡消失,有時我都忘記了雙眼就是最棒的攝影機、雙耳就是最佳的錄音機。
*
「妳會不會有時候想著:我到底在幹什麼啊?」
對我的突發奇言,媛琳挑起右眉、左手托腮,做出思考「我為什麼要問這個」的模樣。
「在幹什麼…俺知道自己昨天做了什麼、今天跟現在做了什麼,但-」她停頓了一會兒,「恩、就是也不一定完全清楚做了什麼。」
「我也不完全清楚妳說了什麼耶。」我聳聳肩說。
「就像-像是俺現在坐在這裡跟你說話,但俺可能去吃東西、練習素描,某方面來說,這不是難以解釋的嗎?」
「妳自己找我的,還有什麼好疑惑的?」
她伸出雙腳踏至地面,走到鋼琴旁,抽起了一張琴譜。
「如果,每件事都有個原因跟目標,那麼會讓人迷惑的,可能不是該做什麼事,而是不清楚原因和目標。」
「那麼-」我看著她說「就眼前來說,妳坐在這邊跟我說話,是比較沒有原因跟目標的囉?
「可能吧!」
「既然如此,那又-」
「又怎麼了嗎?俺認為啊…」她將琴譜放回琴譜架上「你一直沒意識到…像是俺說過某種非理性、與『靈魂』相同功用的東西。」
接著,她假咳了幾聲。
「你彈鋼琴的時候,不會感到有股冥冥之中在選擇一切的東西嗎?」
「妳講話很像我以前的音樂老師。」我吐吐舌頭。
「她說些什麼?」
「把『心』按壓在琴鍵上…會從琴絃中聽見上帝的指示,得到生命旅程的目標。」
我用我自認最莊嚴的語氣,模仿起當時老師的那段話。
沒有引起預期中媛琳的回應。
她臉上鋪滿了略帶不詳般的迷惑,開口說:
「…你有搬過家嗎?」
「沒有,怎麼了?」我詫異的回答。
「那、那你住中永和,烘爐地那方向吧!」
「是啊,我說過了吧!」
「噢…」我發現她神色有異,卻還是不知道自己說錯什麼了。
「那個老師是基督徒,在你升國中,年紀應該四十出頭。」她低聲說。
「差不多,不過我要升國中時,就沒繼續去音樂教室了。」
「後來,那位老師因為女兒去世,休息了一陣子。」
「這個…我不清楚原因。」
她沒有哭泣。
「她女兒叫作陳采琳」她淡淡地說「是我妹。」
太巧了吧!
這樣說起來,我應該曾經見過還在世的陳采琳。
換句話說,以前覺得曾在哪看過陳媛琳,原因不只是打工時那個變裝的【普兒】,而是可能更早以前就看過那張相同的臉了。
過了這麼多年之後,又再度從音樂接觸到了熟悉的人了。
等我回過神時,媛琳正在用好奇的眼神打量著我。
也不知道是為了什麼,我挪動身子、指示她坐在我旁邊。
手指放在琴鍵上時,幾乎不加思考的,我就彈起了【小星星】…
「嘿…你知道【小星星】這首曲子的由來嗎?」
「給妳說。」
「曲子是法國民謠、英文原詞是英國詩,每個版本都有傾訴的意味。」
我完整的彈完一遍,看不清楚她頭髮遮住的表情,於是又彈了一遍…
一遍…一遍…又一遍…
當初練習時,也是這樣從彈完、流暢、熟練,最後樂在其中的彈奏經驗。彈奏的目的早已遺忘,在樂在其中之後還能投入情感的現在,我總覺得有什麼東西好像要從琴鍵上跑出來似的。
「twilled twilled little stars…」
終於,像是放下心防似的,她開始唱和著【小星星】英文版。
她的笑容,跟我所認識的陳媛琳有些不同,卻又顯得更為自然。
*
後來,我才知道,那段「把心按壓在琴鍵上」的話,是母親尚未與父親離婚時對她說的。
當時,母親希望好動的姊姊能跟著學音樂,就像學美術的妹妹一樣有氣質點,所以才對當時還小的媛琳說了那段話。然而,突如其來的離婚(對小孩子而言),使媛琳失去了剛要開始的興趣。
我想,若是陳采琳沒有出事的話,媛琳也許就不用把美術當成自己的興趣了吧!
我希望能在畢業前彈成【Dear Cherry】。即使媛琳已不再拉我去社團教室,我還是每天翹掉晚自習去練琴。某方面來說,這是在紓解大考的壓力;若是說我拙於面對某人,那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季雨為什麼一直沒提到那件事呢?
雖然新聞沒有很大,但是對方是自己曾經熟識的人,難道都不會有悲傷或者些許「是我不好」的感覺嗎?
如果這件事跟自己無關,那麼看見華松翊時,為什麼不但臉色變了,還突然像心虛般的離開了呢?
「妳真的是殺人兇手嗎?」
我當時知道,季雨不是那種會講負面批評、落井下石的人。
只是,我無法那樣問出口-
我害怕聽到她說出的,只會是理所當然般寂寞的答案。
「先當作柏豪他哥沒講過話。」
無論是與她們關係較久的詩織、後來知情的阿人,以及一直都知道卻不相關的柏豪,都同意這件事無須再談-至少在大家專心考試、一起相處的期間,先不要提起這種嚴肅的事情。
我接受了,因為我也不願破壞表面的和平。
就這樣重複剩下的日子,在逐漸炎熱的日子到來時,我們畢業了。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