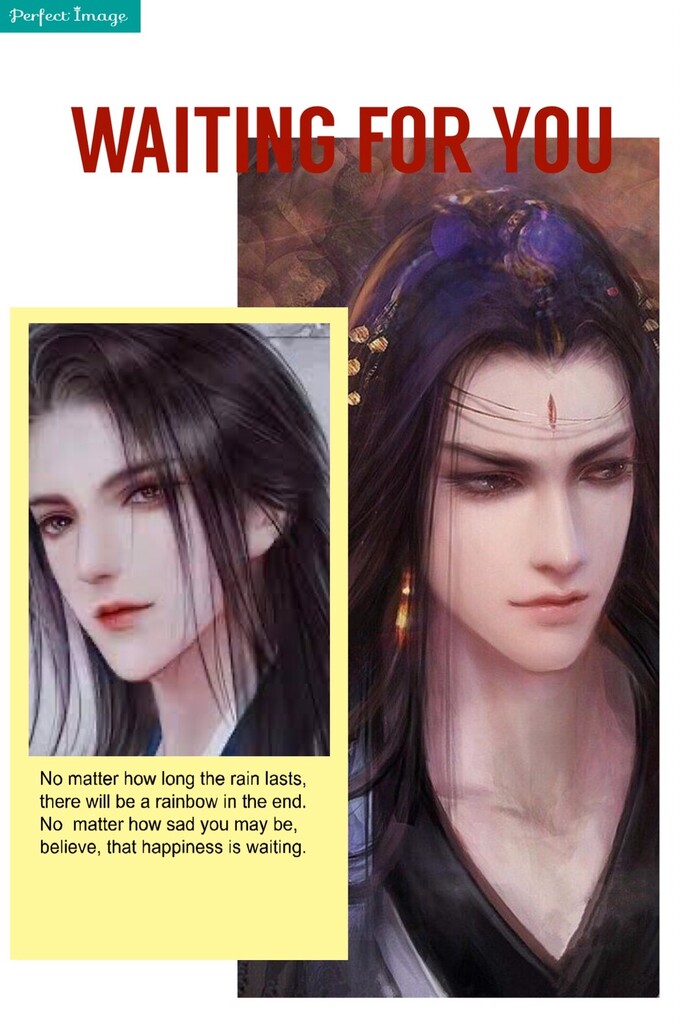
此後,阿言一直值的都是子夜的班。他就這麼守在癸深的寢殿門外,聽著癸深夜夜笙歌,每天晚上換著不同的床伴,玩著不同的花樣,求饒哀告聲,妖嬈呻吟聲,至樂嘶吼聲,從那些淫聲穢語裡,阿言可以很輕易腦補房間裡的春色。
阿言強抑激動的情緒,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更加傷身,噬心散發作的頻率也越發頻繁,疼痛程度越是強烈,逼得他每天晚上值班前,都得服用兩顆緩解藥才有辦法撐下去。
因為晚上藥吃得兇,而他一直無法提供對方有用的,關於癸深的資訊,他知道他遲早會被斷藥,不得不省著點吃。沒有值班的日子,他便不吃緩解藥,常常是一個人在房間裡痛到滿地打滾,直到整個人暈過去。
然後,一個人醒來。
但,他現在什麼都不求了,就算癸深對他的蓄意傷害,就像驚雷一道道,不斷劈在身上。他彷彿失去痛覺,因為他現在只專注一件事。
以他的體力和意志力,大概也只能容許他完成那件事。將纏繞在癸深身邊的那株毒藤連根拔起。
阿言的冷漠和若無其事更讓癸深惱怒,他總是在阿言值班時,變著花樣折騰阿言。
一下子活動太激烈肚子餓了,讓阿言半夜去膳房熬粥送過來,或者體力消耗過甚渴了,讓阿言去端酒過來。
阿言便這樣被癸深叫進房間裡,一次次看著癸深和他的新歡赤身裸體地在床上交纏取樂。
想起過去的繾綣綢繆,阿言心如刀割,都不知道此時的疼痛到底是噬心散發作,還是真正的心痛。
這天,阿言又奉癸深的命送酒進來,太多次這樣的夜,阿言已經練就了麻木以待,他低著頭一眼都不看床榻上的即景,正要退出,癸深又喚住了他。
「等等……」
癸深抱著他今晚未著寸縷的新歡,朝阿言令道。
「他的衣裳被我撕壞了,你的身型跟他差不多,拿套你的衣服過來,就......我上個月賞的,那件鑲了雪熊皮毛的暖袍好了。」
阿言已經失去音羽靈珠,無法抵禦寒冷,癸深說的那件雪熊暖袍,是癸深賞的,也是阿言常穿的。
現在,癸深要把它收回,送給他的新歡。
就像他收回對阿言的情意,如此輕易。
阿言背對癸深,站著不動。他知道癸深不差那件袍子,可偏要來奪他那唯一的一件。
「怎麼?捨不得?」
背後響起癸深涼薄的聲音。
「捨不得就滾,別在我這裡礙眼!」
說完,癸深又轉向懷裡的人兒,溫言道。
「不要緊,趕明兒個讓繡坊給你縫件更好的,兩層雪熊皮如何?」
那新歡歡天喜地地謝了癸深,兩人又滾在一起。
阿言很不想因為感情,耽誤了自己想做的事。但面對癸深的刺激,他又沒法全身而退。
他是凡軀,不是銅牆鐵壁,就算他武功再高,癸深就像一把劍,知道如何對他一揮見血。
因為他是孤兒,是賤民,一無所有,他只有癸深。
阿言靜靜地走出寢殿。
回到自己的房間,阿言的噬心散又發作了一遍,明明今晚也吃了藥,但兩顆的藥量已經漸漸壓不過噬心散的毒性了。
或許是在癸深那裏刺激過甚。
也或許,他的日子已經不多了。
他忍著不再吃藥,又在地板上暈了一次,半個時辰後才轉醒。
仍然是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地板上。
他突然覺得,自己要死了,那麼珍貴的袍子給一個將死的人的確是浪費,如果少爺真的喜歡那名新歡,不如讓這件袍子護持著他,這樣起碼少爺還會高興些。
看著闃暗的天花板,阿言忍不住流下眼淚。
當後半夜,阿言捧著那件雪熊袍子,回到癸深寢殿,癸深的怒氣到達頂點。
他送的東西,他付諸阿言身上的感情,阿言都可以說不要就不要!
阿言殺了癸濯這件事,他替阿言扛下了,來自癸氏貴族和侍衛們的壓力,他沒有殺阿言,甚至仍然將阿言留在身邊擔任侍衛,捨不得處罰他,但阿言可能背叛他的事實卻像一把刀,在他心上一刀一刀畫著,鮮血淋漓。
他很想相信阿言,但阿言無法給他一個正當的理由。
他不知道阿言為什麼要對他隱瞞,相愛的兩人本就應該坦誠相對。
阿言堅持不說,他只能理解為那個原因,甚至那個讓阿言背叛的人比他癸深更為重要,所以阿言選擇倒向了那個人。
這認知讓癸深簡直要瘋了!
今晚他向阿言討要那件袍子,除了想讓阿言難堪外,潛意識裡,他也存了阿言不會捨得讓出袍子的希望。
若阿言還是珍惜著他的心意,給阿言個小教訓,他們仍舊可以重新開始。
所以當阿言捧著袍子出現在城主寢殿裡,癸深的情緒到達臨界!
「這件破袍子有甚麼稀罕的!」
癸深一把扯過那件袍子,將它丟進了火爐裡,看著它很快地就被熊熊火焰吞噬!
阿言呆住了,他只是聽了癸深的話,他不知道癸深為什麼這麼生氣!
癸深氣還沒消,他將案上的書,筆,杯盞,床帳,櫃裡的袍服一件件都扯出來,甚至手邊可以拿到的東西,都丟進火爐裡!
爐火越燒越旺!
燒完了衣服,癸深又燒櫃子裡的其他東西,直到他拿出了一個紫紅色的木製匣子,順手一丟!
那匣子落入火裡,被爐子撞開,露出了裡面的東西,一片一片的。
阿言認得!那是他從寂海寫給癸深的信!
「不可以!」
阿言眼眶一熱,衝向火爐,想把那些信撈出來!
然而火勢實在太猛烈,信箋又是易燃物,阿言不惜將手探進火裡,卻只拉出那只空木匣子,還有一堆黑色的灰燼!
阿言的手和下頷都被燒傷了,然而他彷彿不知道痛,跪坐在地,呆呆看著手中被他搶救出來的,黑乎乎的垃圾。
癸深也看見了他燒的是甚麼,但眼前的阿言,讓他覺得很矯情!
那信箋中的字句有多動人,兩人曾經的感情就有多虛假,他癸深的心裡就有多悔恨!
「假的!都是假的!」
癸深掀了桌子,怒氣沖沖,邁步離開他的寢殿。
阿言那副要死不活的樣子太刺眼了!
他到底想怎樣?
癸深覺得再不走,自己可能會忍不住打死阿言!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