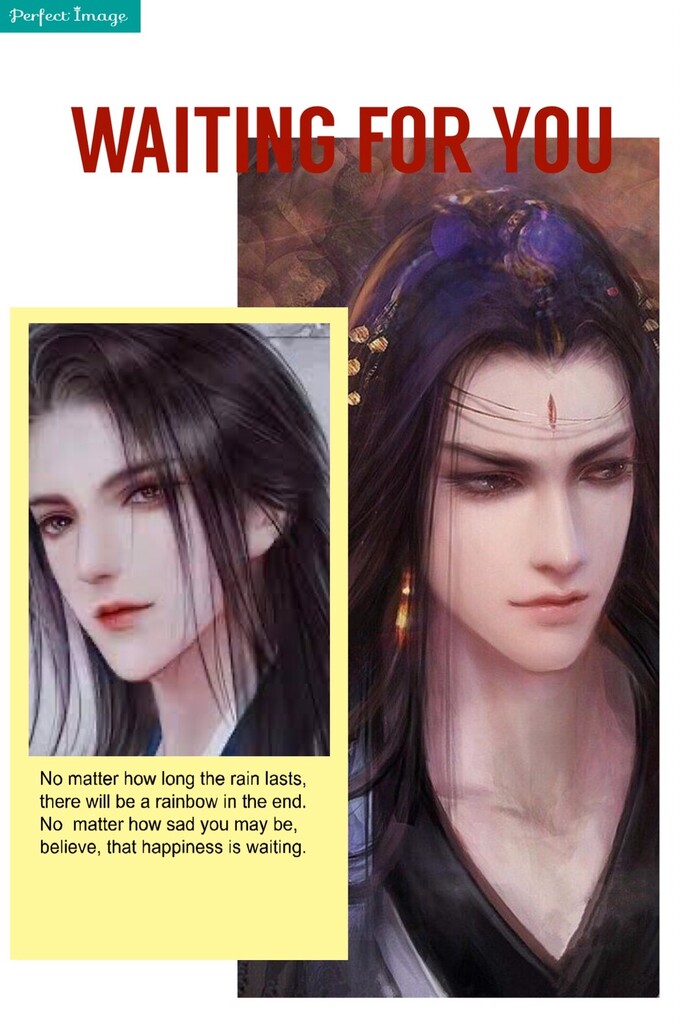
癸珞將這兩天癸深必須處理的公務整理好之後,徑朝城主殿書齋而去。
兩旁侍衛替癸珞開了門,癸珞正要踏入,冷不防一隻茶盞飛了出來!
癸珞是將門之女,雖然武功不如他們那些癸氏的精英戰士,但反應還是不錯的,她身子一閃,杯子掉到地上,砸得粉碎!
「這種小事也做不好,有什麼資格在我面前瞎晃!別再讓我看到妳!」
書齋裡傳來癸深的吼聲!
然後,慣常伺候癸深茶水的侍婢霧兒狼狽地被轟了出來!
霧兒眼眶都紅了,看見癸珞,狼狽地福了一福,叫聲珞總管,過去撿拾茶盞碎片,蹣跚地走了。
「怎麼回事?」
癸珞問守門的侍衛道。
「這兩天,癸深大人的情緒很差,方才負責研墨的霰兒已經被轟出去了,現在是霧兒。」
「她們兩個都是伺候城主慣了的,深知城主脾性,不大可能犯錯啊!」
「所以才說癸深大人的表現是因為情緒差,總之珞總管妳進去時小心一些。」
侍衛好心提醒。他自己也是臨時被叫來上工的。原本值班的兩名侍衛也都被癸深以不同的芝麻綠豆理由轟走了。
癸珞點點頭。她出身癸氏貴族,和那些奴婢並不相同,癸深對她的態度會有底線,不至於拿她撒氣。
她跨過門檻走了進去,看見癸深桌上一片狼藉,公文四散,癸深自己的臉色也很難看。
「城主大人,奴婢來向您報告這兩天的公務行程。」
癸珞朝癸深作了揖。
癸深抬頭,見識癸珞,一腔怒氣強制壓下,揉了揉眉心,道。
「妳說吧。」
癸珞拿出記載行程的木牘,一條一條報告給癸深聽。這兩天公務不算多,剩下的時間,癸深能夠安排自己的私人行程。
「知道了,妳退下吧。」
癸深在半個時辰後就有一項去城郊視察軍演的行程,他只說知道了,卻一點沒有動身的打算。
「奴婢先替城主沏盞茶吧。」
見癸深辦公桌上連盞茶都沒得喝,癸珞走向書齋側間的小廚房,沏了一盞蔘茶,再奉與癸深。
和霧兒沏的茶比起,癸珞沏的茶並不合癸深的胃口,不過癸珞的貴族身分在那,癸深也不好為難她,勉強啜了兩口。
在癸深喝茶的時候,癸珞替他整理了那一桌散花的公文。
「城主若覺煩躁,何不出去散散心?」
癸珞勸道。
她大概知道癸深煩亂的原因。
癸深頓了一下,終究還是道。
「算了,公文批不完。城郊軍演,妳讓癸冽替我去吧。」
交待完後,癸深重新埋首公文中。
癸珞點點頭,先去少將府請癸冽城郊看軍演。對於公務,癸深從來事必躬親,這次卻讓癸冽代他去。癸冽問癸珞城主人怎麼了。
「城主這兩天心情不好,您有空可以去城主殿,陪他說說話。」
癸珞想,過去在朏明苑,癸深、癸冽和阿言曾經相濡以沫,癸冽在癸深心中的分量非比尋常,或許,癸冽會知道如何勸癸深。
畢竟,讓癸深心情不好的源頭,正是阿言。
「知道了,我稍晚再過去找他喝酒。」
兄弟嘛,沒有什麼是一壺酒不能解決的,如果有,那就兩壺。癸冽想。
將城主殿的一切打理妥當後,癸珞去安撫了被癸深暴風尾掃到的幾名侍衛和侍婢,畢竟以癸深的地位,身邊的人最好別換,要值得信任的人才好。
做完這些事,癸珞便提著一籃子晚飯,去客房看阿言。
看到癸珞,阿言很是高興,手忙腳亂地幫癸珞布菜,癸珞還特地拿來一壺酒,要跟阿言對酌。
自從寂海分別,兩人已經半年沒有見面了。各自聊了這半年來的生活後,癸珞忍不住問阿言,他和癸深到底怎麼回事。
「阿言哥哥,我記得你在寂海的時候,每天都就著寂海的月光,讀癸深大人寫給你的信。那時的你,幸福得快要從眼角溢出來了。」
癸珞誠懇地道。
「你每天都希望回到癸深大人身邊。可現在……你已經回來了,卻為什麼要拒癸深大人於千里之外呢?」
癸珞的問題,讓阿言頓了一下。
回來兩天後,他都沒有見到癸深。他不知道自己拒絕和癸深同房,癸深竟然會這麼生氣。
沉默半晌。阿言道。
「少爺有說,他想怎麼處置我嗎?」
「沒有。他連提都沒提過你。阿言哥哥,你們之間到底怎麼回事?你明明對他……」
癸珞頓了一下。
「或者,這半年來,你有了其他喜歡的人?」
癸珞曾經偷看過他和癸深之間的書信,她覺得阿言移情的機率不高,可若不是這樣,要怎麼解釋阿言回來後對癸深的態度?
「沒有。我喜歡的人只有少爺,這點從來沒變過。」
阿言說這句話的時候,帶了些哽咽。
「那這半年來,你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對城主這麼冷淡?」
身為阿言的妹妹,癸深的總管,這兩個人連感情都讓她操碎了心。
阿言想說什麼,可喝了兩盞酒,最後終究什麼也沒說。
「癸珞,少爺身邊有奸細。」
比起他這半年來發生什麼,還有更要緊的事必須釐清。
「妳比我早回來半年,又在少爺身邊貼身伺候,可曾看出少爺身邊有人不對勁?」
癸珞深吸了一口氣。癸深憑甘淵奪權的事,她是陪著經歷的,她當然也知道,癸深資歷不深,許多人對他是面服心不服,甚至癸潺是被他殺死,就因為他想奪取甘淵這個流言也從來沒停止過。癸深的城主之位其實如履薄冰。
癸珞仔細地想想。
「城主身邊都是他用慣了的老人了,反而我的資歷是最少的。他們陪著城主一路走來,我實在看不出誰是奸細。阿言哥哥,你為什麼會這樣說?」
「沒什麼……我只是覺得,癸潺大人死得蹊蹺。他對少爺有知遇之恩,少爺自然不會不利於癸潺大人。不只是癸潺大人的死,甚至蟠龍港那場戰役的失敗,我覺得都有問題。」
阿言試圖說服癸珞。
「那些事我也是路上聽百姓說的,並未親身經歷。所以我想,既然我回到少爺身邊,為了少爺安全起見,還是想查查這件事。」
「我知道你關心城主。既然關心他,不是應該待在他身邊,更能保護他嗎?你們這樣天各一方又算什麼啊!」
癸珞笑著揶揄阿言。
癸珞走後。阿言躺在床上,一直想著癸珞的話。
奸細的事從癸珞身上,是問不出來了。
但他和癸深關係變成這樣,也的確對查出奸細這件事沒甚麼好處,他也沒法近身保護癸深。
可是,那個問題……
他不能讓癸深看出來。
所以一回來,他便選擇和癸深保持距離。
可這樣一來,他就沒法接近癸深,沒法保護他了。
他必須待在癸深身邊,同時不讓癸深發現他身上的那個問題。
到底該怎麼做?
沉靜的北原之夜,月光照在積雪上,把院子裡的樹影映在了窗紙。
當然,若有人影,也映到了窗紙上頭。
他知道這兩天,癸深雖然沒有見他,卻會在睡前,到他房門外待一會。
月光把癸深的身影照在了窗紙上。
阿言發現了,但他裝成沒看見。
因為,他還不知道該怎麼做比較好,雖然不捨,也只能任癸深站在外頭。
而癸深也倔強地就是站在外頭,也不進去跟阿言打招呼。
他們的關係,必須有所突破。
最好能在癸深身邊做個侍衛。這樣,他就能觀察癸深身邊人的一舉一動。
這天晚上,算準了癸深出現的時間,阿言在房間裡擺下浴桶。
然後,從懷裡掏出一個黑色瓷瓶。
瓷瓶在燭光下閃爍陰翳。
阿言拿著瓷瓶的手,有些顫抖。
想了很久,阿言終於下定決心,從瓷瓶裡倒出兩枚藥丸,就茶水服了下去。
每晚來來去去,他和阿言只隔了一道薄薄的門,卻像兩個世界,他走不進去,阿言也不出來。
他很想問問阿言到底怎麼回事,卻又不甘心,明明以前他們那樣好,信裡面字句愛意滿滿,那些難道都是假的?
他不見阿言,阿言便也不去見他。
如果阿言這麼不在意他,他又何必熱臉去貼阿言的冷屁股?
癸深每晚來阿言房門前站站,也不過是想碰碰運氣,也許阿言出來了,他可以假裝偶遇,然後阿言會告訴他冷著他的原因。
而後誤會冰釋,他和阿言還像以前一樣,甚至更好。
今晚,癸深第三次來到阿言房門前,他聽見阿言的房間裡,傳來一陣陣水聲。
怎麼有水聲呢?難道阿言在洗臉?
癸深查覺旁邊有一扇窗,關得不是很緊密,有一個縫隙,燭光從中透了出來。
癸深移動腳步,走向那扇窗,從窗隙裡,他看見阿言背對著他。
正在洗澡。
浴桶上方,是阿言光潔的裸背。
浴桶上方一絲不掛,那下方呢?還用說嗎?
癸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想要抑制快要從胸腔跳出來的心臟,卻因為北原空氣寒冷,讓他差點咳了出來!
擔心驚動阿言,他勉強把咳意壓下。
阿言聽見背後,房門被輕輕推開的聲音。
他沒有回頭,他知道進來的,就是他在等的那個人。
癸深那隻略粗,帶著薄繭的手掌,從阿言平滑的裸肩,摩娑至他胸前、下腹。
「阿言,你故意的……你就是想勾引我……」
癸深的氣息,在阿言耳邊響起,他的兩隻手,摟住了阿言的裸身,他的唇齒,咬嚙著阿言的耳垂。
「那……少爺喜歡嗎?」
阿言故意將頭一側,正好和癸深的唇吻到了一起。
「阿言…..阿言…….你這小妖精…….」
癸深已經心癢難搔了兩三天,阿言卻又用這般活色生香的景象勾引他,兩人一面熱吻,癸深一把將阿言抱起,丟在床榻,整個人壓了上去!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