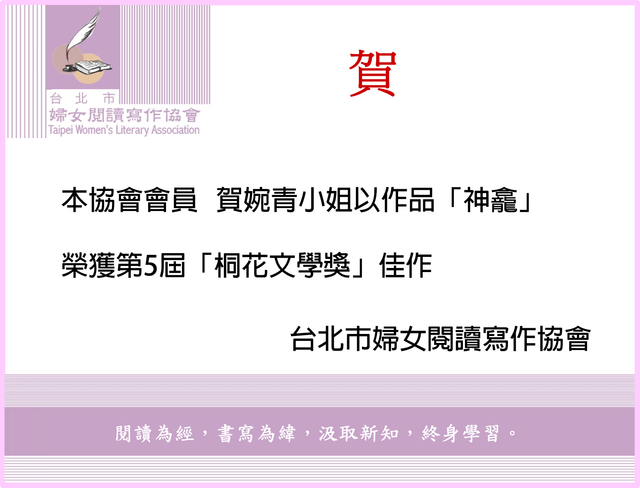
神龕◎賀婉青
每天一大早,外婆撕下牆上的大字日曆,開始她忙碌的一天。她搬出餐桌下的板凳,蹬上,向架在半空中的神龕舉香膜拜。
我不明白為什麼家裡的神龕不立在地面上,卻和四處遷徙、客居的外公外婆一樣,沒有根,懸在半空中?祂的境遇竟和我們一樣,蝸居在擁擠的都市、狹小的空間?或許是保留神龕的權宜之計。
多數時候,我低頭在餐桌上吃早餐,偶一抬頭,外婆拜拜挺直的雙腿,就像一棵札了深根的神木,屹立不搖。我從不懷疑她的穩固性。
有回她插香沒站穩,失足跌下來,我才發覺神木也有年紀的。尤其,在外公過世後,神木的根基像被土石流沖刷過,快速鬆動,搖搖欲墜。
外婆的踮上跳下,總讓我有折枝的憂慮,我勸她,二十多年了,理當拜夠了,佛在心中坐,為什麼非要拘泥形式?
怎麼能?以前拜佛祖、觀音、祖先,現在加上阿公,理當拜得更勤快。
阿公做仙了,在天上保佑我們,他不會想看到您摔傷的。
外婆有一份對外公海誓山盟的老式堅持,她喃喃有詞在凳上站許久,說說停停,我知道她在跟外公談心,如同外公在她身旁。
她閉眼捻香膜拜時,或許是每日身心最安定的一刻,子孫都工作,常不在身邊,只有牌位,堅貞地守著她。
依然,我看著外婆站上板凳拜拜,眼底卻是關係我升遷的上司,有時再叨唸幾句外婆不應踮上跳下,執着在膜拜的形式,更無心知道外婆頭上的神龕裡,到底供奉誰?
生活在同一個空間,我們卻像飛禽與走獸,各有領域,互不交會。
擔憂的事還是發生。
外婆扭了腳,她不得不放棄登高,以手代香,仰頭膜拜。我鬆了口氣,外婆不再懸空;卻發現神木不再高大,是我這小樹茁壯了,還是老樹傾頹了?疑惑在腦子轉了幾秒,不真的在乎解答,思緖又回到,如何完成老闆交辦的任務上。
中元普渡,外婆攤開了折疊桌,插上了鮮花、擺上了水果、端上了雞鴨魚肉,再忸怩地接近我、要求我,代她爬上板凳,清一清神龕,再將牌位請下來放在陽台的供桌上祭祀。
登上板凳,發現我像草生的植物,不能臨風,彷彿一吹就倒;往下望,又感覺腳軟無力,一陣昏眩。外婆數十年如一日的登高禮拜,要克服對高度的恐懼,要準確的踏穩在小枱面的板凳上,憑藉的是她對宗教堅貞的信仰。我發現,外婆頂上的世界,是一個我不知道、也許是我認為不可能存在的極樂世界:沒有疑惑,沒有恐懼。
望向深幽的神龕,陌生的神祇一一清晰了起來:右邊一尊淨潔的白瓷觀音,似曾相識,這不是我當初親手抱回來的觀音嗎?我拿著一塊紅布,在煙霧瀰漫中,繞行香火繚繞的銅鑄大香爐,請出大佛分身,跟我回台灣。當時唯恐怠慢了這尊觀音,一路從山西大同石窟搭車、轉飛機親手抱回來的。仔細回想,不過是兩年前的事,我曾經緊密懷抱、相依為命的天神,竟被我遺忘在半空中,我甚至沒有察覺到衪的存在,而由外婆幫我日日朝拜著。
左邊是余氏列祖列宗的牌位,潤澤的木牌上被香熏出歲月的痕跡;旁邊新作的桃木牌,斗黑的大字寫著外公的名字,像是一對烏亮的大眼看著我。中間是佛祖的畫像,前方立著一座小香爐,頂上的米白色木板被香爐熏得漆黑,兩旁各有一盞蓮花燈,像是玻璃燈穿透我在俗世打滾的心。
原來這就是外婆日日駐足良久,告解身心,求安定的樂土;在這,我卻渾身不自在,彷彿諸神在瞋目相看。
外公從台中東勢到新竹內灣,再上台北打拼,半百時,買下人生第一棟房,不時領兒孫登上鋼筋蓋好,還未完工的新家,監督施工進度。且不時指指點點地說,這裡是餐廳,那兒是客房,你們來找外公、外婆,別怕沒地方住。屋成,外公拿羅盤、定方位,最後敲定在餐桌對側的牆,安上神龕,迎回余氏祖宗牌位,每日踮上跳下祭拜,好似告慰先祖,奮鬥漂泊的人生終於結束了。外公向祖先與眾神,稟報女兒出嫁、外孫出世等,站上神龕說話,變成外公的例行事務,彷彿用私密的話,寫日記給眾神,直到他中風。
外婆接下外公的祭拜重任,學他向神明稟報子孫的近況,並祈求牽手半輩子的外公,早日好轉。外公昏迷臥床,不能如常講解電視新聞時事,及讀報給不識字的外婆聽,外婆的世界不僅少了眼睛,陰暗無光,也成了靜默的空白。沒了電視聲、外公的聲音,僅剩外婆喃喃向菩薩求救,及召喚外公醒來的聲波在空間迴盪。我不敢對看外婆的無助,只偷偷在她祭祀閉眼時看她,緊蹙的眉眼下,常見淚痕斑斑。
外婆耐心地幫外公中風無力的肌肉按摩,盼望改日醒了,還能夠站起來。她不停地跟外公說話,回憶甘苦往事,時笑時嘆,追問外公還記得否?我不知道,祈禱是否真成了藥方,在人眼看不見的神秘中,成為一帖藥,外公真的好轉了。外公終於被喚醒,先坐而站,外婆扶外公,來回客廳練習走路,最後,倚著手杖自行走動。外婆的世界又亮了,雙眼雖然佈滿血絲,卻有火光。外公開始讀報給外婆聽,我恢復留紙條和早睡的外公、外婆溝通的習慣,一切回到過去,直到外公辭世。
外婆扭傷的腳好,又開始攀高。我的工作量愈來愈大,更加的早出晚歸,少了識字的外公做翻譯,以往寫在大字日曆背面的紙條也停寫了,和外婆的交談,只剩夜闌人靜餐桌上削好的一盤水果。
獨自咀嚼水果的同時,我常常翻弄著外婆撕下的日曆,細讀旁邊的小字:忌探病、解除;宜嫁娶、納采。
今天才到醫院看了剛生產的同事、將融資的股票斷頭,應該都是好事啊。宜嫁娶?忙得連相親的時間都抽不出,嫁誰啊?農民曆真是天上人間的故事,與我沒有什麼干係。
一晚,我循例躡手躡腳地進屋子,怕驚擾到已入睡的外婆。
「工作這麼晚才回來?」是遠嫁日本四阿姨的聲音,我這才想起外婆之前一直提,阿姨要返台探親。阿姨把燈扭亮,我們一起吃外婆削好的水果,在昏燈下談心。阿姨質疑我怎麼忙到連削水果的時間都沒了?
原來阿姨晚餐後幫外婆在廚房洗碗,看到外婆將桌上的水果,全去皮削塊,問她為什麼。外婆說有一回問我,桌上的蘋果怎麼不吃,我答沒空削,所以沒吃。自此外婆將水果都削切成塊。
我有點恍然,我真說過這話嗎?當時的我是漫不經心地應付外婆,還是真抽不出時間?
我開始質疑自己的信用了,我的有口無心,打動了疼孫的外婆,日日在夜裡削出一盤又一盤的愛,我卻沒發現箇中玄機,還理所當然地接受,一句謝也沒有。
我叨叨絮絮地要外婆不拘泥膜拜的形式,可她至少謹守著頭上三尺有神明,不打誑語;行禮如儀的形式讓她心安、理得。我自恃無形的心香卻因無框架、標準浮動而常走樣:我可以理直氣壯地因為加班,一次又一次打電話取消晩上帶外婆看牙醫的約診,叫外婆空等。
在金錢權力的世界裡,我麻木忙碌、無法思考,整天揣測上司的喜惡;卻不知外婆也在用心地推敲我的一言一行。當她喃喃自語在半空中朝拜她的極樂世界,低頭下望時,是否也在疼惜我這隻轉不出迷宮的小螞蟻?
曾經,認為外婆日日對過世的外公,喃喃有聲地傾訴是種病態的寄託,看來生病的人是我,我竟然可以漫不經心地忘了自己說過的話,辜負外婆對愛孫的仰賴,讓她在家中巴望。
真是病了,我像隻跑輪的小鼠,終日奔跑,卻不知方向。我看不到身邊最疼我的親人,卻花了最多的時間,和生命中只是過客的路人打交道。
我提早回家,吃完外婆做的晚飯及熱湯,幫忙收拾桌面及洗碗;陪外婆看她喜愛的歌仔戲,我才發現害羞的外婆,會忘我的隨著楊麗花輕聲哼唱;她洗完澡一定用洗衣板將貼身衣物洗淨晾起,使我想起小時候,也拿把小板凳,站在外婆身旁,學她打肥皂,在波浪板上搓揉衣服。我的小手使力不當,水晶肥皂一塊塊黏在衣服及洗衣板上,還靠外婆的大手又搓又揉才洗淨的。這一縷縷的往事就像似曾相識的神祇,一一清晰了起來,記憶雖需要時間沉澱,也需要足夠的空間,才能從容定居。
外婆不再堅持日日登高拜拜,有時讓我替她拜。我從剛蹬上的踉蹌不穩,如繩子牽引、沒有重心的木偶,轉成一步踏實,似擎天昂立的小樹;我想像自己是插接在外婆舊幹上的新枝,以同樣虔誠的心敬拜佛祖。
在這樣的高度中:眼前是慈眉善目的諸佛諸神、列祖列宗。我看清楚白衣觀音兩手各持淨瓶與柳枝:甘露灑下、用柔軟的柳條點化我;列祖列宗牌位上的木痕排列成歲月的年輪,壓出道道的庭訓,似要我繼往開來。
眼下的世界,依然炫目撩人,卻縮成一個小光點。我的焦慮、我的懼,也隨雙腿逐漸的打直,而跟燒盡的香泯滅成灰,還諸天地。

得獎感言:
這篇文章獻給我的外婆。外婆曾遺憾識字不多,我很榮幸成為外婆的筆,記錄她生命中動人的故事,從之前的〈外公看病〉到〈神龕〉,我書寫了外婆的赤子心、慈母情和客籍女人堅韌的生命力。
感恩評審的肯定,看到〈神龕〉中蘊藏的深意:我們心中的神龕也從容定居嗎,還是懸在半空中呢?
最感謝先生、媽媽、雙胞胎,在他們身上,我看到愛和生命力、及長期支持我寫作的親友,你們是堅貞的粉絲,也是靈感的來源,我愛你們。最後建議客委會,得獎文章除了文學出版價值外,也能引薦製成影像。〈神龕〉可以改編成單元劇或微電影,海內外客人眾多,除了社教意義也有票房價值。
作者認為「我心目中的文學不只是書寫,還是一種慈悲的態度。」目前正進行女性移民文學的長篇小說創作。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