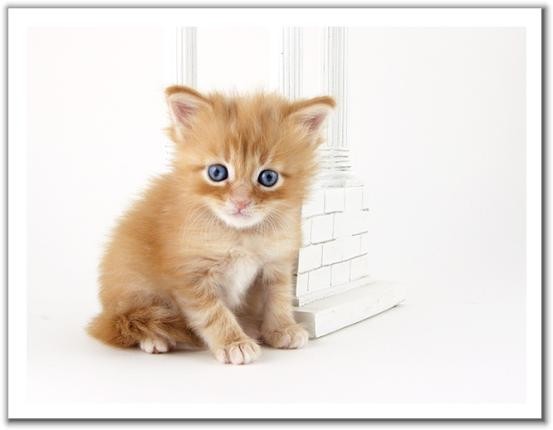
打從有記憶以來,我就瞭解到自己非常「害怕」見到「軟體動物」。例如:毛毛蟲、蠶寶寶、蚯蚓、顫蚓、水蛭、蛆……之類。因為光想像這些沒有骨骼,完全靠著收縮身體就能前進的軟趴趴怪物,就會讓我不由自主的打起寒顫,產生莫名的恐懼感。而且恐懼的程度,已非「誇張」兩字可形容。
前幾年從媒體報導得知,苗栗縣竹南鎮某些學校由於氣候或生態改變,突然出現大量的毛毛蟲。從記者採訪所拍攝出來的畫面看來,無論是教室內外的牆壁或走廊、溝渠,隨處可見蠕動爬行的黑色毛毛蟲。我常想,還好我不是在這些學校服務,否則要我置身這樣的工作環境,我不精神崩潰或瘋掉才怪。而今,我終於明白,我的「恐懼」完全是來自於母親的「遺傳」。
還記得學齡前,巷子後面有幾戶人家,為了遮蔭乘涼,在屋前搭起棚架栽種葡萄。每到葡萄成熟的季節,拇指般粗大的綠蟲蟲處處可見。有些頑皮的男孩子,會將牠們從葡萄葉上抓下來,用瓦楞紙盒收集起來。有一回,因為好奇心驅使,跟著哥哥趨前一看,還當場嚇到一路奔回家中。
國小一年級第一次參加學校的春季遠足,徒步到通霄海水浴場。當時沙灘上一大片防風林,正面臨著「黑角舞蛾」嚴重的危害。不只地面、連樹幹到處都爬滿噁心蠕動的毛毛蟲。我幾乎是緊繃著神經忍到中午,好不容易才盼到老師一聲令下-找處陰涼處吃飯包。沒想到才掀開便當蓋不久,一隻隨風擺盪許久的毛毛蟲,竟然聞香而至。就這樣不偏不倚掉進同學的飯包裡。為了這件超級恐怖的事,我的防禦細胞瞬間全部啟動,嘴巴吃著母親為我準備的荷包蛋,眼睛還得不時抬頭四面張望,就怕一個疏忽禍從天降。搞到最後,美味便當全泡湯,當天還剩下大半個回家。
國小五年級的時候,自然課本介紹到植物的重要害蟲,其中附錄了一整頁包括稻子、蔬果的害蟲。現已身為人師的我,當然知道那些教科書的編輯委員們,無非是想藉由這些真實照片,讓學生清楚了解到這些蛾類是如何危害植物的。只是當年那些爬滿孵化後的幼蟲圖片,就教我當場嚇得渾身起雞皮疙瘩。後來,連複習功課時,我都會一次翻好幾頁,打心底就想刻意跳過那頁屢屢讓我產生過度反應的噁心圖片。
有時隨母親蹲在廚房一角,幫忙著撿菜、洗菜。為了避開這些讓我魂飛魄散的綠色菜蟲,我會事先帶起手套,好降低不小心觸碰牠們的機會。但是每回面對突然出現眼前的綠色菜蟲,我還是會精神失控的發出尖叫聲,甚至一手甩開手上的葉菜。母親聞聲後,幾度語帶心疼與責備的語氣對我說:「妳這麼怕菜蟲,看妳以後怎麼嫁人?這樣如何能討婆婆的歡心?」事後證明,母親顯然是白操這份心了。因為婚後和婆婆住在一起的那段時間,在婆婆親眼目睹我的狀況後,不但沒有責備我,還貼心的體諒我對菜蟲的恐懼,常常在我下班回來之前,先將葉菜類挑好、洗好。
後來進入教育界,有段時間擔任自然科任教師。有幾次因課程或實驗需要,必須面對蚯蚓和蠶寶寶之類。為了不在學生面前出糗,我會事先讓學生明白老師對這些動物的恐懼,請他們在上課時務必遵守幾個重點:千萬不可以在未告知劉老師的情況下,突然在劉老師面前打開他們所帶來的盒裝蚯蚓或蠶寶寶。只是防不勝防,那麼多的學生裡頭,難免會遇上幾個粗心的孩子,屢屢挑戰著我的反射神經。
還有一回,和同事共同指導學生科展,必須帶領學生透過顯微鏡觀察水裡的微生物。正當我張大雙眼,全神貫注貼近接目鏡,示範該如何邊觀察、邊畫下綠藻美麗的外型時,沒想到視野突然迸出一隻不斷掙扎蠕動半透明軀體的恐怖份子-顫蚓。或許我誇張的驚叫聲嚇到身旁的孩子,害他們差點將上萬元的顯微鏡從桌緣扯下。
我常想,別人應該很難體會這些隨處可見的「綠蟲蟲」所帶給我的壓力與恐懼。就像我很難理解別人害怕蟑螂、老鼠的道理一樣。在我眼裡,老鼠跟毛茸茸的可愛寵物-兔子,外觀上其實也沒相差太遠。至於常於拖鞋底下逃命的蟑螂,外型上和其他昆蟲大抵上也沒什麼不同。我想,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對某些東西產生沒來由的恐懼感吧!只是該如何去克服這些恐懼,以免影響日常生活,這才是重點。
近幾年,先生迷上蝴蝶。常常為了進一步觀察蝴蝶的羽化過程,在頂樓陸續栽種許多各式蝴蝶喜歡的食草,像馬兜鈴、馬利筋、牛皮消、柑橘科植物等。最近更誇張,還將幾盆含笑花直接移進客廳裡擺放。上頭當然有我致命的天敵-青斑鳳蝶的幼蟲。起初,我有點生氣,不過後來仔細一想「危機就是轉機」。因為,根據古典制約理論裡的行為學派,是可以透過安排「刺激」與「反應」之間的相對關係,以逐步降低個人對某一惡劣刺激物的敏感度。換言之,我是應該感恩先生的安排。因為當前,他無非是幫我佈置了一個「對蟲蟲去敏感」的實驗方案。所以最近下班後,我會抽空蹲在盆栽旁,觀察這些「綠寶寶」好一會兒,並試著翻閱先生從書局買回來的蝴蝶圖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不只與身邊的蝴蝶共舞,也能夠接納她們童年「可愛」的模樣。
寧兒
【寧兒繼續說故事】
記得母親生前不只一次跟我們兄弟姐妹提及一段關於「稻蟲」的往事,那是一段發生於日據時代,非常不愉快的就學經驗。
當時台灣的稻米屢屢因病蟲危害,導致稻米產量銳減。雖然相關的農業單位,也投注相當大的人力、物力,期望在短期內研發出因應的對策。只是遠水救不了近火,後來竟然有人把歪腦筋動到小學生身上,規定每位小朋友,放假時要下水田幫忙除蟲。至於如何證明孩子們是否「誠實」響應這些政策呢?很簡單,就是規定每人於週一到校時,繳交一定數量的蟲蟲給日本老師驗收成果。
當年外公家靠海,雖然有幾分的沙埔地,家裡根本沒有水田。再加上母親從小就知道自己是童養媳這樣的特殊身分,雖然外公、外婆都很疼她。但是打心底就害怕「軟體動物」的母親,猶豫了半天,還是不敢開口跟忙碌的外公說出這項需要大人們協助,才能完成的家庭作業。
當年才小二的母親,為了這項缺交的家庭作業,還因此被日本男老師叫到講台前,當眾狠狠連甩兩巴掌。母親常苦笑著對我們說:其實當天,這還不是最嚴重的體罰,因為班上有位小男生繳不出作業,情急之下竟然異想天開的抓鹹蔭瓜裡滋生的蛆蛆來充當稻蟲。母親永遠忘不了當天那位小男生,幾乎是被日本男老師從前門一路踹到後門,只因擺明欺騙老師,罪加一等。隔天,當保正的二舅,為了此事還氣沖沖的帶著臉頰紅腫未消的母親,到學校要找日本老師理論。
結果呢?當然是不會有合理的結果。因為母親說:「以前有個老師出手過重,活生生打死一個鄉下人的小孩。最後,還不是家長自認倒楣將屍體抬回去埋葬。」
我常想,這應該也是母親生前一提起日本統治台灣,就會忍不住咬牙切齒的原因之一吧!
寧兒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