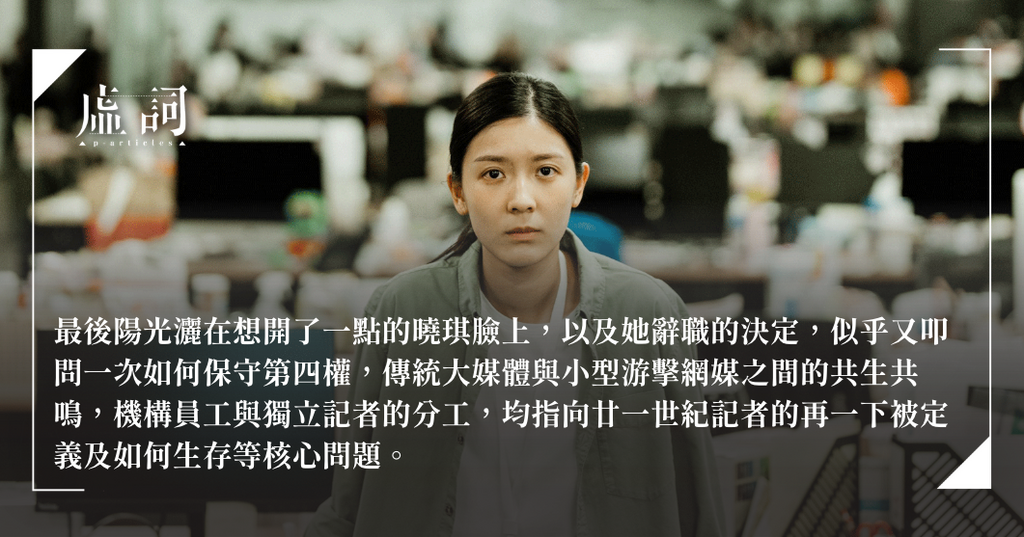
最初的三十分鐘,對我來說還滿動魄驚心的。不是因內容有多曲折或淒慘,而是未進場前對不論故事所說的真實事件,乃至導演及演員組合,也令我滿期待時,卻發現開首情節將所有香港護養院可見幾乎一切最壞情況共冶一爐,一個狹小的私人中心竟同時出現無人處理的老人屍體,被拋棄長者,失智老人,殘疾人士,弱智,情緒病患,還有邪惡看護,禽獸院長,奸商老闆,場面魔幻又刻意地堆砌出一個人間煉獄,以致我有心生不妙的念頭,團隊你們不是又回到一般港產片套路,賣慘,又是建構痛苦,大叫請關注弱勢,惹人可憐及同情的電影吧?
當然看下去知道不是。與其說故事在堆砌悲慘,不如說借主角新聞記者曉琪(余香凝飾)之眼,來旁觀他人痛苦,以報導的視角來超越單一事件的悲情,呈現關注社會現狀的高度。然而,電影厲害的地方是,借用幾個核心人物,反覆不斷質疑這種關注社會問題的新聞的意義,前線記者也是人,面對眼前血淋淋的現況,單是冷眼報導真的切合時宜嗎?老記者看透世事,一句人很善忘,會被明天的新聞取代記憶,那問題是為什麼記者還要努力做新聞?新來記者充滿熱情,但面對報導無用的現實,又可以做到什麼?另一邊律師在制度下無能為力,做出的決定也不被討好。以致,電影幾乎在批判每一個人物的每一種立場,不論是為求目的欺負弱勢的權力者,不求改變只求依賴權力,善用自己的弱來拿著數的弱者,甚至質疑心存正義,但可能只是借善良來自我滿足,站在道德高地卻危害身處險地的人的善心者。不過電影又沒有那種港產片常有的說教味,它就像那家悲慘護養院的情況一樣,擺設出各式各類痛苦的形狀,面對無可奈何的社會問題,人只是做了適切自己身份的選擇。新聞也守在只為了暴露問題,揭示醜陋的程度。
不過,越過了僅僅賣慘的肥皂劇,電影似仍不滿足於僅揭露痛苦的層次,而是通過三個(或三組)主要人物,來輕輕的,反對在苦難面前唯有默默承受及「旁觀」的論述,而是在因緣牽動之下,稍稍地改變自己的心態,積極介入自身或他人的困局,企圖改變一些狀況。契機當然是主角記者曉琪放蛇採訪,遇上痴呆的通伯(姜大衛飾)及弱智的小玲(梁雍婷飾)等人,由僅僅為爆料觀察,到逐漸投入他們的生活,反而剝開了自身的保護軀殼,起初只是燃起一直積壓多年對社會不公及新聞無力的怒火,到後來可說是越過一般記者的界線,渴求了解及幫忙更多,甚至希望在公義上為社會人士尋求更公平的待遇,而非只是揭露;另一邊的通伯,也因為她突然介入了自己已無所無謂的生活,也同樣卸下心房,可能是多年來首次向人展示自己只是扮傻,那個看透世情的一面。然而面對老友過世,院舍越加無良,令像這樣寧可扮蠢避世的老人,也嘗試踏出一步去幫忙;小玲,出鏡及描寫不多,卻是最令人記住的一個。原因是看似在整個劇情中身處於連表達也無力的最弱勢,卻在慘況時及之後,仍用自己的方式表達。梁雍婷的真挈演繹,令角色沒止於表現公式化的淒涼,而是通過無法言喻的行為,努力展露自己創傷,宣示痛苦,或者,更滲雜憤怒。以致,電影從宣傳也好,或最初一半劇情也是,都旨在揭露真相,但到了後期,人與人的關係及命運互相糾纏,那些角色,便開始有了行動,或更準確說是衝動,去突破那些既定而無奈的悲慘,一些沒有香港人覺得可以改變的現狀。然而最後,悲劇的現實似乎仍沒被撼動,反過來追求公義,卻釀成了別人的不幸,令想要幫助及揭發解決社會問題的曉琪,成為因此而無家可歸的人憎恨的對象。
因為面對黑暗時公義無力,更因爭取公義反而令人受傷的結局,讓最後那一場雨景,顯得極具重量。曉琪陷進不可對抗的綿密雨下,走過兩旁指責其害人的罵聲之間,場景猶如一場希臘悲劇,戲院的觀眾跟隨故事主人翁的故事,見證她越過難關,做盡正確的選擇,伸張正義,卻到頭來得不到民眾認同,輸給了命運,也不得善報。萬念俱灰的她最終停在通伯的面前,通伯的一句︰「不要為做對的事而內疚。」而拯救了曉琪的心靈,也同時拯救了在場情緒一直被壓抑的觀眾。至少,在我觀看的場次,前後左右的陌生觀眾並沒有在看到悲慘畫面而有動靜,卻聽了這一句後開始抽泣。我個人覺得香港觀眾在看戲時比較薄情,很難會為別人的不幸而傷感,但會為一些不憤、不爭氣,無可奈何的事情而共情。
新聞作為「第四權」,理應在為了公眾利益的前提下,通過報導對政府及社會之事,而起了監察,揭露社會黑暗,推動社會進步的用途。然而,電影正表達出現實中新聞的無力,它沒辦法改變世界,也不一定會在社會中激起漣漪,而且傳媒機構也逐漸自棄或失去公權力,紙媒沒落,大眾也少看主流媒體的新聞,其力量越發萎縮。然而,最後陽光灑在想開了一點的曉琪臉上,以及她辭職的決定,似乎又叩問一次如何保守第四權,傳統大媒體與小型游擊網媒之間的共生共鳴,機構員工與獨立記者的分工,均指向廿一世紀記者的再一下被定義及如何生存等核心問題。
只是,離開報館,個體深入訪問,說不一樣面向的故事,是否就代表更具行動力呢?就可以超越旁觀,介入事實?獨立記者失去大機構的權利、公眾認受性、資料及資源支援,又要如何採訪?在這個年代,還要有怎樣的能力及信念,才能堅持報導?這些問題電影已沒能觸及,可能留待觀眾繼續思考。電影只是不斷強調,面對巨大的體制及權力,我們全都是弱者。然而面對後現代思潮,人不再相信單一資訊時,除了旁觀、冷漠、放棄、只顧好自己,人還是可以獨立思考、分析判斷、關心、行動。曉琪說這叫善良,可能對當下香港人來說仍免不了肉麻,但用比較技術的詞彙——轉型憤怒,就可能更合我們理性的想法。那是不純粹針對個體加害者有否報應,而是關注通過報導,而期望可杜絕再有同類慘劇發生。那樣,或可在看似所有努力都是徒勞的糾結中超脫,因為那些影響力,定會暴露於白日之下,成為下一次的果,盡力的新聞如是,盡心的電影也如是,也如片尾播放周耀輝歌詞所描繪的世界一樣,令人嚮往。
文章已刊於《虛詞》︰https://p-articles.com/critics/4153.html?fbclid=IwAR0zDXdMvd7u-_huwrZhWH-UF2iMhE0MqNHoww2nabEKd6JOrZ_xm_GOA2k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