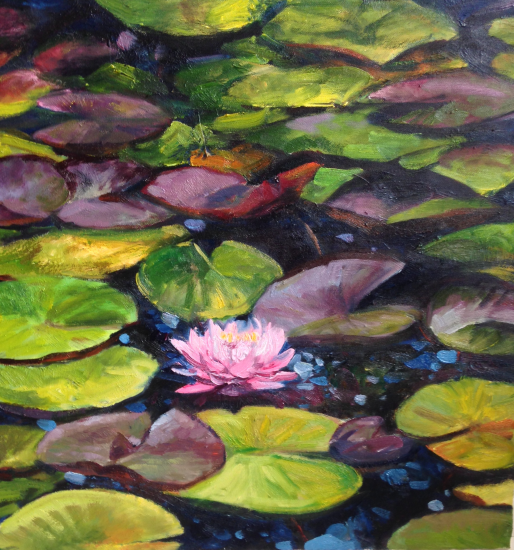
圖/李誌德
印地安那州夏日的腳步逐漸攀上最高峰,家家戶戶的冷氣機都嗡嗡作響,社區游泳池裡繽紛的水球被大人、小孩拋來拋去,在半空中畫上彩色弧線,好似要為北國短暫的夏日留下最燦爛的回憶,又好似在來回揮手,提前向大家預告,過了高峰期,印州的夏日將快速離去,泳池將人去水空,只剩層層水紋倒映天空的一片灰。
健群帶梅幸去做最後的產檢,當醫生說生產可能會延期時,梅幸開始心急,游說健群陪她去購物中心走走。他們在購物中心添購放嬰兒用品的五斗櫃,兩人同心合力抬櫃子進臥房,臉上都開著期待的花朵。
他們的臥房和以前大不同了,雙人床邊多了嬰兒床,粉藍色旋轉音樂吊飾會播放兒歌,可愛的大象、斑馬就在空中跟著轉圈兒,轉著父母對未來嬰兒的想像。長頸鹿布偶、玩具電話,已經在床上等待他們的小主人,床底下還有整箱的紙尿布。這些都是朋友們送來的禮物。
健群大姐與姐夫送的禮最大,嬰兒推車,停在樓下客廳蓄勢待發,彷彿在提醒梅幸:某種青春自在舊心情將結束,做母親的新角色要開鑼了,準備好了嗎?
應是抬重物有效,第二天清晨梅幸先有落紅,接著破水,孕育生命之泉就這樣熱熱地流了出來。原本要上班的健群衝去房間,背起早準備好的「生產包」,和他父母打了聲招呼,匆匆扶著梅幸走去停車場。一向如大哥般照顧梅幸的健群,這會兒顯得比梅幸緊張多了,車鑰匙半天插不進匙孔,開車時嘴唇還微微顫抖。事到臨頭,梅幸反不知從何緊張起。
因為破水,醫院安排梅幸立刻入院,進入待產室,陣痛尚未開始的梅幸,奇怪隔壁、再隔壁的產婦怎麼喊得呼天搶地。有那麼痛嗎?
同住一起的公婆,比梅幸更期待嬰兒的出世,「替嬰兒取名」是每天晚飯後的餘興節目,公公每天提出一張名單,如仲謀、仲傑、仲英等,還引經據典地說:「生子當如孫仲謀。」他的名單上找不到一個女孩名,因為生過五胎的婆婆曾仔細端詳過梅幸的肚子,看前又看後,還要她轉身再轉身,彷彿在挑選母牛。最後下定論:「身後看不到凸出的腹部,就是生男跡象。」婆婆還說,祖母替她父親選妾的時候就是這樣,在荷花池邊用嚴厲的眼光掃過一個又一個女子的腹部、臀部,確定選出能生育又旺家的女人,配給她父親做小,因為她母親生了她就打住。從此,她母親是夏日早枯的荷葉,躲在閣樓窗簾後面,悄悄偷看自己丈夫牽著入盛開荷花的新歡,坐進福特汽車。
就為婆婆說梅幸會生兒子,一向對梅幸不錯的大姐生氣了。
當年大姐因頭胎生女,第一次見公婆就遭白眼相待,為此她好幾年走不出傷痛,直到替夫家生了個白胖兒子,才重新抬起頭來。現在她母親理當趾高氣揚給懷孕新媳婦點壓力,讓她受些罪,怎麼還沒生就挑好話說?大姐不開心,將住在她大房子裡的父母請回健群、梅幸的小公寓,讓大腹便便的梅幸去伺候。
婆婆、大姐這對母女,過去就有不少情結尚未解開,現在為一句話又多了一筆愛恨情仇。當婆婆氣呼呼地說,以後再不去女兒家住時,梅幸心一沈,手上端的盤子也更重了。
梅幸一再請求,婆婆才勉強搪塞了幾個女孩名應景,公公則堅持己見,不取女孩名。他迷信,怕取了女孩名會生女孩。
梅幸遠在台灣的父母第一次升格為阿公阿嬤,特別興奮地送來一些名字,但一再叮嚀:「僅供參考,一切以婆家為重。」梅幸在諸多名字中,找到雙方父母的交集:「仲傑」,就決定兒子的名字,特意避開男女雙方誰尊、誰卑的潛規則。至於女孩,她選父親送來的「天麗」,反正公婆完全不在意孫女的名字,而天生麗質該是父母對女兒最好的盼望了。
陣痛尚不嚴重的梅幸,最尷尬的是隨時有不同的醫生,年輕又帥,輪番進來關心她的開指進度,說著梅幸不懂的數目,讓梅幸成了公開展示的物件。彼時尚未有超音波測性別這回事,他們用聽診器在梅幸腹部來回幾趟之後,異口同聲地說:「心跳得快,是女孩。」
難道經驗豐富的婆婆失了準頭?千年來的「生男生女推算表」敵不過一個金屬圓頭儀器?梅幸開始擔心,如果生個女兒,公婆的態度會不會轉變?健群呢?她的命運會像大姐嗎?
她生自己的氣,什麼年代了,怎麼還是擺脫不掉古文明留下來的封建思想?女人可以站起來保護自己和女兒啊。
醫師看梅幸進度很慢,怕產婦與嬰兒感染細菌,決定打催生針。這一針下去,陣陣脹痛有如波波海浪,自不知名的遠方洶湧襲來,此刻,她才從不夠真實的夢中驚醒,第一次深刻感受腹中靠臍帶相連的,是她的生命共同體,她創造的胎兒是個活生生的生命。
原來,分娩是要將兩個合而為一的生命硬生生地拆開,撕裂,將母親置之死地而後生。梅幸有如面臨死亡前的痛楚。「有死才有生」,梅幸想起她小時在教會裡聽過的歌。
梅幸痛得混身無力,喊不出來,隔壁、再隔壁的產婦又傳來一聲聲的嚎叫。她們哪來的力氣?
健群提醒她做拉梅茲呼吸,抵抗子宮收縮的壓力,但似乎對疼痛無啥幫助,最後還是要靠局部止痛針,梅幸才得以熬過這關鍵時刻。
護士開始遊說健群進產房,和梅幸共同經歷孩子出生的神聖片刻。這對當年來自東方的他們很突兀,健群一個勁地推辭,說他看見血,會暈倒。梅幸第一次知道強壯如大樹時時保護她的健群會暈倒。
梅幸選擇在最後生產時半身麻醉,她要頭腦清醒地見證自己孩子出世的全部過程。
梅幸被推進產房,健群也終被說服進了產房,坐在梅幸床頭位置,護士在床腳架設起大大的圓鏡,那角度被調了幾次,確定想看的、不想看的,都不會錯過。老外醫師、護士,開心宣布梅幸會生個漂亮女兒,所以接生的小毛巾、毯子清一色粉紅色。
健群在梅幸耳邊輕輕的說:「沒關係,生女兒也一樣好!」一個「也」字,讓梅幸聽出來生兒生女真的不一樣。醫學再進步,生產對母親還是種冒險,但眼前新生命的性別似乎比產婦的安危,更直得關注。
在脊髓打入半身麻醉後的梅幸沒有任何疼痛了,分娩成了護理長的工作。護理長努力地推、擠,並高喊:「用力,再用力。」梅幸滿身大汗,聽到醫生說:「頭太大,要再剪、再剪。」有刀剪聲,卻毫無疼痛感。梅幸看鏡子,像在看一齣戲。
「頭出來了,看到臉,很秀氣,應是女生,女生……」
好一段沉默,四周怎麼如此靜寂,梅幸聽到自己太陽穴突、突跳動,她等待命運的宣判。
「嗄?是個男嬰!」醫師與護理長失望地驚呼。
東方婆婆贏了。
「恭喜順產,但我們只能用粉紅毯子包起這個小男嬰。」
或許太過緊張、焦慮,健群一鬆懈,整個頭幾乎跌到梅幸的枕頭上,梅幸看到一行清淚,滑下他的臉頰,落在她的臉龐上,和她滿臉的汗珠匯成一股水流。
陣陣癱軟襲捲梅幸,她在嬰兒啼哭聲中感受暖流湧自心底。窗外琥珀色的陽光逐漸轉紅、轉暗。晚霞璀璨如煙花,不知為誰在天邊一朵一朵地燃燒起來。
(本文刊於2017/06/20中華日報副刊)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