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釋迦族的秘聞─
釋迦族(Sakya),古印度的一個種族,約在西元前一千年出現,居住地位於古印度東部、接近今尼泊爾地方的一個小部落,「佛陀」釋迦牟尼出生於此。西元前6世紀至5世紀間,釋迦族形成自己的小型城邦,都城設於迦毘羅衛城,依附於憍薩羅國。佛陀在世時迦毘羅衛城為毘琉璃王所滅,釋迦族參與了佛陀入滅後的八王分舍利。
釋迦族自稱為印度甘蔗王(Ikshvaku)的後裔,源自古代傳說的伊克什瓦庫王朝(Ikshvaku dynasty),與《羅摩衍那》的主角羅摩同出一系,屬於剎帝利種姓。釋迦族以太陽為崇拜對象。
毘琉璃王時,憍薩羅國進攻釋迦族,迦毗羅衛城遭屠城,自此亡國。
南傳佛教經典並無釋迦族被滅說法,佛陀涅槃後,釋迦族人有參與後事。西元1898年,英國工程師佩普(William Claxton Peppe)在比普羅瓦一座直徑約35公尺、已經崩毀的磚造舍利塔中,挖出了五個裝有遺骨的舍利容器,在其中一個滑石製的舍利壺上,以古老的波羅米文字刻著:「這是釋迦族佛陀世尊的舍利容器,乃是有名的釋迦族兄弟與其姊妹、其妻子等共同奉祠之處。」這個發現為佛陀的歷史真實性提出了強有力的新證明,轟動了當時的考古界,並引起了巨大的爭議。
依斯里蘭卡佛教歷史文獻《大史》及耆那教文獻《Punyashrava Katha Kosh》所記載,部分釋迦族人為躲避屠殺從迦毗羅衛城逃到毗發瓦那(Pipphalvana),因當地生存著許多被視為聖鳥的孔雀,釋迦族人便化名為「孔雀族人」(Maurya)隱居於此,成為後來孔雀王朝的先祖。
現代尼瓦爾人的金匠有釋迦族,自稱是由釋迦牟尼賜姓,但源自古代釋迦族並非不可能。
19世紀開始,西方學者發現,現存婆羅門與剎帝利氏族的系譜有長久的偽造傳統。低階層婆羅門會為各地部落領導人偽造出身,讓他們可以成為剎帝利氏族。因此剎帝利階級的起源並不像傳統相信的,起源於單一雅利安人祖先,而是由印度各地原住部落民所形成。
《長阿含經》〈世記經〉中記載人類世界起源於閻浮提,閻浮提中第一個造的城為瞻婆城,接下來為伽屍婆羅捺城與王舍城。這些地方皆位於印度東方、恆河流域中下游,這些神話說明釋迦族出身於此。
釋迦族自稱源自雅利安人。但是因為釋迦族所處偏遠、僻處婆羅門文化圈之外,雅利安人到達的時間很晚,被認為是未開化地區,所以也可能是源自當地土著民族的血統而不是純粹的雅利安人種。在《長阿含經》中記載,在釋迦族之外,俱利、冥寧、跋耆、末羅、酥摩等五族也受到釋迦牟尼佛的影響;這些小族都居住在印度東方,從恆河流域兩岸一直到喜馬拉雅山區,擁有相同神話,彼此相互通婚,可能也源自同一個祖先。
《雜阿含經》中曾記載釋迦牟尼被婆羅門誤認為賤民的故事。領群特又稱旃荼羅,在南傳佛教《小部》《經集》中,稱為毘舍離人(Vasalaka)。毘舍離屬跋耆族,釋迦牟尼也被認為出身於此,代表兩族之間關係緊密。佛陀堂弟阿難,被稱為鞞提訶牟尼,即毘提訶族的聖者,這也代表釋迦族與毗提訶族之間可能有著親緣關係。
《翻譯名義集》卷一:「瞿曇,或憍曇彌,或俱譚。西域記云:喬達摩,舊雲瞿曇,訛略也。古翻甘蔗、泥土等。南山曰:非也。瞿曇,星名,從星立稱。至於後代,改姓釋迦。慈恩云:釋迦之群望也。文句曰:瞿曇,此雲純淑,應法師翻為『地最勝』,謂除天外,人類中此族最勝。」
釋迦族至高無上,皆是菩薩示現。《大方等無想經》這樣開示釋迦族:「提婆達多。真實生於釋迦如來淨種姓中。不生畜生。若言釋種作諸惡者。無有是處。提婆達多所行惡行。為欲顯示釋迦如來功德力故。釋種中生名禿人者亦無是處。」又云:「大婆羅門。如來世尊常所稱讚。黃頭大士即是提婆達多比丘。六群比丘亦大菩薩。」祖庭事苑(8卷)對黃頭的解釋:梵雲迦毗羅。此言黃頭。以佛生迦毗羅國。就生處而稱佛為黃頭大士也。得出結論:釋迦族這個種族皆是黃頭,迦毗羅衛城翻譯成漢文即是黃頭種族城。這是很多所謂考證者忽略的地方。從釋迦族人示現瞧不起琉璃王的例子,則可看出釋迦族在那個時代的種姓較高貴。
《雜阿含經》卷四:「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缽,入王舍城乞食。次第乞食,至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舍。時,婆羅門手執木杓,盛諸飲食,供養火具,住於門邊。遙見佛來,見已,白佛,作是言:住!住!領群特!慎勿近我門!」
古印度時代,賤民只能居住村外,不可與婆羅門接觸,只能從事被認為是最低賤的職業,如抬死屍、清除糞便等。走在路上,賤民要佩帶特殊的標記,口中要不斷發出特殊的聲音,或敲擊某種器物,以提示高級種姓的人及時躲避。婆羅門如果接觸了賤民,則認為是一件倒霉的事,回去之後要舉行淨身儀式。佛經記載,有個婆羅門,口渴難耐,喝了首陀羅水,事後反應過來,寧可自殺。
正因為佛陀種姓特殊高貴,威德無上,才能攝持賤民加入僧團。基於古印度種姓制度,這個婆羅門對佛陀說,不要進我家門,也就不難理解了。在種姓制度森嚴的古印度,要不是佛陀種姓特殊高貴,這個婆羅門連搭理都不會搭理;要不是佛陀種姓特殊高貴,連接觸婆羅門、剎帝利的機會都不會有,何況說服婆羅門和剎帝利?釋迦族只有是人類最勝種族,才有攝持一切種族的基礎。在那個時代,佛陀打破種姓制度,攝持一切眾生(包括不可接觸賤民)的作為,簡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反對佛教的婆羅門和剎帝利應該很清楚釋迦族種姓,不然早在種姓問題上大作文章。時至今天,印度不可接觸賤民,還處在水深火熱當中。可以想像,佛陀威德是多麼強勢,不然別說布教,就是生存下去都是問題。

釋迦族逃亡後尼泊爾佛教發生了什麼?
許多佛弟子對“琉璃王滅釋種”的歷史和前緣耳熟能詳,但對釋迦族(Śākya)遭滅族後的經歷卻鮮為人知。人們對今日尼泊爾大乘佛教的認知比較籠統,只有少數學者瞭解佛陀後裔對佛法的繼承和梵文佛典的保護。加德滿都谷地的釋迦族人並非尼泊爾佛教的神秘面紗,鳳凰佛教顧問導師明賢法師獨家撰文揭開釋迦族逃亡及傳承佛教的歷史進程。
文獻與口傳:釋迦族逃亡及生存細節
在充滿信仰氣息的加德滿都谷地,釋迦族是一個特別帶有宗教性質的族群。據當地的釋迦族學者介紹,釋迦族的人口超過30萬之多,他們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後人。
大乘佛教的佛弟子從來不會對佛陀肉身的寂滅抱有絕望的情緒,因為他們有著對於佛陀法報化三身的基本理解,並相信自己終有一天能成為佛陀“法子”,回歸“如來家族”中——“釋迦”早已成為一個超越血緣關係的姓氏。但是有一天,當親眼見到高山下的加德滿都谷地,依然有那麼多與佛陀有著遙遠血緣聯繫的釋迦族人在日夜生息時,心頭油然而生親切和歡喜,仿佛這是一份佛陀悄然留給後人的、“佛陀故鄉依然存在佛教”之外的驚喜。
在法顯大師的記錄中,古迦毗羅衛城因為琉璃王報怨的屠戮,城內的釋迦人已經消失了。另外《釋迦譜》的記載也只是提及當時琉璃王誅釋種,殺了九千九百九十萬人,血流成河。許多想出逃的釋迦族人“從東門出還複從西門入,從南門出還複從北門入”,目犍連尊者欲以一缽救五百優秀族人,但終究化為血水。釋迦滅族的公案和前緣是後人異常關注的,相應的也想當然留下一個模糊的印象——釋迦族被滅盡而無後裔,以至於今日鮮有人關注和了知屠城之後的歷史。
有觀點認為,當前尼泊爾佛教只是印度中世紀至晚期佛教的延續,加德滿都谷地是印度佛教遭滅頂之災後逃難佛教徒的庇所。但在尼泊爾當地的佛教傳承看來,尼泊爾佛教可以直接追溯到佛陀時代,佛陀出生在藍毗尼花園,也親自到過加德滿都谷地。而從釋迦族的傳承來看,包括印度琉璃王滅族和巽伽王朝暴力鎮壓佛教後的避難在內,釋迦族在歷史上至少有兩次比較集中地遷居到加德滿都谷地,而這兩次避難都發生在西元前。
尼泊爾的釋迦族人堅信,根據祖輩相傳的歷史,當年迦毗羅衛原住地的先祖並沒有被滅盡,少數倖存者有的逃到了喀什米爾,有的逃到了其他地方。今天加德滿都谷地的釋迦族人就是當初逃難先人的後裔。
這不僅是口耳相傳的歷史,也有佛教經典的記載為證。已故的明•巴哈杜如•釋迦教授和他的兒子米蘭•釋迦教授指出,梵本mūlasarvāstivāda vinaya(《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即戒律)中就有對這一情況的記載。我們發現,漢語大藏經中也有相應的文獻。西元7世紀,義淨三藏翻譯的《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中就有類似的記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惡生太子(即琉璃王)以迷癡故,殺劫比羅城諸釋種。時城中或有走向西者,或有投泥婆羅(《舊唐書•西戎傳•泥婆羅》:“ 泥婆羅國,在吐蕃西。其俗翦發與眉齊,穿耳,揎以竹筩牛角,綴至肩者以為姣麗。食用手,無匕箸。其器皆銅。多商賈,少田作。”)。入泥婆羅者,皆是具壽阿難陀眷屬。後室羅筏城商人,持諸貨物向泥婆羅,釋種見商人已,問曰:“我今遭斯困苦逼,阿難陀聖者豈不來此看我等耶?”時諸商人一心憶念,交易既了,還至室羅筏城,具報阿難陀聖者,眷屬在泥婆羅,作如是言。聖者阿難陀,于諸商人聞是語已,情懷愴然,即往泥婆羅國。國極寒雪,阿難陀手腳劈裂,回還室羅筏城。諸苾芻見已,問言:“阿難陀!汝先手腳柔軟,猶如於舌,因何如是劈裂?”答言:“泥婆羅國,地近雪山。由風雪故,令我腳手如是。”又問:“汝之眷屬,于彼雲何存活?”報言:“彼著富羅(即鞋)。”又問:“汝何故不著?”報言:“佛未許著。”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寒雪處應著富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時諸釋種,于過去時不同業者出城而去,或往末羅國,或往泥波羅,或往其餘聚落城邑。若于昔時同惡業者,雖出東門,南門還入;南門出,西門入;西門出,北門入;北門出,東門入。
釋迦族當年逃亡的區域,玄奘大師《大唐西域記》亦有記載:誅釋西南,有四小窣堵波,四釋種拒軍處……毘盧釋迦嗣位之後,追複先辱,便興甲兵,至此屯軍。釋種四人躬耕畎畝,便即抗拒,兵寇退散,已而入城。族人以為承輪王之祚胤,為法王之宗子,敢行兇暴,安忍殺害,污辱宗門,絕親遠放。四人被逐,北趣雪山,一為烏仗那國王,一為梵衍那國王,一為呬摩呾羅國王,一為商彌國王,奕世傳業,苗裔不絕。
這是說當時有四位在田間耕作的釋迦族人最先見到了琉璃王的軍隊,而進行了武力抵抗。因為他們以暴力進行抵抗,造成了傷害生命的事實,有辱法王之宗,而受到了其他族人的呵責,並被“絕親遠放”。以此因緣,他們遠離故土,投奔四國,卻將釋迦族延的苗裔延續下來。
從這些經典記載來看,少部分業力不同的釋迦族人在滅族之難中倖存下來,逃往各地,其中一支就在加德滿都谷地駐紮下來並且延續到今天。依《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阿難尊者也曾因此前往尼波羅國看望族人,佛陀還因此制定了在雪寒地區可以穿鞋的戒律上的開緣。可見釋迦族的逃亡,佛陀當時也是了知的。
經典的隻言片語只是記錄了點滴片段,更多的經歷或許只能在歷史長河以及釋迦族人的代代相傳中保留下來。文獻的依據是一方面,但今天釋迦族的存在和族人的傳統或許就是對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的最好說明。
釋迦族逃亡後的生活:一直在加德滿都谷地修行
“自從釋迦族遷徙到此地開始就一直是這樣,我們依然在修行尼瓦爾佛教,一直修行,一直修行。”如果問及釋迦族存在的意義,族人今天都在幹什麼,釋迦族人一定會這樣帶著滿滿自豪感並且十分堅定地告訴你。
在加德滿都谷地,佛教是影響僅次於印度教的宗教。尼泊爾佛教經歷了佛陀時代的起源、阿育王時期的發展、梨車王朝最早受到的金剛乘的影響、末羅王朝時受印度教的排斥及僧團體系的變化、18世紀沙阿王朝印度教的衝擊,直到今天得到政府寬容的對待。無論是印度晚期金剛乘、藏傳佛教密宗的深度影響還是歷史上印度教不斷地擠壓,大乘佛教還是在尼泊爾保存下來了,這十分不易。其中,釋迦族的貢獻功不可沒。釋迦族並不是大乘佛法沒落的臺面撐持者,相反,他們就是鮮活的佛法傳人,是一直在修行的佛陀後裔。
釋迦族人遷徙到加德滿都谷地之初,就延續了原住地的佛法傳承,剃度為僧,別親出家,獻身佛教,與世無爭,是尼泊爾佛教的中堅力量。現在,釋迦族(Śākya,或稱Śākya bhikṣu)與金剛師(Vajrāchārya,寺院的金剛乘祭師)同屬於當地的僧侶階層(Gubhāju或Bare),而受到社會各界的尊重。
釋迦族(Śākya)與金剛師(Vajrāchārya)事實上都是屬於“在家的僧人”。他們都居住在稱為“Bahal”的社區——寺院與寺前庭院為中心的居民區,佛教徒之間有稱為Guthi的組織負責公共事務。釋迦族的男孩通常在7歲左右必須經歷一次出家。出家的時間過去是兩三年時間,後來逐漸改成4天。在這四天裏,出家的孩子全部依照十戒來經歷寺院生活,並非只是儀式。“出家”在釋迦族人並不是意味著依比丘戒進行永久獨身生活的開始,而是標誌著大乘乃至金剛乘修行的開始。比如,接受剃度後的釋迦族男孩會得到類似這樣的教誡:“你已經經歷了聲聞乘的修行,現在將進入大乘佛法的修行。你將參與金剛乘的儀式,在經歷更高的修行後,你將了知什麼是chakrasamvara。”
相對而言,金剛師(Vajrāchārya)主要在寺院負責祭祀禮儀事務,而釋迦族人(Śākya)除了在寺院服務,也從事藝術、工巧、商業的工作。他們有自己的根本道場,依寺院生活而又進行在家的修行,穿著世俗的服裝並結婚。這樣的形態被稱為“在家的僧人”或“世俗的出家生活”,佛法在釋迦族人中最終以家族的形式傳承下來。

由於歷史的種種原因,如金剛乘、密宗的影響、國王的不支持,大乘佛教健全的出家體系和戒律體系在尼泊爾沒有得到全面的傳承。雖然這一度成為一些學者質疑尼泊爾佛教純粹性和可持續性的理由,但是我們依然看到,世代傳承佛陀教誨的釋迦族人對佛法的虔信和護持的無二用心並沒有被世俗的形式改變。他們堅持著久遠年代以來最純正無染的信仰,保有對三寶無上的信心和摯誠的皈命。
此心或許不如外在的戒律體系那樣顯而可見,卻足以支撐他們在加德滿都谷地綿延不斷地存在,以及為護持和修行佛法所做的一切努力與貢獻。而釋迦族人身為佛陀後裔的那一份光榮與使命,如同他們的先人在面對滅族之災時依然堅持的關於“法”的原則性一樣,表現得無比堅定和自信。這一份沒有在文獻著作中以文字形式記錄下來的虔誠是對佛陀精神的繼承,也是我們在這個幸運國度裏依然可以看到大乘佛法希望的最好證明。
偉大家族贏得世界尊重:釋迦族代代相傳保護梵文寫本佛典
歷史上,梵文佛典曾經隨著往來印度的各國僧侶和向各地傳法的印度僧人,傳播到中亞、中國、尼泊爾等地。佛典在漢地被翻譯成漢文藏經流傳至今,可梵文原本多數已經佚失。但是在西藏地區和尼泊爾,依然按保存著大量梵文寫本的佛典。
在尼泊爾,保護這些古老的佛典正是釋迦族人代代相傳的使命。尼泊爾佛教經歷了不同階段的盛衰,而當地梵本佛典保存的完好性與豐富性是令人驚歎和感動的。很久以來,這些佛典不為人知,直到1824年英國外交官何德遜作為外族人在尼泊爾發現並偷運出了大量的梵本,外界才知道釋迦族長久以來為佛教默默所做的偉大貢獻。
當時何德遜偷運走的梵文寫本佛典共381捆、200多種,分別存于下列英、法、印三國學術團體。繼何德遜的偷運之後,釋迦族人更好地將陸續發現的佛典寫本保護起來,今天在尼泊爾檔案館、加德滿都圖書館和釋迦族的道場中依然收藏著大量完好的梵文佛典寫本。
根據現有的材料,這些梵本佛典最早進入尼泊爾的時間或許可以追溯到西元10世紀。當時,隨著印度佛教的衰落,大批的印度佛教的出家人從印度逃亡至尼泊爾,並帶來了那爛陀寺、超岸寺等重要寺院所藏的經卷佛典和其他文獻。加德滿都谷地接納了這些珍貴的經典,也接納了當時印度佛教的傳統。保護佛典的方法除了珍藏,還有抄寫經卷。
從西元920年到1768年,加德滿都谷地的釋迦族僧人和金剛師,一直沒有停止過傳抄經卷的傳統,直到今天也是這樣。據統計在末羅王朝末期,尼泊爾就存有有9000種27300卷經卷。傳抄的梵文寫本主要以天城體、蘭劄體和尼泊爾當地的尼瓦體、Bhujimol四種文字寫就。印度傳來的梵文寫本寫于貝葉上,尼泊爾傳抄的經卷則寫於靛藍紙和棕櫚葉紙、Haritalika紙、Thyasaphu紙等當地手工製作的紙張上。
現代對梵文佛典的保護除了傳統的方式,主要採用了整理、轉寫、校刊、微縮文獻、檔案館藏、編目、數位化等方式。尼泊爾檔案館就曾出版過一份完整收錄當前所知尼泊爾梵文寫本佛典的目錄,其中也包括了尼泊爾•德國梵文寫本聯合保護專案的微縮文獻目錄。這份目錄所收錄的梵文佛典寫本共計1829種。從這些資料裏我們可以看到現有梵文寫本的大致分類,屬於佛教的包括:佛經、譬喻、本生經、密續、陀羅尼。此外還有頌與史詩、吠陀、karmakāṇḍa(祭祀儀式)、故事、吟誦的長行、繪畫等。
當前修行人群中的“密宗熱”、世界學術界的“梵文原典熱”之下,人們不難瞭解梵文佛典原典的重要性,並震撼于當年西方人對這些寫本的發現,但是卻少有人關注到作為佛陀後裔的釋迦族人在保護佛典、傳承佛法上長年所做的與世無爭的努力。正因為他們的保護,我們今天才有幸依然可以看到這些古老的佛典,而其中就有大量的大乘經典。在今天的世界人口中,釋迦族所占比重可謂相當之少,但他們為人類的宗教和文化所作出的貢獻卻是傑出並且無二的。
歷史的變遷總是有其複雜的因緣而出乎人們的意料。從當年逃亡的佛陀家族到今天保護佛教作出偉大貢獻的尼泊爾佛教行者,站在世人面前的釋迦族人早已洗盡了惡緣帶來的殘酷氣息,而將佛弟子的虔誠、堅忍與生機保留到當下。
從他們身上我們或者看到了佛陀時代釋迦族零星的高貴遺風,或者看到了在高山國度下經年護持佛法的不易,或者看到了堅守與問題並存的現狀。無論這是一番怎樣的景象,無論世人對此作出了怎樣的評價,作為佛陀的弟子、大乘佛法的修行者,有那麼幾分心意無疑首先需要向佛陀可敬的後裔表達,那就是目睹釋迦族人依舊存在並且一直在修行後的驚喜和欣慰、對釋迦族傳承佛法護持經典的無上的敬意與深切的感恩,以及對釋迦族和佛陀偉大教法最誠摯的祈願和希望。
關於大聖唐卡大聖唐卡以保護、宣傳和弘揚唐卡文化藝術為宗旨,以向世人真實地介紹唐卡藝術及有效保護其傳播與發展為目的,通過收集各種精美的藏地唐卡藝術藏品,每件藏品都表現出了傑出的工藝水準和獨特的民族審美情趣。
由於大多信徒的飾物均是普通材質,其能夠蘊含自然能量有限,縱然有大師開光效果亦會大打折扣。因此大聖唐卡秉承“臻(材質)、精(工藝)、靈(加持)的原則”,甄選最精緻的畫工作品,打造成可以傳世的工藝品,再由寺院高僧以自身的修行力、願力、佛力祈請諸佛菩薩、護法龍天開光加持,蕩滌掉開光物品自性中的塵垢,讓緣主時刻受到保護,祈福保安平善。

當年釋迦族遭受琉璃王滅族之災,族人是否真的被趕盡殺絕?在漢傳佛教中,本公案很多時候是用於說明“因果不虛”的道理,並且強調目犍連尊者救釋種失敗、“神通抵不過業力”,在滅族程度方面受到的關注似乎並不多。甚至一些人默認“滅族真的是被趕盡殺絕了”。然而,佛典裏幾乎一致明確記載了釋迦族人在這次慘案中有生還者,並未被趕緊殺絕。
佛經中記載的“琉璃王滅釋迦族種”公案
佛世時,琉璃王誅殺釋迦族的慘案是佛教中一則重要公案,並常用於闡釋佛法中緣起因果的道理。《增一阿含經》卷二十六、《彌沙塞部五分律》卷二十一、《四分律》卷四十一、《佛說琉璃王經》及《義足經》等數部佛教經律記載了這一公案:早年波斯匿王想向釋迦族聯姻修好,釋迦族自覺是優等的種族,便將當時王族的大將摩訶那摩的一個婢女充作公主,嫁給波斯匿王,成為王后。日後生得琉璃王子。琉璃王子八歲時回迦毗羅衛國,途中到一個講堂中休憩納涼,被看守辱駡為“婢女之子”。琉璃王子受辱後,便發惡願將來當國王後要消滅釋迦族。
琉璃王長大後,通過篡權當上了國王,果然糾集軍隊向迦毗羅衛國殺去。佛知其意,於是提前來到琉璃王行軍要道,琉璃王出於對佛陀的敬意不得已而退回。由竺法護大師翻譯的《佛說琉璃王經》雲:
王心念言:“先古所載,藏室秘讖,用兵征旅遇沙門者,轉回軍還,況今值佛,焉得進乎?”稽首佛足,即便反旅。
如此琉璃王三次出兵,每次都是遇佛在道中而返。第四次起兵時,佛知迦毗羅衛國人宿世業緣成熟,共業的果報不可避免,回到了僧團。
琉璃王殺入迦毗羅衛國後,釋迦族人由於佛陀的教化,雖然極為驍勇善射,但在抵擋敵人時誓不傷敵,於是慘遭殺戮。《佛說琉璃王經》云:得開門入,入殺門衛五百人,斬害不訾,生縛貴姓三萬人,埋著於地,但令頭現,驅迫群象,比足蹈殺,然後駕犁而耕其首……
目犍連尊者用神通將五百釋迦族人攝入缽內,帶出迦毗羅衛國,然而開缽時五百人卻已全部化為血水。
眼看釋迦族人慘遭殺害,在淨飯王去世後繼承政權的摩訶那摩王跳入河水中,請求琉璃王在其浮上水面之前不殺人。琉璃王答應後,摩訶那摩王為了拯救家族,用頭髮將自己綁到了河底的樹根上溺水而亡,為更多釋迦族人的逃出爭取了時間。
琉璃王發現摩訶那摩為族人而死,亦生後悔。《佛說琉璃王經》云:
王甚憐之,有慈哀心:“用門族故,自沈而死,其義若茲。吾為國主,不忍小忿,豈當急戰,使所害彌熾乎?”……琉璃王厚葬摩男,存寵其後,王平舍夷更立長,安慰畢訖,還舍衛國。
然而此時的迦毗羅衛城已是血流成河,慘遭焚毀。因此一滔天惡業,琉璃王及其軍隊在屠城後的七天便被大水所漂,全軍覆沒,琉璃王死後墮入阿鼻地獄。
釋迦族被滅後,佛陀講述了釋迦族今世受此苦難的過去因緣:往昔迦毗羅衛城有一魚村,人們以捕魚而食。當時大湖內有兩條大魚被捕,村中有小兒,雖然沒有親自捕魚,但見到人們捕魚時,他也心生歡喜。他也沒有吃過魚肉,只是覺得好玩,在大魚頭部敲打了三下。當時捕魚的那些人就是今日的釋迦族,當時兩條大魚,一條是琉璃王,另一條是好苦梵志(協助琉璃王討伐釋迦族之人),漁村中人就是現在被殺的釋迦族,而小孩就是釋迦佛。因為殺魚罪業深重,釋迦族在過去劫中受地獄苦。而佛陀當時敲打魚頭三下,現在就由於這個因緣而頭痛三天。
釋迦族並未被趕盡殺絕
但即便是這樣,釋迦族人仍有生還。《四分律》中就記載了摩訶那摩用生命為釋迦族爭取到了出逃的機會。時琉璃王見即生慈心言:“摩訶男(即摩訶那摩)乃為親裏,故不惜身命。”即敕人放諸釋種,彼即受教放之。
《五分律》也有相關記載:王便歎言:“乃能為親不惜身命。”即宣令三軍,若複有殺釋種者,軍法罪之。
甚至,在《佛說琉璃王經》中,除了相關的敍述,還更說明瞭具體出逃的人數比例:“前三億人畢對並命,次三億人蒙自次之,救得皆視息,奔突走脫,得全濟命。又三億人,修家供養,歡宴熙怡,伎樂自娛,不知外有並命之厄。……佛與弟子至迦維羅衛,見諸人民傷殘者多……”。
由此可見,釋迦族當時雖然慘遭屠殺,但並非被趕盡殺絕,仍有相當數量的釋迦族人得以大難得活。
釋迦族的遷徙和逃亡
《阿含經》中,還記載了當時釋迦族人因為業力成熟而導致逃亡的種種不順利:(摩訶那摩沉水期間)迦毗羅越城中諸釋,從東門出,複從南門入;或從南門出,還從北門入;或從西門出,而從北門入。
在上述涉及釋迦滅族慘案的經典中,只有《義足經》的記載稍有不同,是琉璃王得知摩訶那摩死訊後繼續屠城:以其時令諸釋得出城走……(大臣)見釋摩男在水底死,便還白王:“天子,甯知釋摩男持發繞樹根而死。”王即絞城中餘釋。
然而從中中可以看出,當時琉璃王並沒有繼續下令追殺已經逃出城的釋迦族人。經中還說:(佛)即與眾比丘俱,到逝心講堂。道經過諸釋死處,釋中尚有能語者。……佛及比丘悉坐。佛為諸釋廣說經法竟……
這一點,可與《佛說琉璃王經》的記載相互參證,即當時屠城時很多受傷的釋迦族人也存活了下來。
事實上,根據佛教歷史記載,一些對佛教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人就是釋迦族人。比如後秦時來到中國的佛陀跋陀羅(漢譯為“覺賢”)尊者,為中國譯出了六十卷《華嚴經》等重要經綸,成為著名的翻譯家,他正是來自迦毗羅衛的釋迦族人,系釋迦牟尼佛叔父甘露飯王的後裔。元代著名的佛教造像家前往中國北京主造白塔寺大白塔的阿尼哥,也是釋迦族裔。以暴制暴的抵抗遭到釋迦族(Shakya)驅逐。
另外一些文獻,則記錄了釋迦族更為感人的慈悲不殺的家風,如《增一阿含經》云:有釋童子,年向十五,名曰奢(或作“舍”)摩。聞流離王今在門外……獨與流離王共鬥。是時,奢摩童子多殺害兵眾。……奢摩童子即出國去,更不入迦毗羅越。
玄奘大師《大唐西域記》也記載了類似的因為對殘殺進行抵抗,而敢行兇暴,污辱宗門,違背安忍殺害遭到釋迦宗族流放的情況:(琉璃王進攻迦毗羅衛國時)釋種四人,躬耕畎畝,便即抗拒,兵寇退散。已而入城,族人以為承輪王之祚胤、為法王之宗子,敢行兇暴,安忍殺害,污辱宗門,絕親遠放。四人被逐,北趣雪山。一為烏仗那國王,一為梵衍那(阿富汗巴米揚一帶)國王,一為摩羅國王,一為商彌國王。奕世傳業,苗裔不絕。
當時四位釋迦族人日後成為印度北方的四個國王。這四個國家在《大唐西域記》的描述中,烏仗那國筆墨最多。如云:烏仗那……有堵波,高六十餘尺,上軍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之將寂滅,告諸大眾:我涅盤後,烏仗那國上軍王,宜與舍利之分。……昔毗盧釋迦王(琉璃王)前伐諸釋,四人拒軍者,宗親擯逐,各事分飛。其一釋種……(與龍女結婚)……受龍指誨,便往行獻烏仗那王,躬舉其疊,釋種執其袂而刺之。……咸懼神武,推尊大位。……釋種既沒,其子嗣位,是為羅犀那王(唐言上軍)。
歷史上的烏仗那國位於今印度河上游及瓦特邦一帶,是佛法傳承中的重要國度。在密教中,烏仗那國是四大聖地之一,無量無邊的顯、密成就者在這裏,宛如遍地開花結果一般圓滿成就。
釋迦族逃亡後的生活:一直在加德滿都谷地修行
“自從釋迦族遷徙到此地開始就一直是這樣,我們依然在修行尼瓦爾佛教,一直修行,一直修行。”如果問及釋迦族存在的意義,族人今天都在幹什麼,釋迦族人一定會這樣帶著滿滿自豪感並且十分堅定地告訴你。
在加德滿都谷地,佛教是影響僅次於印度教的宗教。尼泊爾佛教經歷了佛陀時代的起源、阿育王時期的發展、梨車王朝最早受到的金剛乘的影響、末羅王朝時受印度教的排斥及僧團體系的變化、18世紀沙阿王朝印度教的衝擊,直到今天得到政府寬容的對待。無論是印度晚期金剛乘、藏傳佛教密宗的深度影響還是歷史上印度教不斷地擠壓,大乘佛教還是在尼泊爾保存下來了,這十分不易。其中,釋迦族的貢獻功不可沒。釋迦族並不是大乘佛法沒落的臺面撐持者,相反,他們就是鮮活的佛法傳人,是一直在修行的佛陀後裔。
釋迦族人遷徙到加德滿都谷地之初,就延續了原住地的佛法傳承,剃度為僧,別親出家,獻身佛教,與世無爭,是尼泊爾佛教的中堅力量。現在,釋迦族(ākya,或稱ākyabhiku)與金剛師(Vajrāchārya,寺院的金剛乘祭師)同屬於當地的僧侶階層(Gubhāju或Bare),而受到社會各界的尊重。
釋迦族(ākya)與金剛師(Vajrāchārya)事實上都是屬於“在家的僧人”。他們都居住在稱為“Bahal”的社區寺院與寺前庭院為中心的居民區,佛教徒之間有稱為Guthi的組織負責公共事務。釋迦族的男孩通常在7歲左右必須經歷一次出家。出家的時間過去是兩三年時間,後來逐漸改成4天。在這四天裏,出家的孩子全部依照十戒來經歷寺院生活,並非只是儀式。“出家”在釋迦族人並不是意味著依比丘戒進行永久獨身生活的開始,而是標誌著大乘乃至金剛乘修行的開始。比如,接受剃度後的釋迦族男孩會得到類似這樣的教誡:“你已經經歷了聲聞乘的修行,現在將進入大乘佛法的修行。你將參與金剛乘的儀式,在經歷更高的修行後,你將了知什麼是chakrasamvara。”
相對而言,金剛師(Vajrāchārya)主要在寺院負責祭祀禮儀事務,而釋迦族人(ākya)除了在寺院服務,也從事藝術、工巧、商業的工作。他們有自己的根本道場,依寺院生活而又進行在家的修行,穿著世俗的服裝並結婚。這樣的形態被稱為“在家的僧人”或“世俗的出家生活”,佛法在釋迦族人中最終以家族的形式傳承下來。
偉大家族贏得世界尊重:釋迦族代代相傳保護梵文寫本佛典
歷史上,梵文佛典曾經隨著往來印度的各國僧侶和向各地傳法的印度僧人,傳播到中亞、中國、尼泊爾等地。佛典在漢地被翻譯成漢文藏經流傳至今,可梵文原本多數已經佚失。但是在西藏地區和尼泊爾,依然按保存著大量梵文寫本的佛典。
在尼泊爾,保護這些古老的佛典正是釋迦族人代代相傳的使命。
尼泊爾佛教經歷了不同階段的盛衰,而當地梵本佛典保存的完好性與豐富性是令人驚歎和感動的。很久以來,這些佛典不為人知,直到1824年英國外交官何德遜作為外族人在尼泊爾發現並偷運出了大量的梵本,外界才知道釋迦族長久以來為佛教默默所做的偉大貢獻。
繼何德遜的偷運之後,釋迦族人更好地將陸續發現的佛典寫本保護起來,今天在尼泊爾檔案館、加德滿都圖書館和釋迦族的道場中依然收藏著大量完好的梵文佛典寫本。
根據現有的材料,這些梵本佛典最早進入尼泊爾的時間或許可以追溯到西元10世紀。當時,隨著印度佛教的衰落,大批的印度佛教的出家人從印度逃亡至尼泊爾,並帶來了那爛陀寺、超岸寺等重要寺院所藏的經卷佛典和其他文獻。加德滿都谷地接納了這些珍貴的經典,也接納了當時印度佛教的傳統。保護佛典的方法除了珍藏,還有抄寫經卷。
從西元920年到1768年,加德滿都谷地的釋迦族僧人和金剛師,一直沒有停止過傳抄經卷的傳統,直到今天也是這樣。據統計在末羅王朝末期,尼泊爾就存有有9000種27300卷經卷。傳抄的梵文寫本主要以天城體、蘭劄體和尼泊爾當地的尼瓦體、Bhujimol四種文字寫就。印度傳來的梵文寫本寫於貝葉上,尼泊爾傳抄的經卷則寫於靛藍紙和棕櫚葉紙、Haritalika紙、Thyasaphu紙等當地手工製作的紙張上。
現代對梵文佛典的保護除了傳統的方式,主要採用了整理、轉寫、校刊、微縮文獻、檔案館藏、編目、數位元化等方式。尼泊爾檔案館就曾出版過一份完整收錄當前所知尼泊爾梵文寫本佛典的目錄,其中也包括了尼泊爾?德國梵文寫本聯合保護專案的微縮文獻目錄。這份目錄所收錄的梵文佛典寫本共計1829種。從這些資料裏我們可以看到現有梵文寫本的大致分類,屬於佛教的包括:佛經、譬喻、本生經、密續、陀羅尼。此外還有頌與史詩、吠陀、karmakāa(祭祀儀式)、故事、吟誦的長行、繪畫等。
當前修行人群中的“密宗熱”、世界學術界的“梵文原典熱”之下,人們不難瞭解梵文佛典原典的重要性,並震撼於當年西方人對這些寫本的發現,但是卻少有人關注到作為佛陀後裔的釋迦族人在保護佛典、傳承佛法上長年所做的與世無爭的努力。正因為他們的保護,我們今天才有幸依然可以看到這些古老的佛典,而其中就有大量的大乘經典。在今天的世界人口中,釋迦族所占比重可謂相當之少,但他們為人類的宗教和文化所作出的貢獻卻是傑出並且無二的。
歷史的變遷總是有其複雜的因緣而出乎人們的意料。從當年逃亡的佛陀家族到今天保護佛教作出偉大貢獻的尼泊爾佛教行者,站在世人面前的釋迦族人早已洗盡了惡緣帶來的殘酷氣息,而將佛弟子的虔誠、堅忍與生機保留到當下。
從他們身上我們或者看到了佛陀時代釋迦族零星的高貴遺風,或者看到了在高山國度下經年護持佛法的不易,或者看到了堅守與問題並存的現狀。無論這是一番怎樣的景象,無論世人對此作出了怎樣的評價,作為佛陀的弟子、大乘佛法的修行者,有那麼幾分心意無疑首先需要向佛陀可敬的後裔表達,那就是目睹釋迦族人依舊存在並且一直在修行後的驚喜和欣慰、對釋迦族傳承佛法護持經典的無上的敬意與深切的感恩,以及對釋迦族和佛陀偉大教法最誠摯的祈願和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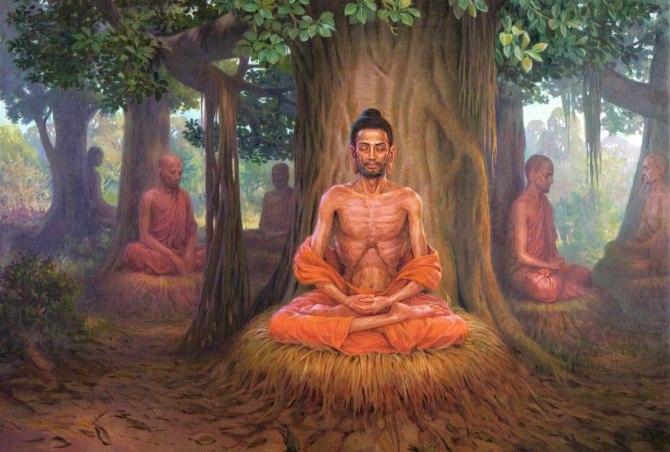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