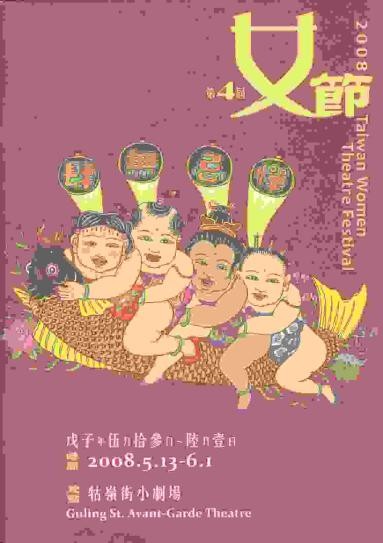
地點:牿嶺街小劇場
主辦:戲盒劇團
2008年5月15日,晚上7點半
《拎著提箱的女人》,編導:林欣怡(凹凸之外),演:李薇、王珂瑤
《不分》,編導演:杜思慧(戲盒劇團)
2008年5月22日,晚上7點半
《可以不存在》,編:蔡孟芬,導:胡心怡,演:蘇芷雲、許天俠、唐宛彤
《家!甜蜜的家?》,編導演:Helen Paris
2008年5月30日,晚上7點半
《我的敵人》,編導演:魏沁如、徐堰鈴
《我的天使朋友》,編:張嘉容,導:張嘉容、梁菲倚,演:梁菲倚、黃采儀、黃武山、施名帥
這次女節的主題叫作「肆無忌憚」,而我在看完六個演出作品之後,第一個跳出腦海的字眼是「私密」。像是林欣怡編導的《拎著提箱的女人》,演出進場時,除了一本女節的總節目冊之外,我還拿到一張以「凹凸之外」的名義所製作的A4單張雙面的節目單,翻開裡頭,佔去最大版面的是謝一誼和林欣怡的兩封通信,謝一誼描述其在紐約求學的生活、友誼、行旅與對世界文化的接觸和想像,林欣怡則描述身體旅行移動的時空模糊感與鄉關何處感,並提醒觀眾可以「帶著整理包包的心情」來看她所編導的作品。原本可能是私密的通信,在有意地安排設計下公開了,而讀者則因為這私密的公開得以參與其中,有趣的是,閱讀的經驗與詮解也只能是個人與私密的,即使可能有讀書會或共看一齣戲的集體經驗,但個人的理解與接受依然會是只有個人最私密的詩意空間,無人能夠闖入。私密公開化,創作者可能還是用自己的藝術語彙和方式在自說自話,通信的私密性與演出作品中三個女人的身體私密故事,在這私密與私密之間,有什麼共鳴或呼應之幽微處,那得觀眾自己去感悟。
三個女人分別是劇場中到處旅行的演員王珂瑤、拎著秘密提箱的中年演員李薇,以及影像中墮胎的演員王珂瑤,三者的形象在演出中似乎是各自陳述與獨白,旅行的移動、自由與跨越,提箱的秘密、沉重與令人不安,墮胎的痛苦與生命靈魂的消失,三個形象所透發出來的情緒與氛圍若有似無地或可聯結,當然也不需要刻意聯結,僅視為三幅不同的身體風景即可。旅行的身體充滿輕盈與歡快,在異文化與異文化的移動與跳躍之間,累績行旅的國家數與城市數成為她的存在,工作是為了存蓄下次的旅費,返家是為了休息與再出發。拎箱的身體晦暗沉重且了無生機,神情當中也充滿了苦澀與疑懼,她在人群當中尋找與詢問,處處無法為家的飄零感,似乎在為提箱裡的秘密找一種安放與救贖。相較之下,影像中的墮胎身體最具寫實感,尤其是那嬰屍的臉孔與幼小的身軀,演出結束後的首演酒會,還看到她們想要拍賣嬰屍翻模的模型,獨一無二的、私密的,嬰屍模型。希望我沒有記錯或看錯。
私密性的自由聯想與自動寫作,也在魏沁如和徐堰鈴聯合編導演的《我的敵人》出現。從企畫書的文案,到節目冊裡創作者的話(節目冊,頁25-6),我不斷地閱讀到其私密的生活瑣事,與詩化意象的文句,甚至可以再加上徐堰鈴過去已完成的文字劇本與編導作品,這龐大的喃喃自語,有時讀來甚至不知所云(從讀者的立場),綿密又細膩的文字書寫(抑或只是一種文字堆積的寫作遊戲?企圖填滿紙頁的空白?),讓人有種細瑣無焦的感覺,非詩非文,反敘事,反主題,言之無物,書寫不是為了投案子、闡發創作理念、介紹節目內容,書寫就只是為了書寫。也因為早知這樣的文字風格,造成我對這種文字的反閱讀,我將其視為線條與符號所組成的圖象,端視其整體版面的架構與設計,不太會去閱讀其中的內容,反敘事與反閱讀,是我找到的相應之道。
在劇場裡,兩個女人的身體有一套不斷重複演示的動作,配以不同的音樂與節奏,身體之間有許多張力與瑣碎的無聲對話,有些可能來自於日常生活身體的轉化,有些則是運用了接觸即興舞蹈的技巧,兩人似友似敵,均著黑色舞衣,散亂的中長髮,一個是舞者魏沁如的身體(但演得蠻多的),一個是演員徐堰鈴的身體(但跳得蠻多的),卻又像是鏡像的兩端,內弛外張地相互拉扯,作品的英文標題為The Enemy Within,形象化地將作品的某些精髓表達了出來。
私密之外,另外一個關鍵字可能是「不分」與「之間」,「不分」是不去為一件事物分類,「之間」是在事物之間的排除狀態,主動地不分,被動地被排除,被排除同時也是因為無法被歸類,歸類和排除,各自造成了不同的存在樣態,在《不分》和《可以不存在》這兩個作品裡頭,都可以看到這種尷尬,但經過一番調適之後,都能夠怡然自得,重拾存在感,重獲新生,當然也重新定義或重新批判規類和排除的武斷與狹隘。從作品所透發出來的情緒與潛意識裡,也可以感到《不分》比較是「我就是我」(I am who I am)的積極性、宣示性與主體性(所以我用who當關係代名詞),而《可以不存在》則是「我是『否我』」(I am what I am not)的消極性、無奈性與客體性(所以我用what當關係代名詞)。《不分》的粉紅歡樂氣息瀰漫整個劇場,「拉夫拉夫人的郵政信箱」與機智問答形式也逗樂了所有的觀眾,在輕鬆的氣氛當中,認識也接受了「不分」,連演員和觀眾也不分了。《可以不存在》則屬黑色暗沉系的,幾段突兀的男女對話處理地有點乾澀詭異,更多是主敘者演員蘇芷雲的苦悶與吶喊、疑惑與宣洩,頓悟之後,最後才得到一種「可以不存在」的釋懷。
同樣是探索負面情緒的還有《我的天使朋友》,這個劇名會令人聯想到邱吉爾稱他的憂鬱症為「黑狗」,甚至是羅素克洛所主演的電影《美麗境界》。這齣戲在探討現代都會單身女子(梁菲倚飾)的寂寞、人際疏離、精神憂鬱與妄想症(幻化出來的三個人物由黃采儀、黃武山、施名帥所飾演)。張嘉容的文字一直都充滿畫面,甚至是劇場的空間維度與人文的溫度,跨界的文字創作讓她迷戀劇場裡的魔幻寫實,但也多半隱身在導演與演員的身後,妥切地扮演「二線」角色。照她在節目冊裡所說,這次會挑起導演的責任是「因緣際會」(節目冊,頁30),劇本文字與意象的繁重負擔,使其很難在劇場演出中揮灑,即使敦請梁菲倚擔任共同導演的工作,但是她想要的魔幻、迷離與恍惚感是薄弱的,比較多的還是沉重、緩慢與拖沓,不過,或許這才更接近憂鬱的況味吧。
《家!甜蜜的家?》是這屆女節唯一的邀外演出,由海倫‧派瑞絲(Helen Paris)solo演出,主要針對英國家庭的餐桌與飲食禮儀做許多的批判與諷刺,漸漸擴而言及許多英國的政治與社會制度,特別是在一種男人的凝視與監督之下,將(女)人淹沒在焦慮與恐懼之中,最後演員形象化地將頭臉淹埋在透明壓克力板所做成的水池裡,看著她載浮載沉地一下嗆水,一下頭出水面搶呼吸,死亡的恐懼與存在的無路可出,令人感受頗為強烈。
繼續女節的理由是:「需要觀眾、劇評與研究者加入擴音迴響,對於作品的風格、語言、身體、美學,以及牽動的性別議題,給予一個被認真看待的位置……對所處創作環境和戲劇理論的反省,是對於自己或觀眾必然的表露。」(節目冊,頁2)看得出來,「定位」(positioning)是女節的核心價值,透過文字、語言、空間、身體和表演,突顯女性主義與性別表演等內容議題,以異於過去的不被認真看待。有趣的是,這次的六個作品,除了《拎著提箱的女人》影像中墮胎的女人形象無法被取代為男性之外,其餘劇場中的表演作品,其性別倘若改換成男性,包括旅行、拎提箱、不分、可以不存在、餐桌禮儀、內在敵人、天使朋友,類似的問題、疑惑、焦慮與恐懼似乎也依然存在,所探討、反省與表露的,毋寧是更貼近「人」的存在與精神狀態,以及意志與表象的劇場世界,也許真是應了「先做人,再決定做女人或男人」這句話的真諦吧!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