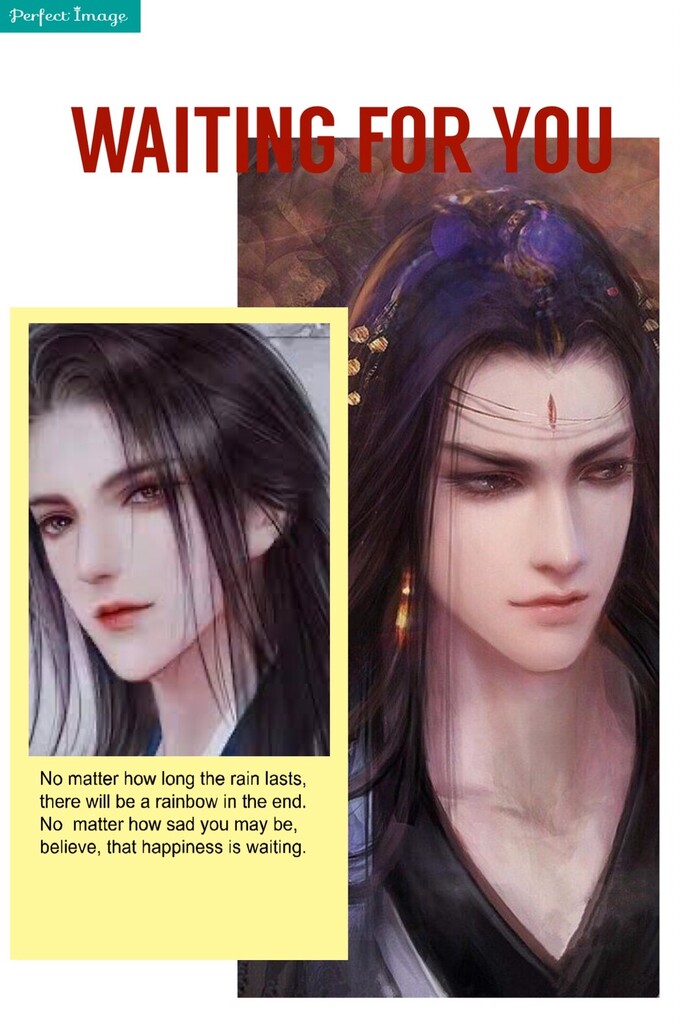
阿言穿著單薄的囚服,離開昧谷那天,癸深特地贏了個小擂台,送他到城門口去。
現在已經是北原的初秋,北原原本就寒冷,下了一場薄雪,癸深塞給押解阿言的侍衛一大包錢,希望他能沿路照拂阿言。看在錢的份上,那侍衛給了阿言和癸深話別的機會。
癸深將全身慘不忍睹,衣著被監獄裡的老鼠咬得破破爛爛的阿言,從頭到腳端詳了一遍,眉頭蹙得很緊。
「都已經秋天了,還要去寂海,他們怎麼讓你穿得這樣單薄?」
說完,癸深解下身上的氅子,要給阿言披上。
倒是阿言見癸深來送他,憔悴的臉上卻帶著一抹雲淡風輕的微笑,他推辭了癸深的氅子,撫了撫胸口的音羽靈珠。
「少爺您忘了,我有音羽靈珠,不懼冷熱。」
癸深這才恍然大悟。說得是,這是得自癸明身上的寶貝,只是癸深自己戴沒多久就送了阿言,情急之下竟然忘了它的作用。
「那好,阿言,到那裏如何,記得寫信回來。」
癸深道。
「我也會回信的。」
能有信件往來,這樣他們之間的情分,就不會因距離而斷絕。
多虧癸深教了他識字,多虧癸深給了他音羽靈珠,多虧癸深教了他武功,多虧癸深護著他,不拿他當靶子。
「少爺,謝謝你。」
謝謝你,關於這一切。阿言道。
「好好活著,我會想辦法把你弄回來。」
臨走,癸深抱了一下阿言。
北原人的體溫大抵比一般人低,但阿言卻覺得癸深的懷抱很溫暖。
這份溫暖,他一直記著。
通常押解人犯時,侍衛可以騎雪熊,人犯卻只能追在雪熊的屁股後面跑,雪熊體積很大,有許多罪犯還沒到達寂海,就已經在路上被雪熊踩死了。幸而癸深使過銀子,那侍衛倒也遵守信用,在雪熊後頭綁了一小輛破拖車,讓阿言坐在上面。雖然一路上還是顛頗,但已經比徒步跑在雪熊身後好太多了。
阿言想起癸深的偶像,曾到朏明苑訓話的前城主癸明。他不知道是如何來到寂海的,他肯定沒有一個癸深可以幫他使銀子。
那時的癸明,也還沒有音羽靈珠,凍也凍壞了他。
認識癸深,自己真的比其他人幸運多了。
走了十天,進入寂海地界,天地一片白霧茫茫,雪虐風饕,連眼睛都睜不開。那侍衛有備而來,足足披了兩條大氅還是瑟瑟發抖,連飛鳥都被強風颳得飛不動,墜地凍死。
侍衛問過幾次阿言冷不冷,阿言說了幾次不冷,那侍衛也就不再問了。只是這種氣候下,阿言只穿了一件破囚衣,還神清氣爽地,那侍衛一副不可思議的眼神,還沒見過這麼不怕冷的人。
進入寂海旁的城寨,一陣腥臭之味撲鼻而來,癸深告訴過阿言,寂海這裡的衛生條件不好,死在這裡的人也多,空氣中浮泛著這樣的味道也不需意外了。只是阿言不怕,他下意識撫了撫胸口的靈珠,他不怕冷,又會武功,就算是在人間地獄,又有甚麼好怕的?
那侍衛不是第一次押解囚犯來到寂海了,把阿言交給一個相熟的獄卒,那獄卒送給侍衛一大片油光水滑的鯨肉,那侍衛開心地捧著鯨肉走了。
寂海這裡有許多鯨魚,鯨肉多脂肥美,寂海的捕鯨囚犯卻不能吃,只供給北原三姓貴族和有錢人家。在北原亡國時,黑雁軍無處可逃,選擇以寂海為根據地,黑雁軍當時吃的就是鯨肉,當下戰力十足,所向披靡,最後匡復了北原。
那個送鯨肉的獄卒名叫癸崇,手下管了二十名囚犯,他把阿言押到囚犯居住的簡陋工寮裡,裏頭已經有了十九名囚犯。他說第二十個剛剛送出去,讓阿言去睡他的位置。
要是一般人睡個死人的位置肯定心有芥蒂,但阿言可是流浪過的人,甚麼苦沒嘗過?他靜靜地走向第二十個床位,說是床位,也不過是一領褐色的破席,那褐色還褐得不是很均勻,阿言覺得那也許是歷任主人乾掉的血跡。
但他是囚犯,也沒太多選擇,除了死,甚麼都不要緊,這是身為一個囚犯必須具備的認知。
這認知才能幫助他熬下去。
寂海這裡做的都是體力活,又沒什麼娛樂,唯一能做的就是早點睡,儲備體力,才能應付明天的苦役。
大伙都準備睡覺了,沒人來管阿言。
阿言的床位旁邊,是個大他幾歲,年紀大概和癸深差不多的年輕人,身上衣著破爛,看著稍微溫暖的,就是一領獸皮背心,手上臉上有好幾處凍傷的痕跡。
那人面無表情。阿言對他笑了笑,意在示好,那年輕人分明看見了卻不理睬,倒頭就睡。
阿言也不想再自討沒趣。他的床位雖然是死人睡過的,但對角就是一扇高高的窗戶。月光會從窗戶照進來。
這是他來到寂海的第一個夜晚。不知道少爺怎麼了,他也和我看著同一輪月亮嗎?
他一個人睡,會想我嗎?
得想辦法快些弄來紙筆才行。
阿言握住胸前的音羽靈珠,胡思亂想著,不知不覺睡著了。
隔天天未大亮,癸崇就把所有的囚犯叫了起來。他的助手每個人發了一個黑黑的餅,癸崇道。
「吃完了就出來集合,幹活了。」
阿言不知道那個黑黑的餅是什麼,看起來似乎有毒,正想問,但看見其他人冷淡的表情,當下把想說的話噎了回去。
他們倒是吃得很快,彷彿那餅是什麼人間美味。
可能嗎?
阿言小小地咬了一口,有草味......霉味......嗯,還有......泥土味.....
他差點吐出來!後來他才知道,這叫地衣餅,寂海的囚犯只有這東西可吃。
阿言吃不下,把餅丟了,馬上有他其他的伙伴過來撿走吃了。
這個動作讓阿言很後悔。他後來發現,寂海囚犯的伙食,一天只給兩個餅,上午一個,下午一個,晚上沒有,餓了就早點睡。
他丟了上午那一個,一直餓到下午才有第二個餅吃。加上高強度的工作,讓阿言頭昏腦脹。
癸崇帶了所有囚犯來到寂海畔。雖是北原的初秋,但寂海已經結冰了。他們的工作就是,一個人發一只鑿子,把冰鑿開,再潛到水下誘捕鯨魚。
在海上鑿冰的動作極其危險,除了溫度低,容易失溫,另外,冰層厚薄不一,在鑿冰的過程中有時會遇到意外的破冰,或者腳滑,人會掉到冰冷的海水裡,四肢麻痺爬不上岸,最後失溫淹死在海裡。
寂海這裡並不把人命當成命,反正有人死了,馬上會有人遞補上,所以一旦發生危險,是不會有人來救的。
阿言拿著鑿子,學著其他同伙,四散鑿冰去了。在所有人當中,大家都凍得直哆嗦,就那個新來的穿得最少,卻一點也不冷的樣子,不禁引起大伙的側目。
鑿完冰後,必須有人下海水去,拿著一袋子烤過的,散發著蝦皮香味的袋子,將鯨魚引到水下的一個海蝕洞裡,讓鯨魚的身軀卡在洞裡動彈不得,其他人再潛下去殺了鯨魚,分肉帶出水面。
這項工作是最危險的,可能會凍死、淹死、或被鯨魚不小心吞了。
沒人要去,為求公平,多半拈鬮。
這次抽到的,是睡在阿言身旁的那名室友,聽癸崇叫他癸潤。
也是個犯了罪的貴族。
大伙把同情眼光投向癸潤,癸潤顫抖著手接過蝦皮袋子,怔忡許久。這才又移動步伐,走向海中央,他們方才鑿出的大洞之一,緩緩沉了下去。
囚犯們在海上鑿出好幾個洞,就是為了讓引鯨的人可以探出頭來換氣,延長在水下的時間。
阿言注意著那些洞穴,但見癸潤游上來喚了幾次氣後,接著有好長一段時間沒看到他。
那是一段遠超過人體閉氣極限的時間。
癸崇見狀,判斷癸潤大概不好了,就要再抽人下去捕鯨。阿言嚇了一跳,問。
「不去把癸潤找回來嗎?」
眾人投以看見神經病的眼神。
他以為癸潤好歹是癸氏貴族,不像他阿言命如草芥,待遇應該會好一些。
而且,那癸潤看上去,和癸深年紀差不多,這麼青蔥的年歲,就要死去了嗎?
沒有人幫他說話,也沒有人應和他。
如果有一天,癸深遇到了危險,即使自己不在他身邊,阿言也希望有人能救他的。
阿言深吸了一口氣,又道。
「你們不去找,我去。」
說完,阿言朝海面其中一個冰洞跑去,一躍而下!
尊重每一條生命,這也是癸深教他的。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