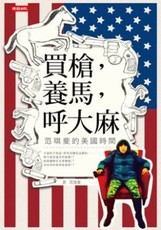
買槍,養馬,呼大麻:范琪斐的美國時間
作者:范琪斐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6-03-09 00:00:00
不說你不知道,原來美國是這樣的……
吸大麻是進步的象徵!?
射殺獵物是光榮傳統!?
沒有用的東西很重要!?
【著名資深駐美特派記者范琪斐,在美國的零時差貼身採訪第一手報導】最近十年大麻開始翻身時,這些酷奶酷爺們想起年輕時的美好時光,大多對大麻合法化非常支持,也成為休閒大麻的主力消費群。這意外促成美國隔世代的交流,加強了爺爺奶奶與孫子輩的感情,現在孫子們去探望袓父母的誘因大很多,因為Nana(袓母的暱稱)有大麻。
一個生活在紐約二十多年的臺灣媒體人,長期觀察臺美兩地文化差異,要用最輕鬆詼諧的筆,引領你認識真正的美國人跟美國文化,保證前所未聞,拍案叫絕。
以前你只知道,她有一張能說會道的嘴;以後你會知道,她有一枝最會說故事的筆,能把她看過所有好玩、新奇的事物一一呈現在你眼前。
★內文試閱:
這是亨利還是貝琪?
跟老美打屁,我最喜歡的話題之一就是食物。因為老美實在太多東西不吃,很容易糊弄。
動作明星威爾‧史密斯是好萊塢有名的好動兒,有一次訪問空檔,我們不知如何聊到蛇,我隨口說了一句:「我吃過蛇。」威爾‧史密斯馬上眼睛瞪得老大,問我怎麼吃。我說:「煮成湯。你下次來臺灣我帶你去吃。」他馬上搖頭說:「No, no, a bro got to have it barbequed. 不行,不行,兄弟我(美國非洲裔喜歡自稱Bro)一定要用烤的。」接下來就開始比手畫腳,假定他有條蛇時要怎麼烤,他是著名諧星,逗得整屋子笑翻了。威爾‧史密斯說得活龍活現,但我跟你打包票,他絕對不敢吃。
Roberto最喜歡跟朋友吹噓,他的臺灣老婆,也就是我,在厄瓜多曾經吃了一整個羊頭湯當早餐,還跟對方形容,如何羊眼睛、羊舌頭、羊耳朵都漂浮在湯中,可清楚辨視,我通常會加一句:「氣管最好吃,軟中帶一點脆的口感。」Roberto看到他的美國同胞聽得目瞪口呆,他就很得意。他都忘了,我在吃的時候,他不但一口都沒法吃,連在旁邊看都受不了,要坐到隔壁桌,說味道太重。
諸如此類,我吃得津津有味,Roberto卻看到快吐的經驗,我們真的太多了。
比如他第一次到臺灣,我媽為了招待未來女婿,聽說他喜歡吃生魚片,特地帶他去基隆吃海鮮。頭盤便上了龍蝦生魚片,為證明新鮮,店家連龍蝦頭跟片下來的龍蝦肉一起上,龍蝦鬚當時還在盤中徐徐移動。在臺灣,這算什麼陣仗?我有次吃活魚,餐館裝魚的水族箱在一樓,廚房在地下室,老闆把活跳跳的鯉魚從魚缸撈出來後,也不殺,就一路把鯉魚從一樓踢到地下室,還跟我說,魚踢到半路便昏死了,沒有虐待動物的問題,我因為太驚詫,只會點頭。所以當我看到會動的龍蝦鬚時,老實說,可能根本沒注意,是一直到Roberto指著龍蝦語無倫次時,我才看到。Roberto則是當場吃不下,連接下來的炸蚵捲、紅蟳米糕全沒法吃,最後吃了個炒飯。
又有一次,Roberto跟我說,他從沒看過他的食物還活著時的樣子。他當然知道牛有長角,豬有四條腿,只不過沒見過他真正吃下肚的那一隻牛或豬生前的長相。我們當時住在紐約,我跟他說此事好解決,在我們臺僑聚集的法拉盛就有賣活殺雞的店。
找了個週末我便帶他到活殺雞店買雞。一進店裡,幾百隻雞分散在約莫幾十個籠子裡,雞聲震耳,紅白綠黑,任君挑選。我們對雞的知識很少,隨便挑了兩隻看來精神抖擻的白毛雞,一公一母,指給工作人員看,工作人員便走到雞籠的另一面準備抓雞。就在那等待的兩三分鐘裡。Roberto逗著雞玩,跟我說他已經給他們取了名字了,公的叫亨利,母的叫貝琪。當時我腦裡正忙著盤算,待會兒是要烤雞還是三杯雞,聽他給雞命名,也不怎麼在意,只覺得他很無聊。
沒多久,工作人員抓了雞,到後面我們看不到的區域去處理,二十分鐘後,兩隻光溜溜的全雞就已經裝在精美的包裝袋裡交給我們。
回到家,我特地用美式做法,烤了個全雞,上了餐桌,我正在讚嘆,今日這雞肥美多汁,我又烤得皮一點都沒破,油亮光滑,真是好雞一隻。切了雞胸給Roberto,等著他讚美,沒想到他語帶顫抖地說:「這是亨利還是貝琪?」他當晚真的又沒吃雞,只吃了雞旁邊的馬鈴薯泥。
有一陣子,我以為是Roberto很難搞。但久了以後發現,我老公已經算不錯的了。比如全魚他是沒問題的,但很多老美是看到魚眼睛,這道菜就再見再聯絡。Roberto一位女醫生同事,一年要去七、八個國家旅行,但說她第一次到菲律賓時,餓了兩天,因為餐餐都有全魚,但她只要一看到魚眼睛就吃不下,一直到第三天實在餓到受不了才開始吃。我想起多年前,有次與一位美國年輕女生聊起她的臺灣行,她說她最驚悚的一次經驗,就是被帶去吃麻辣鍋,鍋中放了鴨血。她問朋友那是什麼?朋友跟她說是豆腐,她吃了兩口總覺得不對頭,又問了一次,這次朋友誠實相告,此乃鴨血,女朋友說她當場在餐桌上便哭了出來,我聽了這故事,當然是當場就笑了出來。
有朋友問我,跟老美講這些,難道不擔心這些老美朋友會覺得我很野蠻很落後。
一點也不。因為我是真心誠意認為,什麼都吃的我,才是進步。
二○○四年英國主廚Fergus Henderson寫了一本書《全獸吃法:從鼻子吃到尾巴》(The Whole Beast:Nose to Tail Eating),書中描述一隻豬的各個部位可以怎麼烹調。此書因被美國著名美食節目主持人Anthony Bourdain大力推薦,在美國聲名大噪。一時之間,從鼻子吃到尾巴成為流行名詞,在美國飲食界蔚為風氣,很多餐廳都特別開發相關的菜單,吸引美國饕客上門。因為實在太過流行,所以我還特地去找了這類餐廳做報導。可是我在報導時實在不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幾條香腸也拿出來說嘴。我們中國人早就一條豬充分利用。我回臺灣下飛機第一餐,通常就是巷子口的米粉湯,再點上大腸、豬肝連、豬心、豬肺……在十多個小時的飛機餐後,你知道豬頭皮有多好吃嗎?
我當然看過老美給我的斜眼。在厄瓜多時,我纏著導遊帶我去買基多最好吃的烤天竺鼠,我在地攤買到之後,全團只有我老公為表示對我的支持吃了一隻鼠腿,其他團員便圍觀看我吃,我當時感覺自已有點像熊貓表演。大概表演得不錯,有幾位團員便自己也去買了來吃。有一位六十多歲的退休女法官剛開始就是一副很嫌惡的表情。她在早些的旅程裡已跟我表達過,她認為吃魚翅是很野蠻很不環保的行為。她不了解我們這些人為什麼不能吃得「正常」一點,一定要吃得那麼珍禽異獸?
我跟她曉以大義,要知道印第安人已吃天竺鼠吃了幾千年,跟我們吃牛吃豬的歷史一樣長,對他們來講,吃天竺鼠很「正常」。而且天竺鼠又不是瀕臨絕種動物,為何吃不得?老美一條牛只吃牛排,其他部位全部丟掉,才不環保,要知道畜牧業是地球暖化最重要的元凶之一,如果要吃牛,就要珍珍重重地把每一部位都吃掉。至於魚翅,我完全同意她該禁掉,能吃的東西那麼多,幹嘛一定要吃快絕種的動物?像我這種什麼都吃,連蟲都可以吃的,才叫真正環保。女法官被我說得一愣一愣,後來真的被我說服,就我的手咬了一口天竺鼠。
我跟女法官後來成為好朋友,但她跟我強調,天竺鼠就那一回,絕不可能重演了。我心裡想,除非我再去南美洲,不然還真難重演,當時應該多吃個兩隻的。
說不得的美國禁忌
我個人認為駐紐約特派員最好的福利之一,就是有很多採訪李安導演的機會,一項我很自豪的紀錄,就是我訪問李安導演的次數可能是華人記者之冠,我從「囍宴」就開始訪問他,而且有好幾次超過一小時的訪問。這倒不是我很會問,而是導演很會講,尤其講到他的電影時,常常一發不可收拾,有時為了趕時效,我還得跟李安的助理李良山使眼色呢。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二○○七年為了「色‧戒」在威尼斯訪問他,我們談到了在中國大陸拍片的經驗,李安嘆了口氣說,他在美國,人家說他是臺灣來的,是「outsider(外人)」,他到臺灣,有人會說,你在美國住久了,你是outsider,在中國大陸,自然有更多人說他是outsider;我當時已在美國住了十七年,深深理解他這話的涵意,因為是outsider,很多事只能看在眼裡,是說不得的。但李安這話還是有玄機,因為李安最被人稱道的,就是他可以把一個跟他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故事,拍得讓「insider(內行人)」都不得不佩服得五體投地,「感性與理性」讓英國人嘖嘖稱奇,「冰風暴」、「斷背山」對美國文化的剖析也是經典,在「斷背山」的威尼斯記者會上,一個美國記者提到,李安對美國牛仔文化掌握之精確,讓這個從小在美國牧場裡,跟牛仔一起長大的她佩服極了,她說電影裡連牛仔們吃的豆子罐頭的品牌都是那個年代的牛仔們最常吃的。李安將他的outsider身分發揮得淋漓盡致,正因為是outsider,有了距離,更為用心,很多事觀察得更精確。
在美國住這麼久,我也有我的outsider哲學,而且我覺得我的outsider身分,非常利多於弊。
美國社會表面上看來非常開放,言論超級自由,但你若以為這表示你在美國啥都能講,啥都能做,你就大錯特錯,美國社會禁忌之多,動不動就踩到地雷。
有一個叫Travel Taboo(旅遊禁忌)的網站搜集了一些在美國不該做的事,比如:
不可以問收入、財產等個人資訊
不可以在人前脫鞋子,所以到美國人家拜訪除非主人要求,不然絕對不可脫鞋
不可以在人前吐舌頭
不可以不問對方是否同意之前就抽菸
不可以在人前用牙籤
不可以在公共場合補妝(化妝)
不可以不跟小朋友打招呼
不可以在女主人未宣布開動之前就開始吃東西
不可以在吃東西時發出咀嚼的聲音,嘴巴裡有東西不可以說話
不可以在晚上坐地鐵,地鐵上會有吸毒的、賣毒的跟幫派分子
其他還有很多條我懶得翻譯,就不列出來了,但以上這些「不可以」,除了地鐵那條絕對是胡說八道之外,其他大致符合美國人一般的習慣。
大家此時一定在想,這麼多哪記得了?我在美國住了二十多年,嫁了個美國老公,自已都成為美國人,我都還常出錯。
有一次一起旅行的朋友說她不舒服,下午的行程就不參加了,我想我們帶了一大堆藥出門,Roberto又是醫生,就很好心地問:「妳那裡不舒服啊?」Roberto馬上出面糾正:「不能問人家生什麼病的啦!除非她自已說。」我跟女朋友道歉,對方馬上說:「沒關係,沒關係。」
各位,這就是outsider的好處,美國人將大大小小疾病,大至癌症小至長針眼都視為隱私,他自己說得,但是問不得,但我因是外國來的,是outsider,有言論免責權。人家常常會說:「她不知道嘛,沒關係。」
給我發現我有這個outsider免責權之後,這還得了,我便常常運用在採訪上。有些問題明明很敏感,老美一般是問不出口的,但我因有某些程度的免責權,便問得大搖大擺。
比如在美國,宗教信仰、政黨屬性、擁槍反槍、墮胎議題都是禁忌,美國自由派與保守派壁壘分明,撕裂的程度,我覺得比臺灣藍綠之爭還要嚴重。所以除非很熟的朋友,已知對方的底細,在一般聚會時是不會談起這些敏感議題的,以免不小心破壞了聚會的氣氛。但因我是outsider,問對方信什麼教,有沒有槍,都很自然,對方也答得自然。所以我跟Roberto出門應酬,大多由我負責聊天,帶回的八卦可比Roberto聽來的精彩多了。
但美國禁忌實在太多,像是你跟非洲裔講葡萄口味的汽水是歧視,你跟墨西哥裔講豆子是歧視,你跟伊斯蘭教徒講頭巾是歧視。我跟Roberto一個亞裔、一個墨裔,都是少數族裔,我常常看到不同族裔的尤其是白人朋友,非常努力地假裝沒有注意到我們的少數族裔背景。但一位白人朋友因把Roberto不小心叫成Robert,少了一個o,我老公便老大不高興,拉下臉來糾正對方,說他的名字是西班牙文發音,不是英文,對方嚇得屁滾尿流,馬上道歉,怕被冠上種族歧視的罪名。
這些是種族的,政治上的禁忌也很多,有一次我跟一個臺灣來的體育記者一起在阿拉巴馬州跑林書豪的新聞,他跑到一半被球隊公關叫去談話,他回來很洩氣地跟我說,他穿的T恤出了問題,原來他在臺灣隨便買的T恤,上面的人像是希特勒,體育記者自已根本沒注意,我一聽便知道要不好了,希特勒被白人至上的偏激派視為袓師爺,阿拉巴馬當時剛發生白人至上偏激派主導的殺警事件,正敏感當中,而且在美國,希特勒幾乎是邪惡殺人魔的同義辭,罵人希特勒是非常嚴重的。體育記者不知情把希特勒人頭穿在身上在球場上穿梭,若是被攝影機不小心拍到,球隊有可能會被觀眾抗議的。球隊公關於是要求體育記者全程要穿上外套。體育記者顯然不知事情的敏感度,幾分鐘後,他為了搶拍照片忘了穿外套,馬上又被球隊公關請去,這一次則直接禁止他回到球場。這個故事告訴我們,outsider的言論免責權有其界限,不要以為是免罪金牌,可在斷頭臺上救人的。
二○一四年,一群明尼蘇達St. Thomas大學的學生想弄一頭駱駝來校園做活動解壓,結果被抗議,有人說駱駝是白人用來罵阿拉伯人的,有人說這是虐待動物。主辦單位覺得很無辜,不知為何幾個月前他們請麋鹿來學校就沒問題,駱駝就不行。總而言之,駱駝敵不過抗議聲浪,最後真的沒來成。駱駝事件發生之後,在美國引發許多討論,美國的禁忌是不是太多了一點?先不要說自我審查對言論自由造成的危害,種種禁忌造成不同族群的人很少能放下心防溝通,對彼此的了解便越來越少,雙方的鴻溝越來越深,在要求達成共識的民主制度裡,便很容易造成施政牛步化。我常常看到我的美國朋友,保守派只交保守派的朋友,自由派只交自由派的朋友,各自的陣營裡,有自己的新聞頻道(保守派看福斯,自由派看福斯以外的任何新聞臺)、自己的電視節目(保守派愛看強調傳統家庭價值觀的像7th Heaven,自由派則喜歡看家庭成員中有同志成婚的像Modern family)、自己的休閒活動(保守派喜歡打獵,自由派喜歡出國旅行)、自己的超市(保守派去Walmart,自由派去Costco)、自己的餐廳、自己的品牌……我自由派的朋友對我到Walmart買菜此事非常不諒解,認為我在支持靠血汗工廠賺錢的企業,我保守派的朋友則對我不信基督這事很感冒,擔心我將來要下地獄。但他們都當我是朋友,因為我是outsider,我只能聽,不能評論,評論了也沒重量。但我常常在想,你們是同一國的人,當你對同一國,有時是同一州、同一城市甚至同一條街上不同族群的人完全不了解的時候,你如何跟這些人在異中求同呢?
那跟不熟的美國人談什麼最安全呢?多年跟美國人交談的結果,基本上運動跟天氣最安全。雖然洋基迷跟大都會迷是死對頭,談天氣也只能止於今天氣溫真高,不能擴張到談地球暖化,因為很多保守派人士到現在還認為地球暖化是自由派科學家自己想像出來的。
沒有用的東西
在大陸科技圈很流行的科技博客IT公論的主持人李如一,有次在節目裡提到,他在美國舊金山一家餐廳裡,看到工作人員清潔桌子使用的一個L型小工具,只能拿來做一件事,就是把桌上的食物碎削刮掉。他覺得很新奇,這麼簡單的事也要發明一個特定的工具來做。李如一討論的重點,是一個東西有越多功能越好,還是功能越少越專精越好?我的重點是,這是個文化差異的觀察,大部分老美大概不會有這個疑問,在美國這種看似沒什麼大用途也就是useless的東西可多了,而且我認為,就是從這些看似無用的東西裡,你可以看到美國最精彩的創意。
美國新媒體Buzzfeed,現在已儼然成為美國第一大媒體,最擅長做「無用」的新聞,而且還以此自豪。他們的新聞不是以政治、經濟、消費這些傳統的新聞類別來區分,而是以LOL(笑死我)、OMG(我的天啊)、WTF(他媽的)、cute(卡哇伊)來區分,常見的新聞是跟讀者推薦像「可以浪費時間的有趣網站」。
第一名就是一條黑蟲會隨著你的游標抖來抖去,然後呢?沒了,就這樣。第二名是看一隻巴哥犬在舔電腦螢幕。那隻黑蟲我真的津津有味地玩了兩三分鐘,巴哥犬我也看牠舔了一整個螢幕才捨得走,你覺得我很無聊,我將網頁附在這裡你去試試看,再回來說我很無聊。(http://www.buzzfeed.com/mlew15/19-websites-to-waste-time-on-right-now-h0se#.uhnlDVvz2X)
嫌Buzzfeed太八卦,但嚴肅的美國媒體也常在做這種看似無用的事。比如美國國家廣播電臺(NPR)很紅的一個節目:這個美國生活(This American Life),有一次就把一個作家無意之間把自己鎖在旅館衣櫥裡二十二分鐘的經歷做成一個特輯,找來簡約主義風格的音樂大師菲利普‧格拉斯(Pillip Glass)做曲,寫成一部歌劇,還在紐約的布魯克林音樂學院(BAM)隆重上演,開幕曲便是女主角喊救命唱了七分半。為了幫助臺灣朋友了解本劇的重要性,就想像是我被關在衣櫥裡,然後找來大導演蔡明亮把它拍成電影,然後我們還在小巨蛋做首映,看楊貴媚演我在電影的開頭喊救命喊個七分鐘,咦,怎麼好像覺得楊貴媚已做過類似的事。總而言之,我聽廣播時聽到救命這一段時,我也想喊救命,但這是因為我本來就不喜歡歌劇,可是我的歌劇迷朋友們,尤其是喜歡當代歌劇的,都對NPR這個特輯驚為天人。
但我覺得在美國將這種「無用」精神,發揮到最極致的就是燃燒人(Burning Man)活動。
這個活動的起頭,是有一群住在舊金山灣區的藝術家聚在一起閒嗑牙,一群人對藝術是不是一定要有用爭論起來。主張無用說的一群人,為了證明藝術作品是可以完全無用的,就用木頭夾板做了個二百七十公分高的假人,在八月最後一個週末,把木頭人帶到海邊燒了。當時吸引了幾百人到海灘觀賞,這是在一九八六年。因為很受歡迎,他們決定每年都燒一個。這個活動越辦越大,假人也越來越高大,在二○一四年時,參加的人多達六萬多人,木頭人高達三十二公尺,約十層樓高。二○一三年我去參加時,整個假人建築大得像我們的小巨蛋。設計時間不算,光蓋起來就要幾百人日夜趕工兩星期,展出一個星期之後,就放一把火燒了。
二○一三年Roberto吵著要去的時候,我覺得他真是沒事找事,這不是到墾丁參加春天吶喊,穿上游泳衣就可以去了。這個活動全程在高達攝氏三十五度的沙漠裡舉行,沒水沒電,參加的人要全部自給自足,帳篷、飲水、食物全都要自己帶去,而且因為要環保,所有垃圾也要帶出來,連洗碗水都要搜集起來帶走,我想到要去沙漠裡髒兮兮過一個星期就頭皮發麻。而且你不要以為這個活動不怎麼花錢,光門票一人就要三百八十美金,也就是一萬多臺幣。我跟Roberto總結下來,連飛機票、買補給物資等等花了六千美金,也就是十八萬臺幣。等燒完了假人,兩人在附近的城市Tahoe的旅館裡,又足足躺了兩天,才有力氣回家。
但你知道嗎?這是我參加過或報導過最好玩的活動,好玩到隔年我們又去了一次。
為什麼燒一個假人會好玩?因為燒假人之前,要做假人,做假人之前,要設計假人,設計假人之前要募款,募款之前,要下一個很大的決心:「我要做假人。」假人越大,這個決心就要越堅定,堅定到可以去問你的好朋友阿明要不要跟你一樣去做一件「無用」的事,阿明也要有同樣的決心願意花很多時間精力去做一件「無用」的事,決心強到阿明去找小美一起來做假人。當一群人決心一起去做一件事,不管有用無用,這件事就不再無聊了。
因為無聊的人實在太多,光做一個假人無法消化,所以在假人旁邊就生出各式各樣工程,有的蓋廟,有的蓋綠建築,有的做奇形怪狀的公車,也有人蓋風格特異的酒吧,在二○一三年有一個臺僑團隊就蓋了一個看似佛像的假人,還有義工在佛像腳奉茶,最後當然也是一把火燒掉。在一個燃燒人活動裡,會有幾千個這樣洐生出來的小活動,全都是參加的這些無聊民眾,自動自發自已組織出來的。因為不需要「有用」,所以常出現不可思議的創意。比如就有團隊蓋了一個電話亭,讓你跟「神」通電話,我也去試了一下:
我:Hello……
神:Hi, I am god. What’s up? 我是神,怎樣啊?(這個神聽起來好像很年輕,可能只有二十多歲。)
我:我可以知道你是那個神嗎?
神:Dud,妳要我是那個,我就可以是那個。
我:那我可以知道你擅長什麼嗎?
神:我什麼都擅長。(神此時有點不耐煩)妳好像沒有什麼跟神講話的經驗,這樣好了,妳有什麼疑難需要解答嗎?
我的確沒有跟神講話的經驗,但問問題我很會,我於是問神不當神的時候在做什麼?神告訴我他在奧瑞岡州的運動用品店工作,這次跟一票朋友參加燃燒人,朋友要他來幫忙當神他就來了,每天要來當班四小時,有點像生命線的義工,反正就是跟人聊天,他說大部分人都是在跟他分享燃燒人的經驗,他很有收穫,偶爾真的也有人哭哭啼啼,他就會指示他們,在五點鐘方向有人在免費送酒喝。神還指示我,在當晚凌晨兩點,J區八點鐘方位的舞廳會有很棒的DJ。
當然美國文化裡也有很多真的讓我想不出有任何用處的垃圾,比如胸大無腦的Kardarshians,比如把猛男如何吊馬子的過程拍成實境劇的Jersey Shore,但便是這種對「無用」之物的寬容態度,讓很多無用之物有機會發展成有用之物,甚至偉大的事物。也就是因為美國人這種能力,讓我對這個國家從不敢輕看。這不是因為美國有言論自由而已,有言論自由的地方很多,像臺灣,但我們的無用之物好像就永遠停留在無用的階段,更糟的是,連有用的都朝無用的方向發展。
我有次一個人在洛杉磯旅行的時候,想給Roberto買個禮物,但不知要買什麼,經過一家日商的百元商店,突然有個主意,我要買一個完全「無用」的東西給他。在店裡,仔仔細細地找了一個多小時。發現「無用」的東西真的很難找,多少總有點小用處,只好把目標由「完全無用」,修正成「沒什麼鳥用」,這才終於找到一隻假鳥,可能是插在盆栽裡當裝飾用的吧,很難判斷。我回家之後,拿出禮物前,我擔心Roberto會覺得我在敷衍他,就跟他解釋了前因後果,沒想到Roberto一看之後就歡天喜地,說是我送給他最好的禮物,隔天就看到假鳥被做成一個裝飾品,掛在廚房牆上。
美國人,真奇怪。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