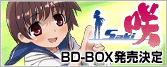這篇是暗殺的番外之一,如果沒看過暗殺系列應該看不懂,因為嚴格說起來這篇應該算是暗殺的…同人吧?因為這篇加治木篇的後續是我硬跟史丹拿來寫的w本來是想跟暗殺系列一起放在熊熊國的,可是某人的庫存已經多到滿出來,檔期排不進去…所以我還是拿來放自己家了。
Yumi Kajiki
夜已經深了。12月的東京似乎連街上的廢氣都被凍結,被吸入肺部的物體冰冷而刺痛,沉澱澱地剜入骨肉裡,最後與血液交融,無法分離。
回到自己公寓樓下,祐巳會還是下意識地抬頭看看自己家所在的樓層,一片漆黑。祐巳想笑自己,臉部的表情卻無法活動自如,應該是太冷的關係吧。
她機械性地拿出鑰匙轉開門。
即使到了現在,她還是會去想像她一開門,久就已經穿著她的襯衫在廚房裡準備晚餐等她回家的模樣。她總是會放下廚房的工作先來玄關迎接她,祐巳都還來不及脫下大衣就被圈住後頸細細親吻,久會在她們的唇間輕聲說著回來啦?今天累不累?祐巳也會以吻來回應她,當然有時候不只這些。
如今,打開門迎接她的,就只有一室的黑暗與濃重的煙味而已。
房裡的空氣因無法流通而窒悶,與殘留的煙草味融合成一股令人作嘔的氣味。祐巳沒有力氣去打開窗或走到自己房間裡,黑暗中客廳桌上散亂著的煙盒與空咖啡罐,她坐在沙發上,深深地將自己的臉埋入雙手裡。
這幾天的片段在她腦海裡不斷交錯,滿是議員的警視廳,屍體,染滿血跡的辦公室,那位社長秘書與美穗子無法理解的笑容,五千萬支票,以及那天晚上,久在受到她那麼冷酷無情的對待之後,最後還是伸手擁著她,軟軟地呢喃著她的名字。
當久摘下戒指丟向她的時候,祐巳彷彿覺得有什麼東西被打破了,匡匡噹噹碎了一地。她沒有後悔過自己做了那件事,但當下望見久的表情時,她有那麼一瞬間是後悔的。她從沒看過久這樣的表情。即使之前她們發生過再大的爭執,久也從來不會把話說死,這樣的一個女人,連在氣憤中也還是處處謹慎。也許是不管發生什麼事,久最後總是會對祐巳笑,才讓她一直都對久予取予求。包括久的信任與愛情。
那天倚在書房門口的久,淡漠地看不出一點情緒,令人哀傷得無以名狀。
之後她再見到久,已經是在偵訊室裡的事了。
她原本可以避開跟久在這種情況下再次會面,但她認為即使久不願,她在這種狀況下逃避只是更加侮辱久而已,於是她還是親自審問她。
預料中地久連看都不看她一眼,嘴邊的笑與她吐出來的話語一樣冰冷。
『妳不是早已預想好答案了嗎?那又何必再問呢。』
那天久的話語,只此一句,之後不論如何,她都沒有再開過一次口。祐巳只覺得右肩上的咬痕隱隱作痛。她對久已有太多愧疚,再怎麼氣惱也無法在久面前發作,最後她還是只能握緊拳頭轉身離開,不忍看見久被員警帶走的模樣。
但其實狼狽的,最終還是自己。
她沒有那麼笨,美穗子的口供並非完美無缺,但這又如何呢?什麼該相信,什麼該懷疑,她已無法辨明。美穗子的諷刺和那位社長秘書的意有所指並沒有對祐巳造成多大的影響,別人對她的看法如何她一點都不在意,她只知道她唯一對不起的,就只有久而已。
所以在案子於無形的壓力下匆匆結案後,警方被迫召開記者會向幾個案件關係人道歉並表達謝意這件事,讓祐巳怎麼都無法接受。但她終究無力改變任何事實。在無數的閃光燈與鏡頭下,祐巳還是笑了。她笑自己捨棄了一切最後換來的竟是這種結果,她突然想到那位年輕社長說的話一點都沒錯。
一切都是徒勞。
久看到她這麼難看的樣子,會怎麼想呢?她不敢想像。
祐巳終於遞了辭呈,她脫下槍套,與她的配槍一併放在智美的桌上。
智美沒有看向她,只是一如往常地笑著,輕聲開口,「這就是妳的選擇嗎?」
「……一直以來我都認為,為了追尋自己的正義與理念,可以放棄一切。包括我最重要的人。」
「所以妳後悔了?」
「我只是無法原諒這樣的自己。」
智美沒有再多說什麼,只是在門關上的那一瞬間,她抬起頭來,望了望她那消失在門後的正直友人的背影。
電車搖搖晃晃地行駛著,祐巳望著窗外不斷向後遠去的景色,東京在霓紅燈的照耀下顯得璀璨無比。她本來打算輕便地上路,但光冬天的衣物就塞滿了她那小小的背包,讓她有點後悔選擇在這種時節去北海道。果然,還是該去沖繩的吧……
不過久喜歡雪。祐巳望著遠處的燦爛燈火,有些恍惚地想。
每年的初雪,老愛賴床的久都會很興奮地從床上拉起祐巳,隨手捉了件大外套就跑到屋外迎接冬天的第一場雪。她總是像個孩子般仰望著天空不斷飄下的白色雪花,直到它們融化在自己的掌心。
祐巳會脫下手套包覆住她冷冰冰的手,然後聽見久輕聲地對她說,祐巳,哪天一起去北海道吧。或是去歐洲,有很多很多雪的地方,好嗎?明明是個怕冷的人,祐巳笑著心想,然後以親吻她的手來回應她,兩人拉拉扯扯又進到溫暖的房裡。
哪天一起去吧。哪裡都好,只要兩個人在一起就好了。但唸書時沒錢,工作後又沒空,她跟久交往這麼久,竟沒一起出過遠門。
冬天,雪,北海道都是所謂純淨的象徵。北海道之所以會這麼美麗,其實只是因為東京太骯髒了吧。而東京之所以這麼污穢不堪,那也只是因為人類是種入境隨俗的動物罷了。入境隨俗,是啊。她什麼時候開始學會抽煙的呢?她竟已記不得了。
祐巳開始有些睡意,她將行李放到腳下,模模糊糊地想著她第一次遇到久的情景,不自覺地笑了。以及後來的告白與交往,她們第一次吵架似乎也是在這麼寒冷的天氣裡,久第一次在她面前哭泣,然後她們第一次在床上合好。一幕幕清晰得彷彿今早才剛發生。想著久沾著薄汗的額與胸口,她微微皺起的眉與染紅的雙頰,讓祐巳突然有些呼吸困難。
哭泣的久。祐巳想著。久是個堅強的女人,但她總是讓她哭。一直以來祐巳都覺得自己才是理性的一方,卻忘了兩人之間是需要彼此包容的。她從來都覺得自己才是對的,不是嗎?之前每一次的吵架,幾乎沒有一次不是久放低姿態,她竟一直都覺得理所當然。祐巳總是認為,就是因為這就是她,加治木祐巳,久才會這樣地愛著她。
但其實從很久以前開始,久就已經習慣去配合自己了吧。久的愛這麼誠摯而真切,然而到底是怎樣的自大讓祐巳到現在才發現,自己所相信的一切其實都是虛假而無從辨別的呢?
在這時節,往都市走的話祐巳正好可以遇到盛大的札幌雪祭,但她並沒有在城裡多加停留,在一個偏僻的小車站下了車。走出車站,比起白色的冰雪世界祐巳更覺得她自己包得像是北海道深山裡會出現的熊似的,久這麼怕冷,不就要穿得更多了嗎?
不過要是久的話,一定會忘了穿外套就興沖沖地往眼前這片一望無際的雪地跑去了吧。高大的衫樹沾滿了雪,看起來像是蛋糕上灑著糖粉的聖誕樹,祐巳心想,又對自己的本末倒置感到失笑。
祐巳拎起背包,拍了拍上面的雪,沿著道路漫無目的地走著。
最後她在離車站約一個小時路程的地方找到了個有溫泉的小民宿,客人很少,民宿的主人是個老婆婆,笑起來堆滿皺紋的模樣讓人感到相當親切。
晚上,祐巳泡過了溫泉,室內的暖氣也很充足,雖然只穿著浴衣身體還是非常暖和。也許是剛剛溫泉泡得太久了,讓她有點些微的暈眩感。她倚在窗邊喝著熱茶,跟前些日子比起來,祐巳突然有種退休了的閒適。望著夜晚的雪景,窗外雪花紛飛。
她拿起了跟櫃檯借來的信紙和筆,想了想,最後還是先寫下了個字。
久。
我現在在北海道。天氣很冷,雪景很美。
走在雪地裡我一直想著,這麼純淨漂亮的白色,要是能帶回去給妳當禮物就好了。現在正好是雪祭的日子,但我沒有停在札幌,在一個不知名的小車站下了車。記得之前在電視上只要看到雪祭的消息,妳總是興奮不已,我把這段行程保留了下來,不願自己獨享。
我其實並不是特別喜歡冬天的,但自從遇見妳以後,每當冬季來臨我便覺得感謝,因為妳總是那麼輕易地便感到開心,到了令人羨慕的程度。北海道的雪景美到讓人嫉妒,但卻怎麼也比不上那天公園裡的景色,那是我這輩子第一次對東京會下雪這件事感到慶幸。
那麼該進入正題了,久。從東京坐電車到北海道的這段路程,我想了很多。妳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嗎?妳懊惱的神情,略帶怒意的聲線,就像在看電影似的,每一幕都如此清晰。妳生氣的模樣非常嬌艷,讓人忍不住想多欺負妳一點。這些雖然我從來沒有對妳說過,但我的確是在那時就喜歡上妳了。
也許聽起來有些推卸責任,但這就是問題所在。
有人對我說,要是妳一開始就替對方預設出一個形象,而對方做不到妳的要求時就對自己的愛動搖,那所謂的愛,也不過是一個假象罷了。妳是這麼樣地一直在配合我的腳步,而我卻只看得到眼前的事物,忘了這麼簡單的道理,忘了當初喜歡上的妳,忘了當初喜歡上妳的自己。我曾想說是不是久變了,但其實變了的不是妳,妳還是當初那個會因初雪而感動的竹井久,但我已經不是那個陪在妳身邊的加治木祐巳了。
我們之間的問題一直都存在,或是說,我的問題。我把自己跨越不過去的東西,不斷加諸在妳身上,妳是這麼樣一直無條件地承受著我,我卻只是持續地無知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可笑地一個人沾沾自喜。其實我並不是不明白,只是一直看不清而已。當我終於醒來後,才發現其實不是我失去了妳,而是我親手推開了妳。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離開的原因。我只是想找回當初妳所愛的那個加治木祐巳。
久。我們現在的距離也許很遙遠,但我並沒有放棄妳。我沒有辦法去重新寄放感情在別人身上,沒有辦法像愛妳一樣去愛別人。只有這個想法,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如此,以後也不會變。這些話語我從來沒有親口對妳說過,現在竟只能用這種形式傳達給妳,妳應該已經在心裡無數次地怪我自私了吧,直到已經麻痺的程度。這些痛苦本該由我全數承擔的,但我卻是個那麼不負責任的人。一直以來都是如此。
我還有很多話想說,但還是先到這裡吧,茶已經涼了。我很久沒有寫信了,這樣想來,我竟從來沒有親筆寫信給妳過。而且我也不確定妳是否能看到這封信,但我還是寫了。果然我還是很自私的吧。
我會在北海道停留一段時間,我會繼續寫信給妳。
祐巳
三個禮拜後,祐巳坐上了函館往上野的列車,她並沒有直接回到東京,先在青森停留了一段時間,又來到八戶,最後才坐上往東京的新幹線。已經快四月了,列車一路往南,窗外的風景就像是高速播放的攝影機一般,有種冬去春來,只花了三個小時的錯覺。
她上車時買了份報紙,標題非常醒目,她盯著頭版的照片好一段時間,對內容卻沒有細看。下了車她並沒有把報紙帶走,就這樣留在車上。
警笛大聲地響了。站在月台上,祐巳往列車開來的方向望去。北海道的景色、窗櫺上凝結的霜露、紛飛的雪、未開的櫻花。她心想。
一切,都已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