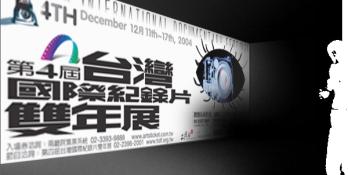
文 /李 志 薔
如果說,1950年代以後,西方國家才正式進入「紀錄世代」;台灣則要遲至八○年代中期才正慢慢開始。台灣早期的紀錄影片,多以新聞片和宣導片的姿態存在,一直要等到陳映真主持「人間」雜誌,阮義忠、張照堂等相繼以黑白攝影和影像紀錄開啟報導文學的先河,才陸續有人投入紀錄片創作的領域。八○年代末起,胡台麗、李道明、吳乙峰、黃明川等人紛紛以人類學誌、弱勢關懷或文學家傳記撐起一片天空,那沈寂已久的暗夜才畫出一道微弱的火光。
九○年代以來,由於解嚴之後社會轉趨成熟,加上電視媒體的推波助瀾,吸引了許多有志者投入紀錄片的領域,題材也從以往的封閉、單一,慢慢擴展開來。舉凡社會運動、民主抗爭、勞工與公娼、原住民文化、弱勢團體、土地倫理、藝術家紀錄、生態觀察與環保議題等等,繁花盛景的圖像,確實令人耳目一新。然而,紀錄片在台灣開始為普羅大眾所重視,並當成一種獨立的創作媒介,亦僅僅是最近幾年的事而已。
近十年來,台灣創作者的紀錄片在國際頻頻得獎,並且由於台南藝術學院的成立,公共電視「紀錄觀點」和「文化容顏」的專播頻道,還有全景和民間影像工作室的大力推廣,民眾們才開始重新認識這種有別於劇情電影和新聞實錄的創作形式,並且認真咀嚼其內容所彰顯出來的社會意義。於是1998年起,一切水到渠成,立法委員王拓的奔走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贊助下,第一屆「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應運而生。這個台灣唯一的國際影展,不僅是國際紀錄片交流和觀摩的場域,更是台灣這塊土地建立起自己的影像紀錄體系,向國際發聲的最佳管道。
兩年舉辦一次的紀錄片雙年展,從1998年以「回歸亞洲」為題,為雙年展跨出自我文化認同的第一步。2000年以「差異新世代」為題,針對世紀交替、新舊交雜下的世界,提出辯證的關照,同時也繼續回應更形熾熱的全球化課題。2002年的雙年展一方面以「再見,台灣激情年代」整理並且挽救了幾乎失散了的街頭運動紀錄片,另一方面,以「距離—開放」引介形式多元的紀錄作品。
今年的影展計有四十多個國家共122部作品獲邀放映。除了「國際競賽」、「亞洲視野」、「台灣獎」等三個競賽單元外,並有七個專題觀摩「互望心中的國界」、「介入媒體」、「比紀錄片還慢」、「凝視死亡」、「天窗─歐洲藝術電視台獨立製片精選」、「評審專題」、「特別放映」等國際觀摩單元。
其中,與我們息息相關者,當然是台灣獎競賽的入圍影片。歷年的參展影片中,老幹和新枝並陳,許多優秀的新生代導演在此發光發熱:蕭菊貞的《銀簪子》、周美玲的《極端寶島》和《私角落》、陳俊志的《美麗少年》、湯湘竹的《山有多高》,還有《流離島影》導演群對顛覆紀錄片實驗美學的嘗試…凡此種種,都漸漸擺脫前行代導演的人文主義美學,企圖發展出屬於台灣自己的紀錄觀點,令人耳目一新。
這些新生代導演,大多出生於戰後二十年,對傳統的束縛都有說不出的疲倦與厭惡,也更沒有「人道關懷」的包袱;傳統的說故事形式已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他們企圖尋找的,是更新、更自我的影像語言,以致在題材上,呈現的是比以往更私密的紀錄形式。舉凡個人或家族歷史的挖掘,青少年次文化的爆發力,以及女性身體與意識的自覺等等,都開拓了比以往更寬廣的影像視野。
延續這樣的創作氛圍,2004年入圍雙年展台灣獎的二十部影片當中,類似的風景圖像益加明顯。更年輕一代的創作者異軍突起:吳靜怡《再會吧,1999》追溯與逝世母親的情感,以象徵性的影像語言,大膽而不流俗的構圖,製造出深刻動人的思親氛圍,不僅結構層次分明,內容亦真摯感人。李家驊《25歲,國小二年級》則深入童年記憶,回溯自身的成長創傷。兩者皆透過影片拍攝,完成了一場療傷書寫的儀式。
另外,陳龍男的《海洋熱》和林育賢的《翻滾吧!男孩》同時展現了青春洋溢的青少年次文化。《海洋熱》描述貢寮海洋音樂祭裡幾個樂團的夢想與熱情;《翻滾吧!男孩》則以類似MTV的節奏,呈現七個國小男孩苦練體操的故事。而郭書鳳《薛西佛斯之福爾摩莎》和史筱筠《藍色咒語》,在紀錄片的形式下,大膽融入劇情與動畫,在在展現出年輕一代導演不甘守舊的企圖與活力。他們皆比前行代導演更關注內在的求索,大膽挖掘自家身世與情感的記憶;或者,乾脆以另一種更輕盈的方式,看待他們所身處的社會。
而在傳統議題上亦是百花齊放,總體而論有不少擲地有聲的成熟之作。不論是以音樂向1930年代的人文歷史記憶致敬的《Viva Tonal跳舞時代》(郭珍弟、簡偉斯導演),或者關注環保生態的《記憶珊瑚》(柯金源、蘇志宗)都有傑出的表現。原住民題材上,王俊雄《霧鹿高八度》呈現布農族在保護與傳承日較消失的傳統文化時,面臨的心理問題。而李中旺《部落之音》則把時空拉回九二一大地震之後,族人之間分裂嫌隙,和重建面臨的種種困難。兩者,都點出了原住民社群在當前社會的困境。
另外,底層人物與邊緣人一直都是紀錄片偏好的題材,除了人物本身戲劇化的遭遇外,這群邊緣人的生活樣貌,正反映我們身處的時代,以及整體社會衍生的病灶種種。陳俊志《幸福備忘錄》關注同志的終極幸福,蔡一峰《假裝看不見》裡的偷渡大陸妹的賣春生涯,楊力州、朱詩倩的《新宿驛,東口以東》則是將場景移至日本,呈現二十年前歌舞妓町台灣女性類似的時代因素。
此外,李道明《離鄉背井去打工》、李淑君《印尼女傭尤尼希》、溫知儀《兒戲》都是描寫當前台灣特殊現象的外籍新娘與外籍勞工的問題。由於經濟發展和社會人力與婚配結構的嚴重失衡,這群外來的「遊牧民族」成了當前台灣必須認真面對的社會課題。
而類似的邊緣人物還有羅興階的《浪人》裡的遊民,鴻鴻《台北波西米亞》的「另類劇場遊牧族」,莊益增、顏蘭權《無米樂》裡認命的老農民,和李立邵《等待》裡印尼的痲瘋村民等。這些人,或懷抱夢想在無情的都市空間執拗地追求,或以道家或修禪的方式看待顛躓的生命,卑微中展現的,自有另一種可敬的人性尊嚴。
誠然,紀錄片的真實影像是深入了解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議題最方便的工具;然而,紀錄真實並不必然完全「反映真實」。近三十年來,全世界的紀錄片已發展出更多元的面貌:無論是在影像美學上的開拓,甚至是劇情紀錄片、表演紀錄片、實驗紀錄片等等不同類型的發展,在在促使人們重新檢視「紀錄與真實」之間的關係。綜觀這次台灣獎的入圍影片,我們欣見導演們除了展現社會批判力外,更能向內、向外求索,開創出諸多奇異的花朵。也期待台灣紀錄片的創作和推廣,都能不斷推陳出新,順利與世界接軌。
(完)
2004.12 月 15日 台灣副刊
為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而寫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