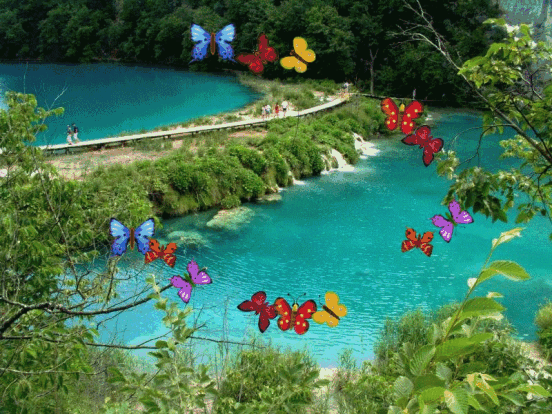
回天,昨晚夢見你。
夢中,人聲喧鬧的酒吧,我坐在黑暗的角落,喝著酒;你開門走了進來,我急忙拿起圍巾遮住臉,不想讓你看到我變了;可是,我又好想拿掉圍巾,大聲告訴你,我沒變。夢中,我掙扎著,夢醒了也是。
我們的認識,是從一封信開始的。
十八年前,我興沖沖到了北京,開始新的學習。對祖國,有期待,有嚮往。出發前,朋友笑我是無可救藥的大中國主義者,我不在乎,我相信中國人合作的世紀就要來臨。
班際聯誼後,很突兀的,收到你寄自宿舍的一封信,你寫著:「常常,坐在教室外陽台水泥短牆上,看著消失於遠山稜線中的落日,不禁想起百年前,香港西醫書院頂樓,孫中山先生。當他看見矇昧無知的同胞與凋弊腐敗的中國,終於從苦難中,撐起整個中國。一樣年輕的醫學生,而我呢,依然是紙上文章……」
我看著信,記起你。
聯誼會上,你的話不多,只是微笑;別人喧嘩,你在傾聽。
我記得你。你,白衣黑褲,短髮潔淨,傲氣不俗;我們燦燦一笑,有如舊識。
我們通信著。
你談自己,「生命二十年的過程中,並不曾有飄零的身世或坎坷的際遇;然而在喧囂的人世裡,卻似乎總有某種寂寞,從四面八方不斷襲來……」
你看國家,「身當斯時斯世,誠有一種不可言喻的痛楚,在內心啃蝕著,縈繞不去。」
第二次再見,是五月,在天安門。我為了看大字報而去,卻看見伏地寫大字報的你。
十尺白布上,是你端正的大字:「民主不能拖延,改革不能拖延」,你又寫著:「照我忠義膽,九死心無愧」,你每寫一句,同學就給你熱烈的掌聲;我從外圍擠向你,卻擠進了歷史。
五月十三日,廣場上的絕食行動開始了。絕食的第五天,是你二十歲生日。
人民英雄紀念碑下,你遞給我一張短籤,你寫著:「古時男子二十歲稱之弱冠,該為自己取字號,今天,我決定自號──回天。因為你不是英雄,你不能叱吒風雲,你無回天之力。」
我看著紙條,呆呆的說不出一句話。廣場上,鮮紅的標語被風吹得沙沙響:「媽,我餓,我把飯留給更餓的人。」我知道你無力回天的痛。
六月三日深夜,天安門的周圍,殺戮開始了,帶槍的解放軍像猛虎出柙,攻擊群眾,廣場中央的我們繼續坐著。
當侯德建說:「我相信留在這裡的同學,沒有一個是怕死的。」大家都哭了,廣播要大家撤退。掙扎一陣子後,外圍的人開始站起來,你牽起我的手,你的手好冰。
我們緊張的離開廣場,走不到十分鐘,卻陷入一場街頭慌亂,槍聲由遠而近,我們越走越快,開始跑了起來。
聽到坦克聲的時候,我幾乎失去跑的力量。黑暗中,我像迷路的小鹿逃竄著,你的手,是牽引我向前的唯一憑藉。
後來,你放開我的手。
你說:「有一位老先生跌倒了。」你飛快的跑去,消失在暗夜裡。
我停下腳步,回頭喊你:「不要去,他可能被槍打到了。」
沒幾十秒,就看到坦克快速開過來,在槍火的微光中,我最後一次看到你的身影。
坦克上,機槍噠噠地向地面掃射,坦克撲向你,你像白紙一樣地倒了下來……,坦克繼續轟隆隆地追趕著我,我邊跑著,哭著,就這樣離開了你。
那夜,在槍聲中,我放聲一路哭,哭你、哭我、哭中國。
我想到你說的「因為你不是英雄,你不能叱吒風雲,你無回天之力。」難道冥冥中,你預見自己的天命?
那一夜,我想,我把一輩子的淚都流光了,以後再沒有任何事值得哭泣。可是你知道嗎?我常覺得,我的哭聲,把你的靈魂牽引出來,你住進我的心裡,我們一起呼吸,形靈不離。
我沒念完書,事件平靜後,我就回到台灣。那個一心回歸祖國的女孩,已經不存在了。
我不知道你贊不贊成?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常常這樣問你,心裡有掙扎。我想到昨夜的夢,我變了嗎?
我愛中國,沒變;愛民主,更多;愛自由,甚於一切。
如果是你,你會怎樣繼續你的生命?
參加這場學運前,你曾說:「我深深相信,生命要以一種更超然的方式延續,而我,正摸索追尋這種方式,我想我會成功的。」你一定成功了,你是永生者,而我的路還長。
回天,什麼時候能再靠近你?也許有一天,中國再沒有殺戮集權;有一天,流亡在異鄉的同學們都能回到家;我也想重新踏上旅程,回到你的故鄉,親吻你倒下的土地,回憶你說過的每一個字。
回天,我懷抱著你的夢想,活在這個紛擾的時代,勇敢地踏出每一步,每一步,都與夢中的你商量。
我想你,日日夜夜,希望今後依然有夢,期待你再入夢……
憶君迢迢隔青天
上有青冥之長天
下有淥水之波瀾
天長路遠魂飛苦
夢魂不到關山難 ------李白
後記:
故事人物純屬虛構
如有雷同
據可靠資料統計
約有2600人
到底死了多少?
中共官方一直算不清楚
不過
總有一天
人民會算清楚的!
紀念六四,舊作重貼。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