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裡是位在城裡時尚區的獨棟五樓公寓,我租屋在頂樓加蓋沒有冷氣設備的雅房,還好不是鐵皮屋。不知何故公寓未與鄰旁大樓合建,也未共壁,像個孤僻的小老頭擠在衣履光鮮的新貴之間,頑固的與眾人保持距離。
樓層雖然不高,然而往下俯視仍令我略感軟怯。沿著護牆我將七、八個花槽圍成ㄇ型,以免不小心太靠近僅過腰身的老舊牆垛。花槽中,鳶尾花開了些許,葉尖尾端的花瓣藍白清朗,綠葉茂盛,花性特有的垂墜拓延開來陣容頗有點聲勢。
若不是礙於現實考量,頂樓加蓋的租屋原本不在我的選項中,但,不要與房東合住、不要與別人分租,要安靜、要自由……,還想種種花,或許再養隻狗……,在這個一般上班族縮食儉用得存上一、二十年才可能購屋的都會,能有更好的選擇嗎?當初領我看屋的仲介誇張的往上一指:況且,整個天空都是妳的!
我的天空?在這彷若空中孤島與天空的雲、的鳥、的星子對望時,總感覺也有什麼在看著我,是上帝?衛星?也可能是遠處凸出建築群矗插雲中的 101大樓裡的上班族,或就是環伺四周的高樓人家。
友人說我太敏感。我知道,他心裡要說的其實是「神經質」。我敲著鍵盤告訴他,放心吧,賃屋之初我即擬好〔緊急撤退計劃〕。我說,樓下路邊植有成列小葉欖仁樹,緊急狀況時若往樓下跳,我一定會記住先後退個 10公尺助跑,然後奮力躍出拋物線,或許尚可寄望被欖仁樹伸展的枝網攔截住,再不濟,應該多少也會緩衝下墜的力道;不過,我的運動細胞實在匱乏,所以平時要多練習跳遠…‥。 skype畫面裡,朋友的筆動了動,又動了動,對話框空白。短暫沉默後跳出「嘿、嘿」說,「不知道要說什麼」,而後補了一句「神經放大條一點,日子會比較好過。」
我耍寶的比比腦袋作勢絞鬆神經(哎呀,真是錯亂了,耍寶給誰看哪?),心底有點酸酸的,然而不想跟誰說,「島」居之初頗長的一段時日,夜不成眠。
搬來沒幾天,原本住在五樓的老太太房東,不小心絆了跤住進醫院,後來痊癒出院,她的兒子就接去同住,外傭也跟去照顧了。房東在樓梯間加了一道鐵門,多了一重屏障,可以說安全,也可以說孤絕。老公寓更安靜了。
成長過程一直處在熱熱鬧鬧的環境,家中人口多又開店做生意,就學住校即使不是大通舖起碼也是八人宿舍;之後自己的家,算是最清靜的,二十多年的兩人世界再加上不曾斷養過的貓狗以及滿院綠言花語。如今租處一房一衛浴的小屋是這頂樓上僅有完備的了。丟棄於一角的花盆和似乎隨時可能傾倒的花架加上搬家公司吊送上來的書櫥皮箱衣鞋碗杯散置身旁,一如沉船被衝上岸的破爛,我,是災難後的倖存者……孤島上的生命除了我,只有一束死命釘在水泥水塔縫隙的半枯野草。
那是個初春的早晨,我蹲在一堆自己的全部之中,把頭埋在膝蓋上,沉思。風,拂過臉頰,涼涼的,我沒有哭,只是在回溯這場災難到底是怎麼回事?現在,我在這裡了,下一步呢?
夜裡,牆在歎息。
房內所有的燈都亮著。孤獨如一隻飢餓的蚊子,在耳際輕哼,細微而清晰。偶而有哪戶人家傳出挪動什物的聲響,大腦立刻下令耳朵豎立警戒;似乎有人輕躡腳步上樓,似乎有人旋轉門把,似乎風在敲窗,夜深沉,啊,是牆在歎息。經過一整個白日的曝曬,夜裡的牆自萬千個毛細孔吁吐熱氣,輕手輕腳剝裂一條條細紋擠壓出它過度承載的心事,來自歲月,來自頂樓無從遮蔽的風霜。入夜我和衣而臥,瞪著頭頂上的燈,看它的光圈忽而暈散矇矓忽而收斂白亮,等著眼皮累了撐不住了,不再聽命繃緊的神經,拉下眼簾沉我於夢的深淵……
感覺未曾閤眼,實則半睡半醒,似睡似醒。朋友交待我,就寢時手機擺在床頭以備緊急之用,其實以我一慌就傻愣的「身手」,這舉動不過是給自己壯膽罷。失眠的焦慮給我汗水涔涔的錯覺,然而,夜幕覆罩的孤島,我不敢起身,不敢開窗。
白天撐住精神在電腦前工作,多份兼職面對不同業務窗口,忙碌喧囂的訊息往返,在只有鍵盤敲打聲的寂靜空間進行。想像頂樓的天空電流交會彳彳擊發電波交織一幅密密麻麻、層層疊疊的網路,伸手可觸,然而無感、無覺。螢幕開啟數個視窗, skype、 msn、 fb、 mail,談正事的、瞎扯的;可與不可言說錯綜複雜的心情在緘默中漫衍,按一個「讚」代以所有情緒,一個符號詮釋所有心情。
極簡。
一如天空下,我的生活。
朋友曾問我怎麼受得了天天上下樓梯?他只來過一回,氣喘吁吁地爬上頂樓來,一邊嘟嚷著,現代人沒有電梯怎麼活呀。或許是我不常出門,倒不覺得五層樓樓階有多累人。其實現代人還蠻容易達到「足不出戶」的,敲幾下盤鍵,採辦足夠存糧宅配到家,即可大隱於市。郵差快遞來按門鈴,我將藤籃用繩索垂降下樓,等信件物品放妥再拉繩上樓,兩相省事。朋友手上提著幾大叢連根帶土的鳶尾花,沒好氣的白了我兩眼,「剛不說?先把花吊上來,害我提那麼重。」
花。找到倚在陽台一角的鳶尾。朋友連培養土都準備齊全了,我卻疏懶的任它躺在大塑膠袋裡。
將鳶尾花取出,一叢一叢平舖於地,悶了幾日,葉的尖端已顯枯黃,這是與我同存於天地的生命哪,我何等殘忍?還好泥土中的花根無恙。分株時根莖清脆的分離聲似掐斷一截新鮮蘆筍,撿來棄在一角的大小花盆花槽,拌土、分株將鳶尾栽植妥當,順便將周圍環境整理一番,勞動了一上午總算大功告成。抹去兩臂薄汗,放眼成排狹長的葉子綠得煞是美麗,雖然初栽每株鳶尾尚歪歪倒倒,然而可感覺到它們在新土裡尋求到安穩,認真的呼吸。孤島不孤。
三日、五日,鳶尾花一株株站直了身,昂然於自己的天空。
春風已杳長夏亦盡,夜魅幾時曳逃的?未察覺從哪天開始我已不再畏怯夜裡的孤島。看暮色漸沉,看小葉欖仁樹的盡頭一大塊未知作用的預定地植被茵茵綠意,難得的未圍起隔板,周邊人行道筆直寬敞,一個個走入暮色終於不見的運動者形影,總要到夜將深了才逐漸安靜。然而僅孤島寂寂罷了,附近夜市人間煙火正繁忙。我已習慣了偶而不當「魯賓遜」,穿著 T恤短褲腳踩藍白拖下樓穿過小巷,悠哉覓食。夜市重油又死鹹的小吃或許不符健康,然而長時間被餵養微波食物的腸胃樂得暫時解放。
夜深深,回到公寓打開大門拾級而上,施施然刻意不放輕腳步,以免驚擾或許正失眠者放出哪一隻耳朵追隨我。
幾日晨起,見水泥地有雨來過的印漬,洗石子護牆水潤的色澤未褪,幾片葉尖猶懸凝珠,夜裡似幻的窸窸窣窣真的是雨的聲音?簷下的石棉板一向聒噪,我竟能酣眠不聞?
花盆表土猶濕潤著,鳶尾花熟盛期後蔫萎的花體重量使它謙虛地俯下身子,也藉此姿態落地生根繁衍下一代,造物主的巧思令我安心,穹蒼懷抱下的鳶尾花與我必然有屬於各自的天空。
─中華副刊2013/0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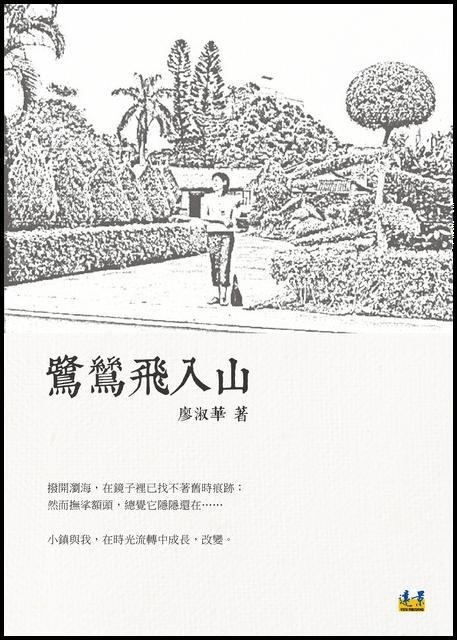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