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07年10月26日,阿盛散文集《夜燕相思燈》新書發表會,會後阿盛、向陽與到場文友合照。
我與阿盛認識甚早,兩人都是1950年代出生的「庄腳囝仔」,是原因之一;在寫作經歷上,大約同時起步,是原因之二;曾經在中國時報有過同事之緣,是原因之三──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我們對台灣這塊土地都有著深厚的感情,我們的寫作不是沒來由的,赤腳走過泥土,我們都為腳下的母土而寫。這使阿盛和我之間,隱約存在著某種書寫的默契。我們的作品有土臭味,因而臭味相投。
阿盛崛起文壇,源於1978年3月在聯合報副刊發表〈廁所的故事〉,獲得詩人楊牧的讚賞,使他受到文壇的矚目。事實上,阿盛早在高中階段就已經開始寫作,編輯學生刊物;高一就在台灣日報副刊發表小說,較諸同年代作家,起步甚早。可惜的是,考上東吳大學中文系之後,卻忽然停了筆,大學四年間一無作品。直到畢業後,才開始重拾筆桿,第一篇作品〈同學們〉刊登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這篇佳作,讓副刊編輯部驚豔,當時負責督導副刊的楊乃藩召見了他,並要他到報社上班。就這樣,阿盛以一篇散文進入了當時同輩作家稱羨的中國時報,擔任副刊編輯,也開始了他此後寫與編的人生旅程。
這是1978年的事。鄉土文學論戰在1977年爆發了將近一年,來自台灣南部新營的阿盛在這個浪頭下出發。一篇〈同學們〉讓他進入主流副刊,一篇〈廁所的故事〉則使他成為文壇鵠望的新銳。他寫台灣的鄉土,寫日常的瑣事,乾淨俐落、妙趣橫生,而不落前人窠臼。這使他可以無懼於鄉土文學論戰的官方論述,理所當然寫自己的鄉土。
1978年我還在當兵,工兵二等兵,帶著圓鍬十字鎬,跟著營隊流浪於台灣南北做工事。畢業前出了第一本詩集《銀杏的仰望》,是詩壇新人,創作力盛而量豐,投稿副刊,發表作品,是當兵時唯一不覺苦悶的事。人間、聯合等各報副刊和各家詩刊也常見我的詩作,就在這樣的投稿過程中,認識了阿盛。但真正相熟,則是在1979年9月我退伍後,來台北進入海山卡片公司擔任文案編輯的事。這一年,中國時報文學獎增加敘事詩獎項,我寫了三百餘行的長詩〈霧社〉參賽,次年二月獎項公布,我得到優等獎,與我聯繫的就是阿盛。
1980年6月,因為詩人商禽的推介,我進入時報周刊擔任編輯,和阿盛成了同事。這時的阿盛由副刊轉到生活版,辦公室離時報周刊很近,我們有了更多共事的機會。他和我聊得來,我們的文學觀點相近,有時也找林文義、陳煌就近找個咖啡館聊天。在這個階段,作為編輯的阿盛已經實際主編生活版,常常丟一個題目,或者找一張相片來,要我及時寫文章,或者看圖寫雯些文字,多半是應急之用;但有時則是特別企畫,我印象中,他曾要我為街頭的各種行業寫短文(例如送報生、豆腐店……),請攝影記者拍照,以圖文刊出,頗獲好評。
1981年9月,阿盛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唱起唐山謠》,這對一個青年作家來說,比結婚還重要,出版後,阿盛送我一本,希望我這個「老兄弟」寫篇評論向讀者推薦,我當然義不容辭,於是以〈質樸而文暢〉為題寫下了我的讀後,刊登於臺灣日報副刊。記得當時我是這樣平價阿盛散文的:
阿盛不是個「美文家」,在他的俚語俗諺中,在他的日常用語裡,我們看不到「徐志摩」的影子,可是我們看到了生命,以及生命的「甜美與苦澀」。通過阿盛,現代散文多闢了一道活水,這道活水從民間來,也流回民間去;不只是見證的鏡,也是引望的窗。
這篇文章距今已經30多年了,於今重看,似乎也沒「走經」多少。阿盛似乎也因此對我的評介產生了信心。從此之後數年,他每有新書出版,我多半成為第一位,為他的書寫序,向讀者推薦他的具有濃厚台灣味的散文,沒記錯的話,我前後為阿盛的書寫了6篇序文,2篇書評,可說是「阿盛讀書會代言人」了。1984年阿盛將他的第一本散文集一拆為二,加入新作,分別出版了《兩面鼓》(批判散文)與《行過急水溪》(抒情散文)兩本集子,確定了他完整的散文風貌。這時我已在自立晚報副刊擔任主編,《兩面鼓》收入的大多是批判散文,包括阿盛應我之邀在自立副刊開的專欄「金角銀邊」的雜文;《行過急水溪》晚了半年出版,收入包括〈廁所的故事〉在內的抒情散文。這兩書都由我寫序,我以「不規不矩求規矩」為題,給予阿盛散文極高的評價,指出「散文阿盛」的特色就在於打破規矩、自塑規矩,說他的散文已經「在當代散文中,獨樹冷峻奇峰」。如今看來,我對老兄弟阿盛,果然沒看走眼。
這個時期的阿盛,來到創作的高峰,但他對自己的書寫又抱持甚麼看法呢?我從書房中找出1984年4月阿盛親手書寫的一篇未落題的自述文章,用「中國時報稿紙」(一張200字),寫了8頁。我在首頁上用鋼筆標註「阿盛自述/ 73年4月」;頁邊又有「呈致 方梓」字樣──我已經忘了這篇阿盛自述是否曾發表過?但是它一直留在我的書房內,並且攀爬著歲月泛黃的爪痕。這年34歲的阿盛,如此述說自己的寫作觀點:

** 1984年4月,阿盛自述文稿首頁。

*** 阿盛自述文稿第5頁,強調「一篇敘述小時候祖母如何為自己把尿的文章,好過一篇失戀後寫給女孩看的衷心話」。
「個人」的看法是,別離開共通的人性、別脫開群體的社會,倒也不一定實用,說實用太玄,不過,私心式的呢喃,關門式的夢話,我極不喜歡,一篇敘述小時候祖母如何為自己把尿的文章,好過一篇失戀後寫給女孩看的衷心話,還要動人。我出生在戰後破敗的鄉下,一切都很簡陋,懂得很多活在泥土上的人該懂得的人類活動,這對我的寫作很有幫助。我不喜歡水泥鋼筋及三房兩廳兩廁,那是生力麵,小攤子小飯鋪最好,只要衛生點,則幾乎無缺失,寫作亦如此。
這段自述,很有個性地表現了阿盛不同於流俗、不喜於呢喃夢囈、風花雪月的創作觀:人、社會和土地,才是他關注的對象。這就是阿盛的本質,散文阿盛獨樹一格的文風就由這樣的本質發散開來,如台灣野地的百合。
也在這個時期,阿盛忽有改用筆名的念頭。這年8月27日,阿盛寫了一封信給我,前段先說《兩面鼓》已要再版,想請林文義寫篇書評,在自立副刊,問我可否。次段則說:
我決定更改筆名為「盛其躬」,自日前「犬養十一郎正傳」後,不再使用「阿盛」筆名,特此奉告,此中涵意,在於寫作風格力求更新自我突破,嘗試不同的筆調、方向,盡力而已。
我收此信,頓時愣住,一個已經成名的作家,要改筆名,這也是大事,詩人「葉珊」改名「楊牧」的時候,詩壇就有過一段難以適應的期間,最後還是因為楊牧以新作品、新路向來昭告一個傑出詩人的存在。當時我猜想,阿盛也是在這樣的心情下「厭棄」了帶有泥土味的「阿盛」的嗎?而想以「盛其躬」來調整文風,要「躬逢」一個「其盛」的新的文風嗎?
我贊同阿盛想要突破舊有文風的想法,但我不贊成他想想要改筆名的做法。我沒有回應。一個半月後,阿盛又發了一張明信片給我。說「盛其躬這筆名不好」,「他日再作研究可也」,又說「你若有意幫我想一個筆名更佳」。我可不上當,好好的「阿盛」,沒有特殊原因,改筆名幹嘛。

**** 1984年8月27日,阿盛給向陽的信,說他要更改筆名為「盛其躬」,後作罷。
這可算是「秘辛」了。我若不寫,大概連阿盛也忘了28年前他曾動過改筆名的念頭了吧。
幸好阿盛沒改為「躬其盛」,否則台灣文壇可能少掉一位足以表現台灣味的散文大家。阿盛繼續寫著,1985年他推出散文集《綠袖紅塵》、1986年出版《春秋麻黃》,更加鞏固了他特有的文風,同時也顯現了他由鄉村事物寫到都市風情的傑出筆力。屬於散文阿盛的年代由此展開,到2007年出版《夜燕相思燈》為止,他總計出版了27本文集,包含詩集《台灣國風》和兩部長篇小說。阿盛創作量之豐、質之佳,已經可以由這些作品來說話了。以近著《夜燕相思燈》來看,我認為這是散文阿盛的另一個高峰,我在為該書寫的推薦詞是這樣說的:
阿盛散文雜糅古典與現代、鄉土與都會,隨心運轉,隨意鋪排,展現俚俗和典雅爭勝、詼諧與嚴肅共存的獨特文風。這本新著《夜燕相思燈》以常民社會為素材,寫人間生活的百般無奈、人性深層的萬端矛盾,左刨右削,上諷下刺,笑中帶淚、淚中見笑,允為替小民吐怨氣,為亂世開不平之佳構。讀後拍案,無錯!
春夜燈下念老友,翻出阿盛寫於1984年的文稿、信函,重新回想我與阿盛的文字往來,閱讀曾經為阿盛著作寫過的書評與序文,這才感覺時光如此催人,歲月如斯易逝。阿盛與我已不再是當年的青壯作家,滿懷雄心,欲開文學新路。唯對書寫台灣土地與人民,則從不休止。
我想到2010年11月,阿盛以他散文書寫的成就榮獲吳三連獎,我以基金會副秘書長身分主持頒獎典禮,用台語朗讀評審委員會評定書。兩個交往30多年的「老兄弟」,當年初識時豈知會有今日這一幕?而阿盛上台領獎後,發表得獎感言的一段話,則令我動容。就以阿盛當天說的話作為本文的結束吧:
我執筆像是拿鋤頭,在文學土地上耕作。三十多年來我很感念我母親,她從不干涉我要走哪條路,有一次她上台北找我,看我半夜趕稿,問我寫作這麼久,是一直無法合格嗎?我說寫作可以賺錢。快截稿時,她問我說,怎麼不多寫一點?…我常在想:寫作真的是給大家看爽就好嗎?我不認為如此。寫作像是耕種一樣,根植於這片土地,發芽、開花、結果,永遠有著最深的感情。這塊母土雖小,但沒有第二塊,不可能再多或再少,我的寫作就是為了這塊母土。
《南一國文教學誌》,2012年7月,頁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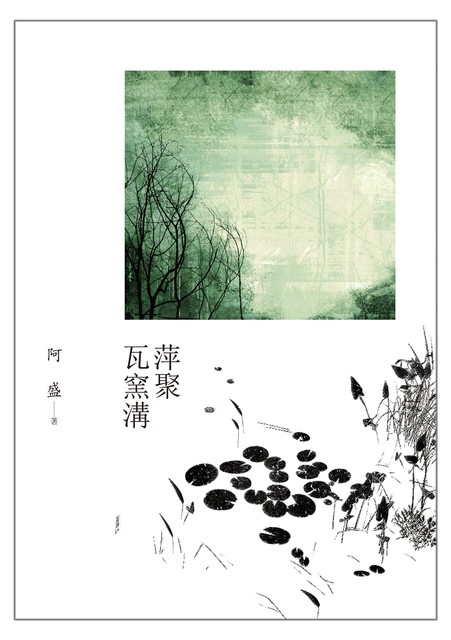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