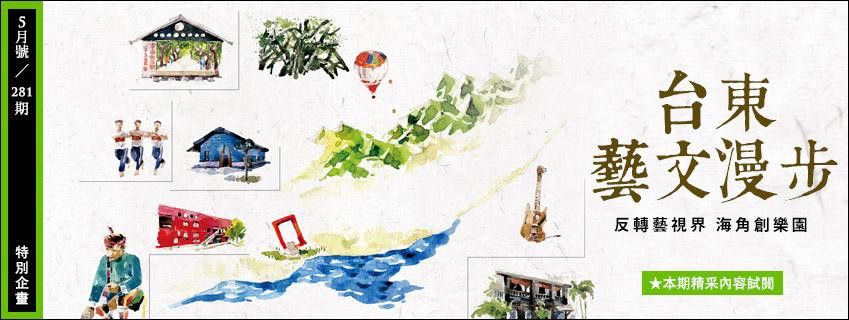
1995年,一個遇到觀眾態度不佳會罷演的部落劇場,由布農文教基金會催生。2002年,一群無分族群的藝術創作者游牧於金樽海灘,是為意識部落的誕生。2000年,陳明才與逗小花離開九二一地震災區,移居都蘭。1999至2001年間,在太巴塱阿美族藝術家阿道.巴辣夫.冉而山穿針引線之下,阿桑(A-Sun,布農語「鳥巢」、「窩」之意)劇團、漠古大唉(Makota'ay,阿美語「溪水混濁」之意)劇團、都蘭山劇團相繼成立,概計台東的表演團體,當然,更不用說還有台東劇團,、卑南族南王部落的高山舞集、調查與發揚馬蘭阿美複音的杵音文化藝術團、以及近年成立的布拉瑞揚B.D.C舞團。
這些藝術家、團體及空間,彼此多少都有交會的時候。其中的多數人,同時也都是台東社會運動的中堅份子,近年,從較顯著的議題,例如反核廢、反美麗灣等運動,藝術以表演、文件、設計、裝置顯現,藝術家不只用音樂、行為藝術、繪畫創作,甚至用走路實踐社會行為。2013年4月初那一場從都蘭鼻海域,陳明才投海處出發,集結各族群、領域二十餘人,走向凱達格蘭大道,為期16天的「不要告別東海岸徒步行動」,就是一場報信,同時聆聽、蒐集其他部落訊息,進而肉身地傳遞自然的土地觀的集體行為。行動隊成員踩在烈日水泥公路的步伐,猶如象群深沉的腳步,振發隱入大地的頻率,連結遙遠的同伴。
藝術創作與社會運動的結合,在台東何其緊密。要說是激進,其實更古典。從部落的視角,文化、經濟與社會本來就是一體,是「現代」切割、分類了它們。而對他們來說,他們先是人,才是藝術家。
2002春天於金樽持續長達三個月的意識部落,是藝術家思索「自主性」的重要場景,且效應擴散、發酵至今。藝術家對自我創作主體的尋找、自剖與國家文化資源的關係等種種掙扎與徬徨,因此經過一次洗鍊。研究者許瀞月於〈地下塊莖圖譜:安聖惠(峨冷.魯魯安)的藝術創作〉一文,這麼詮釋意識部落:「一方面他們的實驗是一種脫離社會科層制式生活,透過沉思冥想,學習祖先生活的態度──藝術家們雖然都是要讓自己鬆脫觀念的疆界,追求野性的思維,可是並不是要讓自己生活在原始社會;另一方面,達卡鬧表示他們除了輕鬆談笑,始終關心的話題是原住民的未來。」整理依斯坦達霍松安.那布的說法,意識部落形構了一個游牧式的共同體,具有脫疆界的集結型態,創作慾望必須先於國家文化資源,亦確立「決策者即參與者」的會議模式,這些也是之後發生於台東的諸多藝術、社會行動場域的特質。
那布也是布農文教基金會的文化部長、阿桑劇團的催生者之一。阿桑以戲劇進行部落文史、凝聚部落意識,2003年作品《內本鹿事件簿一.海樹兒的故事》以1941年日據時期內本鹿部落布農族人被迫遷村的歷史事件為題材,通過「現在」的眼光及劇場化的詮釋,面對這段殖民傷痕,挖掘出再現樂舞做為原住民劇場表述主體的另一種途徑,因為傳統既已消失於現實,那麼更要將「現實還有什麼」擺在眼前。當時這些劇團的成立所延伸出的一條軸線是「部落劇場」的討論與實踐,其與原住民劇場之名的差異、兩者與族群文化情境的相適性,都依然存有值得繼續追索、對話的意義。
阿道與阿緹蓉這對夫妻檔創立的漠古大唉劇團(2001),可說是冉而山劇場的前身,兩團的起點也都是策辦「原住民成人戲劇表演藝術研習營」,四面八方邀來的講師與學員,在少則一週多則半個月的課程期間共同生活、作夢、學習,日出而作,日落亦不息。
「巫者舞也」,「祭」者「劇」也;
升火祭場亦生活劇場,更是「創造」之泉。--阿道.巴辣夫.冉而山
巫與舞、祭場與劇場、生活與藝術之間的關連,阿道自有一套轉換的心法。講個比參與式劇場還參與的例子,2010年某一天,阿道在都蘭糖廠表演《二十四小時巴來訪行為.藝術.集》(PalaFang,阿美語「誠心款待」之意),那天我從花蓮一路騎車下去,遲到了幾小時,阿道已帶屈指可數的參與者到金樽拿新鮮的食材,然後所有人回到糖廠,希巨.蘇飛(木雕家、都蘭山劇團團長)的木雕工作室工寮,吃東西,聊天,喝飲料,聊天,中間請希巨放映、導讀《路有多長》紀錄片,因為講的正是都蘭部落阿美族台籍老兵的故事,也是希巨長年著力調查、訪問的部落歷史。這場行為直至凌晨時分,所有人都撐不住去睡了,才隨之告終。如果要問我究竟表演了什麼?我只能說,什麼也沒有發生,卻很難忘記親身經驗整個過程,所留下來的,無以名狀的感覺。
「其實像包紮漂流木的過程,我是要包紮一個受傷的大地,那個難過都在包紮的行為,跟後來畫在上面的畫。應該也是療癒自己,好像你無從跟誰怎麼說,因為再怎麼說,它就是一個事實了。」2011年,意識部落發起成員見維.巴里,在杉原灣做了一件行為《沒有海,我的冰箱怎麼辦》,在電視台受訪時他表白心境。那一年,東岸藝術家在美麗灣渡假村飯店前發起為期一個月的「違.離」集體藝術行動,夜以作日,駐地創作。重要的原住民藝術書寫者及策展人李韻儀於〈藝術修行者~見維.巴里〉一文認為,這是「繼2002年金樽的『意識部落』行動之後,東海岸藝術家們第二次海邊的集體生活創作實踐」。
意識部落的持續力以不斷變形,可伸能縮的彈性樣態繼續呼吸,追問什麼是藝術與實踐什麼是生活同等重要。「生活」不只是把握當下,更不是把自然當作保護傘,而是與自身的藝術、生命,互為觀照,如陳明才留給我們的啟示:
我是個劇場工作者,面對東部的大山大海,我不再僅從純藝術面去思謀突破創作之道,而是很自然地以大地、環境、區域性、生活為基礎來觀照藝術文化。藝術不再是唯一的,它就是整個大自然之一環。(〈天佑都蘭鼻-獻給眷顧我們的大海〉,《奇怪的溫度》)
※刊於《PAR表演藝術》281期特別企劃「台東藝文漫步」(2016.5)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