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頻臨失衡的地球—生態與人類精神】 美國─阿爾·戈爾著(17)
(註:戈爾是美國克林頓總統時代的副總統—1992年著書)
《結論》
生命運動不息變化不止。太陽與大地,水與空氣,為我們培育出累累果實。我們得到這些果實的滋養,不斷地生長和創造、破壞和死亡、撫育和組織。我們自己在改變,世界也隨著我們改變。人類社會生長得越來越巨大複雜,於是向自然世界索取的也越來越多。每一天我們都向大地的儲藏庫挖掘得更深,使用更多的儲藏品,同時也就產生出各式各樣越來越多的廢物。變化孕育變化,從它自己汲取動力,直到有一大,整個地球似乎加速沖向一種意味深長的轉變。
在本書的前面,我描述過兩類變化。一種變化逐漸而緩慢,我們的日常生活是一個典型。另一種是劇烈而系統的變化,這時,一個模式會突然從一種平衡態轉變為另一種。但還有第三種變化,它把前兩種變化的要素結合在一起。布魯克黑文國家試驗室的兩位物理學家,P.拜克和K.陳,提出了一種新理論,叫作“自組織臨界態”。它描述了這第三種變化的一種式樣。這個理論初一聽有點複雜,但我相信它特別有助於我們瞭解變化的動力學——無論是我們生活中的變化還是世界大勢的變化。
拜克和陳開始研究的東西簡單極了:沙堆。他們把沙子一粒一粒倒在桌面上,先形成了一個沙堆,然後越來越高。他們一面仔細觀察,一面借助於慢鏡頭錄影和電腦類比,考察每一個新沙粒落在沙堆頂上的時候沙堆裏確切有幾顆沙粒被觸動。沙堆堆高時,單獨一粒沙子就可能引發一場小沙崩,有時甚至引發一場大沙崩,雖然這種情況較少。但是,不管小沙崩還是大沙崩,都是由所有沙粒的累積作用慢慢造成的——一次次小變化逐漸改變了沙堆的結構,終於使大沙崩比較容易發生。
常識會告訴我們,大多數沙粒錯位,只是由很少幾粒別的沙粒引起的,而且對整個沙堆也沒什麼明顯影響,然而,大多數這樣錯位元的沙粒對後來發生的事情其實具有極大的影響。它們為今後大大小小的改變創造了機會。令人吃驚的是,我們可以用數學準確地算出每個新沙粒引起多少沙粒錯位和各種規模的沙崩的概率之間的關係。
不過,這裏還有一點是很重要的。一個沙堆必須達到所謂臨界狀態,即每一個沙粒這時都和沙堆裏的所有其他沙粒具有直接或間接的力學接觸,一粒落沙才可能使得沙堆發生上述那類可以預測的反應。達到臨界狀態的沙堆從來不可能處於平衡態。一旦沙堆裏的所有沙粒都有了力學接觸,每個新落上來的沙粒就會把對它的作用的“作用力回聲”一層層傳下整個沙堆,無論這種回聲是多麼微弱。新落下來的沙粒就這樣把它的作用力傳遞到整個沙堆,使得某些沙粒易位,同時也就多多少少重構了整個沙堆。在這個意義上,沙堆“記住”了每個新沙粒的作用,這種記憶整體地或全息地儲存在所有沙粒之間的相對位置之中,儲存在沙堆本身的三維形狀之中。
沙堆理論描述了一種自我組織的臨界狀態。我們忍不住會拿它來比喻人生發展的過程。個性的形成就像沙堆的形成。一個人的各條主線定了型,他就到達了臨界狀態。每一個成形的個性都是獨一無二的,都會以不同的方式接受新事件的影響。這時候,新經驗的作用就通過振盪傳遍整個性情,有時候這種作用直接表現出來,有時候則間接地為將來發生的改變作了準備。新經驗通常附加在已經成熟的個性之上,不過,人到中年,沙粒有時候會不斷堆高,就仿佛還在尋找另一種成熟的形狀。這種不穩定的結構會讓一個人發生一系列的改變。心理學常把這種現象稱作更年期轉變。很長一段時期積累起來的細微變化結合在一起,最後可能爆發為一次情緒的雪崩。一個小小的刺激就可以觸發這種情緒劇變。這種劇變有時候並不根本改變一個人成熟時的基本形態,而是使他的人格更加雄厚,就像一個更高大的沙堆,質量更大,各個方面更加厚實。
拜克和陳在描述沙堆理論的時候使用的辭彙和我不盡相同。我說“成形過程”,他們說“未臨界狀態”,我說“成熟的形狀”,他們說“臨界狀態”,我說繼續堆高的不穩定狀態,他們說“超臨界狀態”。瞭解他們對術語的使用,我們就不難理解他們的結論了。
未臨界狀態會一直增長,直到達到臨界狀態。如果沙堆大於臨界值,那就是超臨界狀態了。這時候發生的沙崩,其規模會遠遠比臨界狀態引致的沙崩大得多。處於超臨界狀態的沙堆會不斷發生沙崩,直到再次達到臨界值。未臨界狀態和超臨界狀態都會自然而然地向臨界狀態發展。
我受到這個理論的吸引,部分是由於它有助我理解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有助我把我兒子的可怕事故及隨後那段日於承受下來。那次事故險些使我兒子喪生。就在那之前的一段時間裏,又發生過另外一些變化。這些痛苦的經驗一個個疊加到一起,使我感到自己的生活進入了超臨界狀態。改變使我的整個生活一層層經歷了振盪,但最終卻把我帶回像從前一樣的成熟狀態,只是現在變得更充實更深厚。我有了一種更清楚的眼光來看待我自己,來看待我此生想要完成的工作。我現在就以這樣的眼光展望將來。
聲名遠播的心理學家埃裏克森首次記錄並描述了我們人人都經驗過的人生各發展階段。他同樣記述下來,我們從一個階段發展到另一個階段,會面臨一串可以預料的危機。他解釋說,這些危機有時是必要的,否則我們就可能陷入某種解不開的衝突而不再繼續成長。我有幸在埃裏克森教授指導下從事研究。我那時正處在人生的一個尷尬階段,在這個階段,一個人心理上的首要任務是發現並確定自己是個什麼人。我現在則到達了一個階段,用埃裏克森的話來說,這個階段的中心是“養育後代”。按照埃裏克森及其門徒的見解,這個階段之前,大多數人首先需要學會充分地與他人交流,學會互相信任。而在步入中年之後,對人生危機的進一步解決,將使一個人能夠對很多他人產生關心,具備樹立和引導下一代的能力。養育後代,這是人一生中最富有生產力最豐饒的階段,這一人生階段的核心就在於為將來培育果實。
上面的兩個比喻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現階段人與地球的關係呢?也許可以說,人類文明現在已經越過了未臨界狀態,到達了某種成熟的形態,到達了世界共同體或地球村的階段。也許我們這個物種臨近了更年期危機?人們對急劇發生的變化的不斷累積越來越心感焦慮,這似乎在預兆越來越巨大的雪崩將向我們的文化和社會壓頂而來,將把家庭這一類傳統建制連根拔起,把一直滋養著我們對未來的關切的那些價值統統埋葬。每一個人每一個社團都互相分隔,他們的所作所為的確會引起振動,這振動會波及整個世界,但我們卻似乎不能夠在分離我們的鴻溝之上架設起一道橋梁。難道我們註定要被性別、種族和語言分隔,而人類文明註定要陷在互相隔離的民族、宗教、宗族和政治體系之間的衝突中不能自拔?我們現在具備的能力足以在全球規模影響環境,那我們是不是也已經足夠成熟,把地球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照料呢?難道我們還是些年輕人,剛剛生長出新的力量,卻不瞭解自己的力量何在,擋不住逞一時之快的欲望?抑或我們已經臨近文明的一個新紀元,在這個養育後代的階段,我們將集中關注未來的一代一代?目前關於可持續發展的討論,說來說去,就是關於養育後代的討論。然而,我們是否當真作好了準備,從短期思維模式轉變為長期思考?
這些問題很難回答,甚至不可能回答。這既因為眼下發生的改變是長期積累下來的,也因為人類文明發生的變化及人與環境的關係的變化現在的確具有全球性質。我們回過頭來看一看沙堆的比喻,考慮一下拜克和陳兩人所報告的一種現象。這種現象表明,某個臨界系統的大規模變化十分複雜,要加以理解就很不容易,要預測就更難了。
通過對沙堆某一特定區域的觀察,我們不難確定導致沙子下落的機制,甚至可以預言在短期內是否會發生沙崩。然而局部的觀察者仍將無法預言是否會發生大規模的沙崩,因為那是整個沙堆的全部歷史的結果。無論局部動力學的情況如何,發生沙崩的頻率相對來說總是很高的,而且這一頻率無法變更。臨界狀態是沙堆的一種整體性質。
臭氧洞就是個突出的例子。這個例子表明,人類文明把危險的化學氣體排放到大氣中,使大氣的整體模式產生出了無法預測的後果。臭氧層總體上在損耗,這是可以預料的。但南極上空的臭氧層忽然變得那麼薄,近乎于完全消失,這種“雪崩效應”卻完全始料不及。既然我們仍舊在增加同一類的氣體,類似的變化肯定還要發生,雖然我們不一定知道什麼時候發生。就全球變暖來說,當然也很可能發生類似的突發事件:我們把越來越多的溫室氣體排放到大氣裏,很難相信其後果僅僅是全球變暖。全球變暖問題本來就比臭氧層損耗問題更廣泛也更嚴重,而只要我們的作法無所改變,那就可以肯定氣候遲早會出現雪崩式的改變。而且,幾種重要的改變幾乎同時發生,其產生的後果就更可能是一場嚴重的災難了。
且不說我們對生態系統造成了日益加重的威脅。人類文明內部正在發生的劇烈變化也很可能對文明本身的品質和穩定構成嚴重威脅。每十年增加10億人口,這造成了一系列的難題。單單人口爆炸就要把世界文明推到超臨界狀態,從而可能出現不可預測的雪崩式變化。為了對付這類危險的事變,我們必須嘗試尋找盡快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的道路,對我們塑造自己的未來的能力獲取某種成熟的理解。就像埃裏克森曾寫過的那樣:“整個種族面臨毀滅,這種可能才使得整個種族的倫理成為必要。”
面對全球環境惡化這樣巨大的困境,我們很容易覺得泰山壓頂,無能作出任何改變。然而我們必須拋開這樣的態度,因為只要當許多許多個人都承擔起自己的那份責任,才有可能解決這一危機。我們可以教育自己教育別人,可以從自己開始最低限度地使用資源,可以更積極地參與政治要求變革。通過這些辦法以及其它很多辦法,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起到作用。最重要的也許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估量一下自己和自然世界的關係,從性情的最深處刷新與自然世界的聯繫。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就必須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重建真誠。
人類始終力求生活得有目的。就此而論,20世紀對人類不算仁慈。兩次世界大戰,滅猶太屠殺,核武器,現在又來了全球環境危機。我們中的許多人會懷疑人類能不能存活下去,更別說過上清明快樂充滿希望的生活了。我們躲進工業文明製造出的種種富有誘惑性的工具和技術裏面,徒然生出更多的問題來,因為我們互相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離開我們的根基也越來越遠。我們把自我狹隘地定義為與他人與世界完全分離的東西。我們只關心自我,而且把這種關心當作所有社會交往和文明整體背後的首要動力。我們開始忘記反復考驗的真理,只看重強有力的影像。我們開始相信,面臨可能發生的滅頂之災,只有這些反映並放大了自我的影像才有意義。但這種回應不可能持久,終於,它讓位給了另一種感覺——真實而正當的生活在從我們身邊滑走。在我看,強調自我的影像已經變成了大潮流,以致我們陷入了集體認同危機。我好多年來一直在努力追索我自己的真相,我認識的其他很多人也是這樣。從來沒有那麼多人在問:“我們是誰?我們的生活意義何在?”各種世界性宗教都重新興起了原教旨主義,從伊斯蘭教到猶太教到印度教到基督教;新的宗教運動、意識形態和形形色色的崇拜此起彼伏;新時代的說教風行於世;世界各地文化的神話和故事讓人五迷三道。所有這些都是明證,說明我們的現代文明的確遇上了精神危機,這一文明的中心基礎似乎只是一片空虛,沒有一種比自我更大的生活意義。
就我自己的追索而論,我最終既更好地理解了自己,也更好地理解到我們能為拯救環境做些什麼。也許因此我開始相信一種心靈的生態,它與健康的自然生態一樣,都依賴于平衡和整體的原則。例如,過於注重內心似乎會導致一個人與世界格格不入,從而不能夠從與他人的交往中汲取精神養料。反過來,過於注重他人,乃至於不能在自己心中默默地理解,似乎會使人們變得行如路人。的確,關鍵在於平衡——慎思與行動的平衡,個人關切與社會責任的平衡,對自然的熱愛和對神奇的人類文明的熱愛的平衡。這是我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尋求的平衡。有些習性和誘惑會把我們從真誠引開,就像狂歡節遊行的旋轉木馬那樣一會兒把我們甩到這邊,一會兒把我們拋到那邊,直到我們的靈魂迷迷糊糊不辨南北。但我希望,而且也相信,我們大家都能找到一條途徑,擺脫所有這類習性和誘惑加在我們身上的動量。
如果人真能把握自己的航程——我相信我們能——,那我確信應該從信仰開始。在我看,信仰有似某種精神的陀螺,它在自己的圓周裏旋轉,裏裏外外保持著穩定的平衡。當然,若不賦予信仰以個人意義,它就只是一個空名。我個人堅信不移,上帝是世界的創造者和維持者;我在個人內心深處理解基督並與基督相聯繫;我在所有人、所有生命和所有事物那裏都感覺到恒常的神性。這些是我的信仰的根基。但我也願再次肯定:世上存在著啟示的力量。具有信仰的人們看來早就明白這一點,只是我們的文明便它變得模糊了。信仰的真髓在於:以不可阻撓的決心去堅信比我們自己更廣大的精神現實。我相信,信仰才是首要的力量,使我們能夠選擇意義與方向,並在生命的混亂挫折之中加以堅持。
我同時也認為,我們大家都經常會看不清在似乎無關輕重的道德選擇和後果重大的道德選擇之間有一種聯繫。然而,在我們的一切選擇中都刻意遵循正義原則,無論這些選擇多麼微小,它們都有助於正義在世界上發揚光大。反過來,一個人若屈服於誘惑,在作出微小的選擇時不顧道德後果,他在面臨重大選擇的時候也多半會那樣去做。在我們的個人生活和政治決策中,我們同樣負有道德上的責任,認真從事,抗拒誘惑,誠心待人,對我們的所作所為負責——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集體。我們是同一個陀螺,它要麼保持平衡,要麼失去平衡。亞里斯多德有言:“德性是一。”
我們和地球的關係現在失去了平衡。對文明整體來說,重建這一平衡所亟需的信仰是我們的確還有一個未來的信仰。我們可以對這個未來充滿信仰,努力成就它保護它。我們也可以隨波逐流,仿佛哪一天就不再有後代來繼承我們的遺志。地球瀕臨失衡;選擇在我們手中。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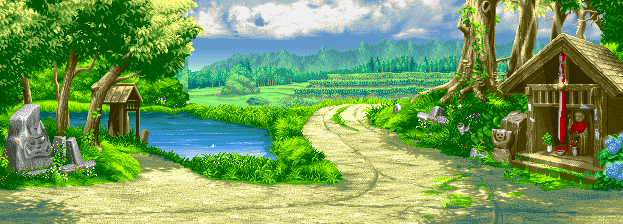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