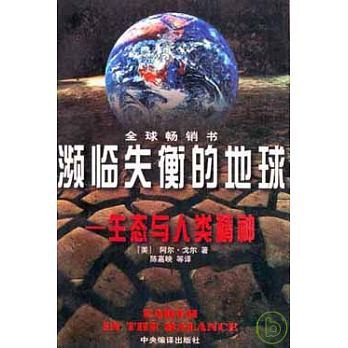
【頻臨失衡的地球—生態與人類精神】 美國─阿爾·戈爾著(13)
《第二部分-尋求平衡》第十二章 機能失調的文明
每一個人類社會的核心處都有一系列說法,用來回答人類最基本的問題:我們是誰?我們為何來到世間?然而,當人與自然之間那種破壞性的關係模式日益顯露時,我們便開始疑惑那些古老的說法是否真有道理。有時,我們甚至想為人類文明的意義和目的創造新的說法。有個名叫“深層生態主義者”的團體現在名聲日隆。它用一種災病來比喻人與自然的關係。按照這一說法,人類的作用有如病原體,是一種使地球出疹發燒的細菌,威脅著地球基本的生命機能。深層生態主義者把我們人類說成是一種全球癌症,它不受控制地擴張,在城市中惡性轉移,為了自己的營養和健康攫取地球以保證自身所需的資源。深層生態學的另一種說法是,地球是個大型生物,人類文明是地球這個行星的愛滋病毒,反複危害其健康和平衡,使地球不能保持免疫能力。按照這種比喻,全球變暖就是地球受害而拼命反擊入侵病毒時發燒,上述病毒的廢棄物已開始污染了地球有機體正常的新陳代謝過程。當病毒迅速繁殖時,受害者的發燒標誌著其“身體”正在調集抗體以攻擊入侵的病原體,意在摧毀它們,拯救自身。
我以為這種比喻是絕對錯誤的。它的明顯問題在於把人類定義為地球上瘟疫的載體,天然就是傳染散播破壞的。這種比喻的內在邏輯只會導向唯一的藥方:從地球上消滅人。有個擁護深層生態學的團體叫“地球高於一切”,其領導人之一M.羅塞爾曾說:“你們聽說過自然之死,這真的會發生。但是,如果砍掉食物鏈上最高的一環,自然界就能重新建構——而這最高的一環就是我們自己。”
某些把這種說法當作微言大義的人實際上是在鼓吹為保護地球而對人類宣戰。他們認為,抗原的作用就是延緩疾病的傳播,給地球以時間來聚集力量反擊,如果必要,則消滅入侵者。“地球高於一切”的又一創建者D.弗爾曼是這樣說的:“現在應是地球上出現一個武士社會的時候了,它應挺身與災難之神相對抗,成為反擊那些蹂躪這個寶貴而美麗的星球的人類瘟疫的抗原”。(應該補充一句,有些深層生態主義者是更為慎思周全的。”
這種比喻在道德上無法接受。此外,它的另一問題是,它難以提供一個準確或可信的解釋,說明我們是誰,我們如何能找到所述危機的解救之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笛卡爾、培根及科學革命的其他建築師把人類定義為游離於物質世界之外的靈智,而在今天,為深層生態學的定義正名的挪威哲學家A.內斯和其他許多深層生態主義者似乎也將人類定義為地球上的異化存在。這是人類與地球離異的笛卡爾哲學的現代版本,但他們達到這一結論的途徑恰好與笛卡爾相反,這頗為耐人尋味。深層生態主義者並不把人視為抽象思想的生物,只通過邏輯和理論與地球相聯繫。他們犯了一個相反的錯誤,即幾乎完全從物質意義上來定義人與地球的關係——仿佛我們只是些人形皮囊,命裏註定要幹本能的壞事,不具有智慧或自由意志來理解和改變自己的生存方式。
按照笛卡爾的解說,我們與地球無關,有權將地球僅僅視為一堆無生命力的資源,可以隨意掠取。這種根本性的錯覺導致了我們今天的危機。但若說深層生態主義者的新解說也是一種危險的錯誤,它起碼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什麼樣的新解說能夠解釋人類文明與地球的關係,我們是如何走到這危機的?答案中有一部分是清楚的:我們的新解說必須能闡明並促進在人類與地球之間建立自然健康的關係的基本問題。過去有個老說法:上帝讓人類與地球訂約,由人承當好管家和忠仆之職。在人們歪曲誤解這一說法以便迎合笛卡爾式的世界觀之前,它曾是一種有力、高尚而正當的解釋,說明了人類在與上帝之地球的關係上扮演的角色。今天,我們要做的事是排除歪曲,重新講述這個故事。
然而,只有當我們弄清人類與地球之間的危機是怎樣產生的,能夠怎樣解決,我們才能講述新的故事。為達到新的領悟,我們必須考慮笛卡爾脫離肉體的純靈智模式的所有後果。
感覺代表著精神與肉體的基本聯繫,換一種說法,它代表著人類靈智與物質世界的聯繫。由於現代文明認為二者之間有天地之別,我們覺得有必要建立一系列精巧的文化規則,以鼓勵思想的充分表達,同時壓抑感覺與情緒的表達。
現在,人們最終認識到,這些文化規則中有很多條與我們認識到的人性基礎全然不符。人性的基礎之一當然是人的大腦,它是在進化遺傳中積累生成的。在我們的大腦中,最基本和原始的部分負責身體運動和直覺,大腦中最後發展起來的主要構造負責抽象思維,被稱為新皮層。在二者之間則是負責情感的那一大部分,被稱為腦邊緣系統。人只作為抽象思想而存在,這種說法當真會變成一種十分荒謬的觀點,好像即在大腦中,只有新皮層才真正發揮作用。
抽象思維只不過是感知的一個分支。我們的情感、感覺、對自己身體和外部自然的知覺,這一切對我們從精神上和肉體上體驗生活都是不可缺少的。僅僅依據新皮層的分析能力定義人的本質會造成一個不可容忍的兩難命題:當我們大腦的其他部分流溢著情感和直覺時,我們怎能僅僅關注抽象思維呢?
堅持認定新皮層的至高地位要付出高昂代價,因為人本來是作為物質和精神充分統一的整體來體驗生命的,而精神一旦脫離了肉體,它就會由於意識到自己失去了這種統一的經驗而承受劇烈的痛苦,而且還得不自然地漠視這種痛苦。生活讓每個人面對個人的和周圍環境的問題,當然也包括我們希望逃避的各式各樣的精神痛苦。然而,精神與肉體、靈智與自然的割裂則在現代人心靈中造成了一種最根本的精神痛苦,它使得一切人很難療治其他心理傷痛。
確實有道理假定,一種文明的成員如聽任或鼓勵這種割裂,他將更容易受到精神失調的傷害,其特點是扭曲了思維與感覺的關系。這種觀點似乎有點匪夷所思,因為我們還不習慣從現代文明模式這一更廣闊的角度尋找心理問題的原因。流行病學專家現已經常從社會模式中尋找身體疾病的原因,因為社會模式對最易受害者施加特別的壓力。例如,在美國這一類國家,高血壓的廣泛流行幾乎完全歸因為現代文明模式——食物中的鈉鹽大多。儘管精確的因果關係解釋尚是一個謎,但流行病學學者斷定,現代文明中食物多加鹽的相當普遍的傾向是高血壓廣泛存在的原因。在現在殘存的前工業化的文化中,食品不經加工,鹽的消費很少,高血壓實際上無人知曉,老人的血壓與嬰兒相同被視為正常之事。在我們的社會,人們則認為血壓隨年齡一道增長是自然之事。
不過,解決高血壓問題比解決心理衝突問題容易得多。大多數人面對精神痛苦的方法和他們面對其他痛苦的方式一樣:不是正視痛苦的根源,而是在痛苦前退卻,馬上尋找逃避或有意忘卻的辦法。忘卻精神痛苦最有效的辦法之一是使自己幹些愉快的、緊張的或其他需要全神貫注的事情,讓自己分心。作為權宜之計,這種分心術不一定有害,但如果長期依賴這種方法,它就是危險的了。最終成為某種癮嗜。我們甚至可以認為,所有的癮嗜是否都源於逃避精神痛苦的強烈而持續的需要。癮嗜是一種逃避。
過去,我們常從毒品或烈酒的角度論及癮嗜。但有關癮嗜的新研究已深化了我們對問題的理解。現在我們知道,人們可以對多種行為方式上癮,例如不能自製地賭博,拼命地工作,或經常看電視。這些都是讓人逃避不欲面對之事的辦法。一個人只要有特別的畏懼——例如害怕人際親密、失敗、孤獨——這個人就很容易受癮嗜之害,因為精神痛苦而導致對逃避的強烈需求。
在現代世界中,精神與肉體、人與自然之間的割裂產生了一種新的癮嗜:我認為,我們的文明實際上對消耗地球上了癮。我們失去了對自然界另一部分的生動活潑的直接體驗,而這種癮嗜能使我們逃避這種損失引起的痛苦。人與世界的交流能提升人的精神,使人的知性中充溢生活本身的豐富性和即時性,但我們卻遠離了這種交流,而工業文明的喧囂又掩蓋了人類深刻的孤獨。
我們可以對自己內心的空虛裝做視而不見,但是,其後果卻可以從我們接觸事物表現出的不自然的反復無常看出來。我可以打從電力工程借用的一個比喻。一個大量用電的機器必須“接地”以穩定通過機器的電流並防止跑電。一個機器如不接地就會構成嚴重威脅。同樣,一個人的身體或精神若不“接地”,其思想感情也會對其接觸的一切構成威脅。我們一般認為,每個人身上流動的創造性偉力是好事,但是,這種力量如不恰當“接地”,就是不穩定的,危險的。這對嚴重癮嗜者更為正確。癮嗜者不再與生活的深層意義接觸,好像人因電流過強而甩不開600伏的電線,他們緊緊擁抱自己的癮嗜,哪怕生命力從其血脈中流失。
同樣,我們的文明也更加執著於其積習,每年消耗越來越多的煤、石油、樹木、土壤以及從地表掠取的上千種其他物質,不僅將其改造為人生息棲居所需的一切,而且變為我們並不需要的東西:大量的污染;花數十億美元廣告讓人相信其有用的產品;大量的過剩產品,既壓低價格又造成產品浪費;各種消遣之事。我們似乎日益沉溺于文化、社會、技術、媒體和生產消費儀典的形式中,但付出的代價是喪失了自己的精神生活。
精神損失的證據太多了。各種形態的精神疾病已經達到傳染病的水平,在兒童中尤為突出。在青少年中的三大死亡原因是與吸毒酗酒相關的事故、自殺和他殺。購物現被視為消遣。物質產品的積聚高過歷史上任何時期,但感到生活空虛的人數也前所未有。
工業文明的龐大娛樂機器仍以充實的許諾引誘著我們。當毒品注入人的血液,促成大腦中的化學變化,吸毒者便體驗到一時的“興奮”。與此不無相似的是,我們征服世界的新能力也能帶來突然的欣喜。但這種狂喜是與時而去的,它不是真正的充實感。吸毒者的比喻也可用於另一種情況。一個吸毒者在生活中逐漸需要更大的毒品劑量才能產生同等的興奮度,同樣,我們的文明似乎需要不斷增長的消費水平。然而,為什麼我們認為對大多數自然資源的人均消耗年年增長是自然正常之事呢?難道我們需要更高的消費以產生以前較少消費所產生的同等娛樂效果嗎?當我們討論通過科學技術和工業獲得新的可畏力量時,我們是否有時太醉心於人類征服地球的新力量首次應用時的興奮,卻較少關注得失的仔細平衡?
吸毒的本質是一種虛假許諾,它可能讓人體驗到真實生活的生動與直接,卻無需面對生活中的恐懼和痛苦。我們的工業文明向我們做出了同樣的許諾:對幸福和舒適的追求至高無上,拼命消費層出不窮的光亮新產品被視為這種追求的最佳成功之道。這種廉價滿足的華麗許諾是如此誘人,使我們甘心情願地忘卻了自身的真實感受,不再謀求生活的真正目的和意義。
然而,因為對真實性的渴求依然存在,這種許諾就永遠是虛假的。在健康而平衡的生活中,人與人造世界的對話儘管喧鬧異常,可以讓人暫離生活的深層節律,但它不能阻斷這些節律。在吸毒的病態中,這種對話就不僅僅是喧鬧的消遣,生活已失去平衡,吸毒者日益對其吸食物傾注心力。吸毒者一旦沉溺於與生活替代物的虛假交流,他們那貧乏可悲的人生節律便與自然和諧日益不相容,不合拍,不同調,而自然和諧才能帶來生命的樂章。當這種不合調更為強烈,衝突更加頻繁,不合諧的極點便開始表現為一次比一次更具破壞性的連續危機。
我們對不斷消耗更多地球資源的模式已經成癮,這部分造成了人與自然關係的不和諧,這種不和諧現已表現為一系列的危機。每次危機都標誌人類文明與自然界之間更具破壞性的衝突。過去,所有對環境的威脅都是地方性或區域性的,現在,有幾種威脅是戰略性的了。每秒鐘有1.5公頃雨林消失,現存物種的自然滅絕率突然加速了上千倍,南極上空出現臭氧洞,所有緯度上的臭氧層變薄,保證地球上可以生存的氣候平衡可能受到破壞——這一切都表明了人類文明與自然界之間日益猛烈的對撞。
許多人對這種對撞,對人類與自然間不健康關係的毒癮性質似乎茫然無知。對於缺乏瞭解者,教育是解決之方。但更讓人擔心的是有些人不承認上述模式是破壞性的。確實,許多政界、商界和知識界的領導者以或硬或軟的語調否認這類模式的存在。他們起著“授權者”的作用,清除不便之礙以保障毒癮式行為繼續進行。
這種否定心理的機制是複雜的,但癮嗜仍可作為其模式。一些人希望能繼續中毒上癮的生活,讓自己相信這種生活對自己和他人並無不良影響,於是他們就採取了這種視而不見的辦法。例如,你若對酗酒者說烈酒正在毀掉他的生活,他會激烈地駁斥你。一個酗酒的司機多次出事故,卻總把事故說成是孤立的,每一次事故都有互不關聯的原因。
因此,這種否定本質上是癮嗜者的一種內在需要,不願看到其癮嗜行為與其災難性後果之間的聯繫。這種否定的需要常常是極為強大的。如果癮嗜者承認自己有毛病,他們可能將不得不注意到自己拼命想回避的情感和思想。完全丟棄自己的癮嗜,就會使他們在面對自己圍捕的獵物時失去自護的主要盾牌。
有些理論家說,許多癮嗜者所想圍獵的物件是一種深層的無力感。癮嗜者常常表現出一種瘋魔般的需要,想完全控制滿足其欲望的某些事物。這種需要來自他們對真實世界的一種無助無力之感,並與之成反比關係。真實世界的自在自發性和對他們控制行為的反抗使這些人覺得受不了。
這一心理劇發生在自覺意識的邊緣帶,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人們正是在這一邊緣帶上對現實的不停入侵進行防衛。與此同時,為了確保現實不突破心理防線,癮嗜者常常不可能誠實,以致朋友們很難相信他並不知道自己對己對人都做了些什麼。不過,癮嗜者的不誠實從某一意義上倒也容易解釋:這些人已執迷于滿足其渴望的要求,讓其他一切價值都服從於這種需求。因為對其行為的真實理解會導致禁止這些行為,他便堅持說他沒什麼問題。我們對人類對地球的破壞性影響麻木不仁,這大體出於同樣的原因。因之我們有一種類似的非常強烈的否定欲望。這種否定可以令人恐懼和荒誕的形式出現。例如,1991年南加利福尼亞州出現了持續5年的旱災,一些人家竟把他們枯死的草坪用漆塗成了綠色。這就像有的人給死屍化妝,使感情上接受不了死亡的人看到死屍恍如在世,J.康拉德在《黑暗深處》中寫道:“要是你深入洞察地球,征服地球可不是件美好的事。”但是,我們已沉迷於這種征服,因而我們否認死亡令人不快,否認死亡就是毀滅。我們用心良苦地自我辯解,卻對我們行為的後果視而不見。對警告我們要改弦更張的信使,我們視如仇敵,懷疑他們妄圖篡權,指責他們包藏禍心——馬克思主義,中央集權,或是無政府主義。(“殺死信使”實際上正是一種否定。)我們看不出自己造成的各種自然危機之間的聯繫,視其為互不相關的事件。例如,這些枯死的草坪與1991年後期造成成千上萬人無家可歸的熊熊大火有關係嗎?越來越頻繁發生的災害越來越如幽默作家W.布朗所說的“歷經上天啟示的自然之旅”。
儘管如此,我們仍確信有辦法劫後餘生。不過,否定的屏障並非永遠無法穿透。在癮嗜的晚期,當這種行為模式的毀滅特性暴露無疑,癮嗜者會愈覺難以抵禦撇棄惡習的欲望時,他們開始乾脆聽天由命。這時,惡癖已病入膏肓,似乎無藥可治了。同樣一些人日益感到無法否定我們與地球的關係具有的毀滅特性,但他們的反應並非挺而抗爭,而是聽之任之。我們以為一切都為時已晚,全無出路。
這種做法只能宣告末日來臨,其實亡羊補牢猶未晚也。讓癮君子康復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讓他們正視想要逃避的現實苦痛。不是幹旁的事以分散內心的警覺,而是必須學會面對苦痛——感覺它,思考它,消化它,佔有它。只有在這時他才能開始正視它,而非逃之夭夭。
所以,我們只有停止否認現時行為模式具有的毀滅特性,才有可能治癒我們的地球病。我們想要控制自然界的那種仿佛無法抑制的欲望可能源於面對“張牙舞爪的自然”而產生的深沉古老的恐懼,讓我們束手無措的感覺。但這種衝動已把我們推到了災難的邊緣,因為隨心所欲地控制自然斬斷了我們與它的紐帶。我們還必須認識到,一種新的恐懼正在加深我們的癮嗜:越是由於征服自然而興高采烈,我們對其後果也愈發恐懼,而這種恐懼只能使我們的自我毀滅愈發不可收拾。
不過,我所稱的癮嗜行為模式只是問題的一部分,因為它不足以解釋我們對地球掠奪行為的複雜性和劇烈程度。它也無法解釋為什麼很多有頭腦和心懷關切的人會不知不覺地協同他人對全球環境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壞。涉及到人類文明的所作所為及其原因的時候,他們怎麼會繼續生活在一系列自欺欺人的假設之中。顯然,問題並不僅限於我們每個人作為個人與地球相連的方式。我們作為整體在決定自身與地球關係的方式上有什麼地方已鑄成大錯。
比喻會有助於理解,有幾個比喻曾幫助我瞭解到我們與地球的關係發生了什麼問題。其中一個最能啟發人的比喻出自關於某些患病家庭的較新理論。它是研究癮嗜理論、家庭療法和系統分析的心理學家與社會學家建立的一個綜合理論,力圖解釋現被稱之為機能失調家庭的運行機制。機能失調家庭的概念是R.D.萊恩、V.薩特、G.貝特森、M.埃裏克森、M.鮑恩、N.阿克曼和A.米勒等理論家最先闡發的,近來更被諸如J.布萊德肖等作家所完善並普及。他們想解決的共同問題是:為什麼由本意良好、頗似正常的個人組成的家庭會彼此反目成仇,將家庭成員和整個家庭推入危機。
機能失調理論認為,關於如何教育後代和關於人的立身之本的不成文法規是代代相傳下來的。這些法規的現代文本是由導致了科學技術革命的同一哲學世界觀造就的。它把人定義成與物質世界相分離的靈智。這一定義隨之引出了應當壓制感覺和情感,使其服從於純思想的假定。
結果,這種科學觀導致了對上帝的不同理解。一旦很多自然奧秘能夠依據科學而不是神意得到解釋這一點成為不爭的事實,我們似乎就有理由假定,造物主以可見和可預見的模式啟動了自然界之後便撒手不管了,只是高居九大之外俯視眾生。或許,我們對家庭的觀念也改變了。家庭被視為一個小太陽系,父親是一家之長。由他發號施令,其他家庭成員則在圍繞他的軌道上運行。這種改變對孩童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科學時代之前,孩童們以家長和自然界無處不見的上帝為自己生身立命之本。以這兩個參照系為堅強的支柱,他們就很難在生活中迷失方向。但是,隨著上帝從自然界中隱身而去,家長制(差不多總是父親)實際上成了上帝的代言人,在執行家庭法規時享有上帝之權威。為人父者最終要登基成帝,而他們的子女在這個無所不能無所不治的父親統治的家庭體制中為扮演何種角色而不知所措。
家長以上帝之權威執法。像布萊德肖及其他人指出的那樣,這樣形成的法規不容他人置疑。機能失調家庭賴以維持遵紀守法和心理順從的方法之一是進行身心分離的教育,壓制會觸犯法規的感覺和情感。同樣,我們的文明維持法規的方法之一也是進行天人分離的教育,壓制會使我們感到與地球斷絕了聯繫的感情。
我們家庭與文明的規則維持思想與感覺的分離,要我們無條件接受眾所承認的無言之謊言。這兩種規則都鼓勵人們對情感漠然處之,即使對這種觀念和規範有了疑問,想加以改變也會感到束手無策。結果,這種法規常常促成了心理衝突或角色表演。既荒唐又至高無上的規則會造成癮嗜,虐待兒童和壓迫行為等不正常現象層出不窮。這就是機能失調家庭的範例。
機能失調家庭中的人常常會表露出某種嚴重的心理失調。仔細分析後可以看出它是整個家庭機能失調模式的一種外在表現。治療這種病人時,醫生注重的不是個人病理,而是家庭關係的影響和規範他與家庭關係的不成文規則與觀念。
例如,我們早就知道虐待兒童者大都在童年時也受過虐待。在分析這種現象時,醫生發現了一種自我生成的原型:受害的兒童會記住肉體上的強烈痛感,但儘量忘卻精神的痛苦。為了弄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他不得不徒勞無益地重演一個力大無窮的長者欺負一個弱小無力孩子的那一幕,只不過這一次他扮演的是欺負人的角色。
另一個複雜些的例子見於米勒研究機能失調的創新之作《天才兒童的衝突》。一些家庭的孩子被剝奪了正常發育所必需的無私之愛,感到內心失去了什麼東西。因而,這些孩子變得很自卑,開始不斷如饑似渴地向他人尋求認可。“相互依賴”這一新辭彙描述的是依賴他人、互相求取認可和對自己的好感。這種欲望總得不到滿足,一直延續到成年,常常造成癮嗜行為和對人際關係的不正常的態度。用一句流行歌曲的話說,就是“四處求愛心,處處都碰壁”。不幸但幾乎無例外的是,當他們自己有了孩子,他們會把孩子表現出來的情感饑渴看作滿足自己渴求認可的手段,以獲取愛而非給與愛的方式來滿足自己的情感。他們忘記了給與孩子無條件的愛,而孩子恰恰需要這種愛才能在感情上充分發育。這樣,孩子也產生了內心缺少什麼東西的感覺,並在他人的臉上和情感中尋求這種東西,卻又常常得不到滿足。就這樣,這一迴圈往返不斷。
家庭機能失調的理論通常不需確認家庭哪一個成員是壞人,或故意傷人。每一代家庭成員經歷的痛苦和悲劇的真正根源常常來自家庭規則的習得模式。機能失調理論作為一種治療方法為我們提供了巨大的希望,因為它不是從個人而是從個人之間的關係、不是從命中註定的共同人性而是從世代相傳的共同思維方式來判定問題的癥結所在。
這是事情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是嬰幼兒時期在體內形成的失調有很多極難去除。當然,是人類進化造成了漫長的幼兒期。在此期間我們基本上要完全仰靠父母。A.蒙塔古在幾十年前第一次指出,進化使人腦越來越大,而源於靈長目的人類無法使其產道適應頭顱已經過大的嬰兒。自然選擇之法是讓嬰兒早一點生下來,把初生嬰兒依賴父母撫養的階段延長數年。在這段時間裏,孩子的身心發展差不多等於是在孕期環境中進行的。但是,這段社會和心理發展的漫長時期使兒童極易受好的或壞的影響,而在一個機能失調的家庭中,他們會吸收、消化父母傳輸的失調性規則和對生活的乖戾假定。而且,由於父母所灌輸的多為他們自己幼年所得的教訓,所以這些規則會世代相傳。
每一種文化都像一個擴而廣之的大家庭,而最能決定一種文化的獨特之處或許當屬它對於生活的規則和假定。在西方現代文化中,我們從小被灌輸的生活假定深受笛卡爾式觀念的影響,人類應與地球分離,就像精神應與肉體分離一樣;自然應服從人類,就像情感應服從理智一樣。這些法規在不同程度上傳給了我們每一個人,造就了我們對人為何物的看法。
機能失調家庭理論對我們思考環境問題有直接關係。這一理論還有助於弄清我們是如何在人與環境的關係上創造出如此深重的危機,為什麼這一危機並非我們與生俱來的人性之惡或病理遺傳因素所造成,以及我們如何能夠醫治這種關係。不過,這一比喻同時也告訴我們,現時的環境危機已如此之嚴重,以致我認為我們的文明本身必須被視為患了某種機能失調症。
與機能失調家庭中的規則一樣,統治我們與環境關係的不成文規則是從約375年前科學革命中的笛卡爾、培根和其他一些先驅者那裏代代相傳下來的。我們吸收了這些規則並以此為處世之本已有數個世紀,而從未嚴肅地反省過它們。同一個機能失調家庭一樣,機能失調文明的規則中有一條就是不能對規則質疑。
機能失調家庭的規則不受懷疑,這有一項重要的心理原因。嬰兒或正發育成長的兒童完會依賴父母的照顧,他們想也不可能去想家長會有問題,即使他們感覺到規則不對或沒有道理也一樣。由於子女不能把一家之主的家長判為機能失調的根源,他們只好認定問題出在自己身上。這一時刻正是心理創傷形成的關鍵時刻。它是一種自我感染的創傷,使孩子失去了基本的自信。這一創傷所造成的痛苦常常會延及一生,其造成的空虛感和孤獨感會積蓄起大量心理能量,而在關鍵的心理成型期釋放出來。不幸的是,他們在成型期間所追求的是永遠得不到的:無條件的愛與認可。
與兒童不能反對家長一樣,我們文明中的每個新一代現在都感到完全依賴于這一文明。超級市場貨架上的食品,家中水管流出的自來水,房屋,營養,服裝與設計,我們的娛樂,甚至我們的身份——所有這些都由我們的文明提供,因而我們連想都不敢想拋開這些便利。
把我們的比喻進一步延伸:正如兒童在家庭關係上把自己當作家庭機能失調的原因一樣,我們也把自己的文明未能培養集體精神和共同生活目標的責任歸罪於自身。很多人覺得生活無意義,有一種空虛和孤獨感,他們因而變得自疚自責。
頗具有反諷意味,正是我們與物質世界的分離是這種痛苦的主要原因,而且正是由於我們的教育讓我們與自然分離才使我們覺得必須完全依賴我們的文明。在我們看來,文明取代了自然滿足我們全部所需的功能。正如機能失調家庭的兒童感覺痛苦是由于家長使他們相信精神中缺少某些重要的東西一樣。我們確實感覺到痛苦的失落,也正是源於灌輸給我們的東西。人作為一個物種和自然有與生俱來的聯繫,但灌輸給我們的觀念卻把這一紐帶描繪成某種不自然的東西,某個通往文明世界旅途中的驛站。結果,我們把與自然界失去聯繫造成的失落感歸罪於自身的痛苦,把耗費地球資源當作忘卻痛苦的一種方法,永不滿足地尋求人工替代品來取代不再與世界進行溝通的感受。
機能失調家庭中自感負罪的兒童常構築一個虛假的自我來和他人相處。他們小心謹慎地偽裝自己,以假亂真,以不斷修正自己給他人的印象來使這個虛假自我精巧逼真。同樣,我們在自己的文明中建造了一個虛假的世界:塑膠花和尼龍草皮,空調和霓虹燈,打不開的窗戶和永不止息的背景音樂,不知陰晴的白晝和永是白晝的夜晚,隨身聽與隨身看,閉門娛樂,和微波爐配套的冷凍食品,用咖啡因、酒精和藥物刺激才能猛醒的昏沉無力的心臟,還有大腦的幻象。
我們瘋狂地破壞自然,沉湎於以虛假的代用品來充當對真實生活的直接體驗。我們這樣做是在按祖先傳給我們的劇本演出。然而,正像機能失調家庭中的不成文規則能夠無言地製造和維護規則自身的權威一樣——儘管這會給家庭帶來接連不斷的危機,機能失調症的文明中有很多不成文規則同樣要我們無言地接受破壞自然的行為模式。
我們的文明機能失調這一概念並非只是一個理論建構。在令人恐懼的本世紀,我們就已目睹了文明機能失調的一些特別邪惡的例證:專制社會如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史達林和其後任統治的共產主義蘇聯,以及名聲不及於此但性質一樣的其他例證。事實上,只是在不久以前國際社會還組織了一支聯合部隊,挫敗了伊拉克的薩達姆·候賽因領導的復興社會黨專制。
以上這些機能失調社會都缺少自我認可。這種認可只能來自享有自由表達權的人民。這些社會都表現出將自己和其政治哲學強加於毗鄰社會的無法滿足的欲望,都以武力佔領它國進行擴張為目的。此外,它們都在自己的社會中用共同假定編織了一張無所不在的網。這張網大多數人都能看透,但無人敢於指出這一點。這些社會在宏觀上顯示了機能失調家庭的病理。機能失調家庭中正在成長的兒童從家長的臉上尋找對自己是否健全和正常的認可。當他找不到這種贊許的表情時,就開始感到自己有問題了。由於懷疑自己的價值和真實性,他開始控制自己的內心體驗,壓抑本能,偽裝情感,將創造性轉為機械性,用不能令人信服的想像的自我來轉移自我失落的感覺。同樣,當專制社會的統治者壯膽從人民的臉上看出他們對自己的真實感受時,很少會覺得世界太平無事。相反,因為人民並不——也不能——自由地表達他們的認可,所以統治者開始害怕有什麼問題。人民以無精打采的目光對視統治者,空洞抑鬱的眼神所傳達的不自在和恐懼是所有國家受壓迫者所共有的神情。專制社會的統治者從其公民的表情上找不到認可,覺得別無它途,只有在無法滿足的野心驅使下盡力擴張,靠強加於人來找尋能證明自身價值的證據。
專制擴張一般以佔領一個弱小而相對來說無防禦能力的毗鄰社會開始。其他社會期待著這種侵略能夠滿足侵略者而默不作聲。其中一些社會是因為害怕自己成為下一個目標,而另一些則確信自己不會是下一個。但是,如果這一專制社會已經嚴重機能失調,它滿足的時間就不會太久,會想繼續擴張。是的,這一可怕的模式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專制擴張在本世紀直接導致了一億以上的生靈塗炭。
當然,現代專制主義現象極為錯綜複雜,每一實例都有其獨特的政治、經濟和歷史原因。但是,不管具體的原因是什麼,它總是具有對內部失調的恐懼和向外部尋求認可的心理特徵。現代專制社會觸目驚心的病態擴張就是這種機能失調模式造成的,而只要它們拒絕正視不斷腐蝕其內心的民族性的虛偽、恐懼和施暴傾向,它們就無法恢復健全的心理。
作為整體的人類文明以史無前例的方式破壞自然這一現象也同樣錯綜複雜,其中很多破壞行為都與具體的地理和歷史條件有關。但從心理角度講,我們對地球上剩餘的野生世界進行侵略性的迅猛擴張,正表明了我們向外部文明掠奪那些已經無法在內部找到的資源。我們無止境地搜刮,直到土地深處,掘光能找到的所有煤礦、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我們隨挖隨燒,讓大氣層充滿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這是我們機能失調的文明在向自然界中無力抵抗部分的任意擴張。工業文明毀壞了大部分雨林和原始森林,這就是我們的積極擴張已超越合理邊界的尤為令人恐懼的例證,表現了一種得不到滿足的欲望:向外部尋求解決內部機能失調問題的方法。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代專制擴張的第一個受害國埃塞俄比亞也是造成我們破壞自然的機能失調症的一個早期受害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義大利法西斯被趕了出去。那時,埃塞俄比亞40%的土地被樹林所覆蓋和保護。不到半世紀之後,由於歷經幾十年世界最高的人口增長率,無情地消耗薪柴和牧草,出口木材以償付外債利息,覆蓋埃塞俄比亞的樹木己不及1%。先是表土大量流失,隨之而來的是旱災——不復離去的旱災。400萬饑餓而死的人其實是我們機能失調的文明擴張行為的犧牲品。
在研究如何制止我們的破壞性擴張行為時,幾乎每個人都會對我們似乎按捺不住地想要君臨天下的無情欲望感到震驚。未滿足的需求永遠是侵略的原動力,而這些需求永遠不會真正得到滿足。遭到侵略的地區成為不毛之地,其自然生產力被耗竭,其資源被掠奪殆盡,而所有這些破壞只是更加增大了我們的胃口。
機能失調家庭中最弱小無助的成員是撫養人的虐待對象。與此相似,我們一步步蹂躪自然界中最易受破壞而最無保護的地區:濕地、熱帶雨林和海洋。我們還虐待人類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員,特別是那些不能為自己說話的人。我們容忍人們從土著居民那裏竊取土地,剝削最貧困的地區,更甚的則是侵犯我們子孫後代的權利。我們全然不顧後果,一寸寸地搜刮地球,使我們的子孫後代的生活水平甚至多少接近我們一些都不再可能。
從哲學角度上講,未來歸根結底只是一個脆弱發育中的現在,所以不可持續的發展應被稱為“虐待未來”。像家長侵犯脆弱兒童的個人疆界一樣,我們侵犯的是人類生命延續鏈上我們這一代正當許可權的時間疆界。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每一代的男男女女畢竟只能居住在同一個地球上,所以我們也有責任保證我們這一代人所稱的未來能夠安全地成長為另一代人的現在。實際上,我們現在正以腐敗的方式將自己機能失調的規劃和不合拍的節奏強加于未來世代,而這些持續增加的重負將使他們不堪承擔。
與兒童性虐待的受害者打交道的員警、醫生和心理學家常常奇怪一個成年人——特別是家長——競會犯下如此的罪行。他怎麼會對自己的行為造成的哀嚎、悲泣和痛苦不聞不見,麻木不仁呢?我們現在知道,這些成年人在孩提時代適從了撫養他們的家庭機能失調的模式,導致了精神的麻木。這種漠然感可以麻痹他們自己的良知和判斷,促使他們情不自禁地重演別人對他們所犯的罪行。
正如機能失調家庭的成員麻痹自己的情感以逃避不然就會感受到的痛苦一樣,我們的機能失調文明也形成了一種漠然感,以使我們感覺不到自身從世界中分離的痛苦。機能失調家庭和機能失調文明都憎惡真誠完整的生活體驗。兩者都把個人封閉在一個抽象寡情的思維織成的密網之中。這種思維永遠在注視他人,假定他們在感受什麼,注意他們可能說什麼或做什麼,提供自己渴望已極的健全感和認可。
但出路是有的。機能失調模式並非註定要循環往復,以至永遠。關鍵是要勇敢地正視現實。癮嗜者能夠做到正視他的癖好,機能失調家庭能夠正視控制他們生活的不成文規則。同樣,我們的文明也能夠而且必須洗面革心,正視驅使我們毀滅地球的不成文規則。正如米勒和其他專家指出的那樣,哀悼最初的失落並有意識地全身心去體會它所造成的痛苦能夠使創口癒合,使患者解脫羈絆。同樣,如果全球環境危機的根源在於人類文明與自然之間的關係陷入了機能失調的模式,那麼,我們若能正視並充分理解這一模式,認識到它對環境和我們自身的毀滅性影響,我們就走出了第一步,開始哀掉我們的所失,逐步治癒我們對地球和我們的文明造成的損傷,開啟人類作為地球管理員的新篇章。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