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頻臨失衡的地球—生態與人類精神】 美國─阿爾·戈爾著(2)
《第一部分-失衡的危險》 第一章沙漠駐舟
我站在一條漁船的甲板上,鋼板在太陽下熱得發燙。碰到好日子,這條漁船一天可以捕50噸魚。可這不是個好日子。這條漁船的駐錨之所,曾是中亞所有地區產量最高的漁場。現在我向船頭望去,豐產的希望卻十分渺茫。我應該看見藍綠色的溫柔波浪拍打船舷,實際上極目所見卻只有滾熱的幹沙。這支船隊的別的漁船,東一條西一條,也都陷在幹沙之中,沙丘一直伸展到地平線盡頭。
奇怪的是,這讓我想起我前一個星期在美國看電視的時候看到的一個煎雞蛋。煎雞蛋應該在平底鍋裏吱吱起泡,可這個煎雞蛋卻擺在費尼克斯城市區的人行道中央。我想,這兩件事是這樣聯想到一起的:這個雞蛋,就像這條漁船一樣,本身並無不妥之處,而它的棲身之地卻經歷了想不到的改變,讓人覺得它擺錯了地方。那個電視畫面上了新聞,是因為亞裏桑那州那天也實在不是個好日子,連續兩天氣溫打破記錄,達到華氏122度。
一個相比。如今它正在消失,這是因為人們要在沙漠裏種棉花,設計得很糟的灌溉計畫用掉了供養它的水。新的海岸線從沙原退縮,離開眼前這支永久停駐的船隊差不多有40公里。然而,附近的小城慕那克仍然在製作魚罐頭,魚不是從鹹海來的,而是通過西伯利亞鐵路從一千多英里以外的太平洋運來的。
我1990年8月到鹹海來,是來親眼見證這場破壞。這場破壞的規模近乎聖經故事中的災難。但我在這次旅行途中還看到了其它令我驚憂的現象。我從慕那克回到莫斯科那天,我的朋友A.雅布羅科夫剛好從白海回來。他也許是蘇聯環境主義者的領頭人,剛剛緊急旅行到白海去調查一樁從未發生過的事情:幾百萬海星神秘地死掉,被海水沖上岸,一堆一堆,膝蓋那麼深,蔓延好多英裏。他穿著膠皮褲,在海星的殘骸裏走來趟去,試圖解釋突然死亡的原因。那天夜裏,他講述了那是一幅怎樣的情景。
後來的調查表明,白海災難的罪魁禍首多半是軍用放射性廢物。可是,世界各地的灘岸邊上,還沖上來過很多其他神秘的批量死亡。罪魁禍首又是什麼呢?沖刷上裏維艾拉(法國和義大利接壤一帶的著名海濱勝地。——譯注)海岸的死海豚不斷增加。法國科學家最近得出結論說,死因在於環境壓力不斷累積,到了一定的時候,使這種動物變得太弱,無力抵抗一種病毒。德克薩斯州的海灣沿線,海豚的死亡數字也突然增長,1988年夏天,12000頭海豹神秘死亡,屍體被沖上北海海岸。這些事件大概出於同樣的原因。一年以後,威廉王子灣死掉的海狸和海鳥沾滿了石油。這一事件對科學來講固然並不神秘,但它絲毫不減對人類文明的起訴。
一幅令人困惱的圖像剛剛消褪,另一幅又出現在面前,向我們提出新的質問。孩子們在朝陽下衝浪,他們不僅要當心偶或出現的海蜇,而且要當心浪頭有時會卷來用於皮下注射的針頭。這意味著什麼?針頭、死掉的海豚、沾滿石油的海鳥,這一切難道不是在提醒我們,我們曾經熟識的世界之岸正在加速瓦解,我們已經站在新的海岸線上,面對超出我們想像力的巨大危險?
“我們從自然中來,現在卻把脊背轉向自然,這時候,我們腳踝上感到有奇怪的潮水在上漲,卷成的漩渦正把我們拉到腳下的流沙裏去。每一次這樣的潮水退去,留下的總是一些大船的殘骸,遠離海洋,七零八落散亂在我們時代的沙原上。每一幅這種發人深省的畫面都是一次新的警告:我們若不懸崖勒馬,災難已經指日可待。
為了尋找造成環境危機的潛伏原因,我跑遍世界各地,考察研究過很多這種描述毀滅的畫面。1988年晚秋,我來到南極橫斷山脈。在這高山上,午夜的太陽從天空中的一個小洞裏閃耀著。我站在不可置信的寒冷之中,聽一位科學家講他正在挖掘一個時間之洞。他把風雪大衣的大領子撥到後面,他幾乎被光線烤焦的臉上佈滿深深的皺褶。他指著一個冰芯,讓我看它的年輪。這個樣品是從我們腳下的冰川挖掘出來的。他的手指沿著時間指回20年以前的那一層冰,告訴我說:“這就是美國國會通過《清潔大氣法》的那一層。”距離華盛頓整整兩塊大陸,在世界的底部,我們可以檢測到,哪怕我國減少一點點廢氣,地球上最遙遠最偏僻的地方受到的污染也會改變。
我們的雪橇飛機停在堅冰築成的跑道上,為了防止飛機的金屬部分凍結,發動機始終沒熄火。跑道的上風頭,離開南極點不到100碼,科學家每天好幾次對空氣進行跟蹤觀察,繪出大氣的無情變化的曲線。迄今為止,最突出的大氣變化隨著上世紀初的工業革命發生而在此後不斷加速。工業意味著燒煤,後來則是燒石油,越燒越多,增加了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含量,這種物質把大氣裏的熱量留住,慢慢使全球變暖。訪問期間,我看到一位元科學家記錄下來那一天的測量結果,在圖表上陡峭的曲線盡頭上再往上加了一點兒。他告訴我,即使在這地球的極頂,也很容易看到大氣的劇烈變化仍在加速。
兩年半以後我到了地球的另一極。在北冰洋12英尺厚的巨大流動冰塊上,我們一行支起了小帳篷,在午夜的太陽底下睡了一覺。吃飽早飯,我們坐著雪橇又向北走了幾英里,去和在冰塊底下巡遊的核潛艇會合。這裏的冰層比較薄,只有三英尺半。核潛艇破冰而出,載上我們這些新乘客,重新潛入冰層下面的水裏。在船上,我和一些科學家作了一次談話。這些科學家到這裏來,希望更精確地測量極地冰帽的厚度。很多人認為由於全球變暖,冰帽正在變薄。美國海軍利用水下聲納技術獲得了一些資料,這些資料可能有助於科學家瞭解北極冰帽的實際情況。但這是些絕密資料。不過我事先為這些科學家和海軍談妥了一項解密的協議。現在呢,我想親自看一看北極。航行了8個小時以後,潛水艇再次破冰而出。我面對一片雪景,風掃過白皚皚的雪原,雪原閃閃發光。天地之間是隆起的冰丘,就像岩席擠撞後拱起的小小山脈。這種景象有一種異樣的美。然而就在這裏,二氧化碳的含量也在急劇升高,而氣溫最終也將隨之升高。實際上,人們預測,全球變暖將使極地的氣溫比地球上其他地方的氣溫升高得更快。極地的大氣變熱,冰就會變薄。由於極地的冰帽在調節地球氣候方面作用極大,冰帽變薄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考慮這種後果並非想入非非。我從北極回來以後6個月,一個科學研究小組報告說北極的冰層分佈發生了可觀的變化。另一個小組的報告則認定北極的冰帽在最近僅僅10年裏就變薄了2%。這個報告雖有爭議,但頗可由後來的各種資料加以支援。而且幾年後科學家進一步證實,在北極圈以北的大量陸地上,春季的融雪每年都發生得更早;凍土帶的深層土壤的溫度在穩步上升。
說起來,環境破壞得最讓人不安的圖景恰好在北極和南極中間。在巴西的赤道地帶,持續不斷的黑煙像烏雲一樣在天空滾過,無邊無際的亞馬遜雨林正受到威脅。人們燒掉成公頃的雨林,以便開闢快速牧場,為快速食品工業提供牛肉。1989年,生物學家T.羅維厥依曾帶我到那裏訪問。人們告訴我,在旱季放火的日期越提越早,如今每年砍掉的雨林比整個田納西州所有的都要多。羅維厥依說,亞馬遜雨林裏每一平方英里裏的鳥類種屬比整個北美的鳥類種屬加起來還要多。這意味著我們正在滅絕成千上萬種歌聲,而我們今後再也聽不到這些歌聲了。
但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亞馬遜是個遙遠的地方,我們幾乎注意不到這些鳥類以及其他珍貴物種的消失。然而,我們漫不經心,只能自食苦果。這些物種就像諺語所說的金絲雀,無言中向礦工報警,只不過這一次的警報是:比較起過去6500萬年之中的任何時期,地球上的動植物物種消失的速率現在至少都要快上1000倍。
那些大動物、漂亮的動物,一旦受到威脅或瀕臨滅絕,有時倒也會引起注意。我曾經訪問過赤道上的另一個地方——東非。我在那裏看到一隻死掉的大象,偷獵者用鋸子鋸斷象牙,而為了獲得這值錢的象牙,他割開了大象的頭,留下一幅陰森可怖的畫面。顯然,我們對象牙的純粹審美方面的看法必須有所改變,因為生長象牙的大象正受到威脅。在我眼裏,那晶潤的潔白現在看上去已經變了,它仿佛是一份證據,表明曾有變態的精怪來訪,從此,象牙仿佛變成了一個美麗而冰涼的幻影,帶來驚喜,也帶來死亡。
在海洋下面,我們會碰到另一個幻影。我曾在加勒比海潛水,看到並觸到一株死珊瑚的白骨。在珊瑚樹的表層上,生活著一種微小的有機物,渾名“租客”,這些微生物把珊瑚樹打扮得色彩繽紛。它們不習慣變暖的海水,難以存活。失去了表層的微生物以後,珊瑚變得透明了,露出了自己石灰質的骨架。於是,地球各地的珊瑚樹都忽然開始像經過了一道漂白。過去,這種現象幾乎從來是偶然的暫時的,然而,多次發生以後,珊瑚樹就無法復原了。最近幾年以來,科學家發現地球上的廣大地區突然出現了大規模的漂白現象,而越未越多的珊瑚樹從此不再複生。它們雖然已經死掉,卻更加明亮耀目,附身於此的,與附身在象牙那淒迷光彩之中的,也許是同一個精怪。
然而,我們無須遍遊世界就能目睹人類對地球的戕害。隨便走到哪里差不多都看得到一些景象,提示出環境所受的壓力。每當參院開會,我和家人就住在弗基尼亞州的阿靈頓。有一次我開車出門,一隻大山雞晃晃悠悠走過街道。我緊踩刹車。這只山雞撲撲飛過停在路旁的汽車,越過人行道,進了鄰家的後院。它消失了,但這幅自然似乎錯了位的景象卻久久揮之不去。山雞怎麼會跑到我們的街區來散步?要知道,這裏離開國會山僅數英里之遙。也許這片街區的環境,說來說去對野生動物並非那麼不相容?要麼,會不會有人拿它當作寵物來飼養,就像鼓肚的越南豬近來竟成為流行的寵物?我一直迷惑不解,直到幾個星期以後,我忽然想起來,三英里開外的河邊上,原有幾百英畝森林,這是我們整個地區保存下來的最後一片森林,而開發商正在用推土機把它們削平。樹木倒下,好騰出地方來澆水泥,蓋樓房,建停車場,鋪街道。同時,曾經生活在樹林裏的野物只好逃亡。鹿多數被汽車撞翻,另一些生物逃脫得稍遠一點兒,比如這只漂亮的大山雞,竟一直逃到了鄰家的後院。
在我明白這一點之前,我曾閃過這樣的念頭:美國中產階級的居住區也許容得下野生動物存身,既然鴿子、松鼠、黃鼠狼、負鼠一一學會了在城市近郊安身,山雞之類好生為之,說不定也有個機會。我想到這裏,模模糊糊感到一點安慰。這一點實有諷刺意味。反過來,現在我帶著孩子到動物園去看大象或犀牛,就會想到那只山雞。它們像那只山雞一樣,既讓人驚喜也讓人悲哀。它們讓我想到,我們正在創造一個對野生動物懷有敵意的世界,這個世界喜愛水泥結構更甚于喜愛自然景色。我們在人工鋪設的路面上和這些動物相遇,而它們正沿著這條道路走向滅絕。
在北半球的高緯度地帶,有些夜晚,天空自己也會呈現另一種幽靈,提示正在發展的生態失衡。如果日落後天空晴朗,如果大氣污染還不曾完全遮蔽你所在地區的天空,你有時可以看到一種奇怪的雲。暮色剛剛升起的時候,高天深處有時會出現這種“夜光雲”,在我們頭頂熠熠閃爍透明的白色。這種雲看上去很不自然。是不自然——夜光雲越來越常見,是因為大氣裏的甲烷大量增加。(甲烷也叫沼氣。垃圾場、煤礦、稻田都釋放沼氣。新砍伐的樹林中成億的白蟻,燃燒化石燃料,以及人類很多其他活動,也都產生沼氣。)過去,人們有時也能看到夜光雲。現在不斷增長的過剩沼氣把水蒸氣帶到高層大氣,在比過去高得多的大氣層凝結起來,形成雲氣,在夜色已經籠罩大地的時候,這種夜光雲還在高空久久反射太陽的光線。
我們該怎麼感受夜空中的這些幽靈?單純的驚奇?像在動物園裏那樣的混合感覺?也許我們應該為我們人類自己的力量瞠目結舌。為了掠取象牙,人把那麼多大象的頭扯開,乃至於這個物種會瀕臨滅絕。用同一種力量,人把物質從它在大地上的位置扯開,數量如此之大,乃至於擾動了日夜的平衡。我們使全球變暖又加了一層威脅,因為在造成溫室效應的各種氣體中,甲烷是增長得最快的一種,現在總量位列第三,僅次於二氧化碳和水蒸氣,已經改變了高層大氣的化學結構。不過,即使我們不談這種威脅也罷,但我們把這種雲氣送上天空,讓它在入夜時幽靈般地熠熠閃耀,這就不使我們自己吃驚嗎?也許我們的眼睛已經完全適應了人類文明的強烈光線,再也看不出這是些什麼樣的天光雲影了——這是大自然的明示:人類文明正和我們的地球猛烈衝突。
雖然我們有時還很難看清對環境的戕害究竟意味著什麼,但到現在為止,我們誰都會有過某種親身經驗,提示出環境受到的破壞。也許是太多的夏日氣溫超過了華氏100度,也許是太陽曬焦我們皮膚的速度越來越快,也許是人們不得不持續爭論應當怎樣處理堆積成山的垃圾。然而,我們的反應很讓我迷惑。為什麼我們到現在還沒有全力以赴來拯救我們的環境呢?我們也可以換個問法。為什麼同是令人吃驚的圖景,有些會立刻激起行動,或至少讓我們關注怎樣有效地回應,而另一些卻並非如此,反倒讓我們癱瘓,或尋求一些比較好過的辦法避開問題?
在某種意義上,我在南極和北極這兩極的旅行使得我往往從相反相成的角度來考慮這些問題。我在潛水艇裏幾次有機會從潛望鏡看到北極冰山透明的底部,那景象頗讓人有幾分幽閉恐怖。有一次我忽然想起幾年前曾有三條鯨魚被困在波弗特海的冰山底下。四個大陸的電視臺網路趕到那裏,實況錄播鯨魚為獲得空氣而進行的痛苦搏鬥。這些鏡頭使得全世界都激動起來,於是科學家們和救援者們很快蜂擁現場。人們實施了幾個精心設計的方案,但是都失敗了。這時,蘇聯派出了一艘巨型破冰船,破冰而來,救出了兩條還沒有斷氣的鯨魚。當時,我和成百萬的人們一道慶幸這兩條鯨魚得救。這時,我在潛水艇裏,另一個念頭卻浮了上來。很多科學家認為,人類每一天都使得100種物種滅絕。如果真是這樣,那在我們救援這幾條鯨魚的這些日子裏,就有2000種動植物消失了——永遠消失了,而誰都沒有注意到。
與此相似,德克薩斯的小姑娘潔西嘉·麥克盧爾掉到一口井裏,成隊的男人女人前來營救,數以百計的電視鏡頭和記者把她的痛苦遭遇和營救者的英勇事蹟送到數億人的家庭和心靈。我們在這件事上的反應似乎也有點片面。就在潔西嘉受苦的那三天裏,有10萬和她年齡相仿或更小的男孩女孩死于原可以預防的原因如饑謹和痢疾。造成這些死亡的不只是糧食歉收,而且也有政治上的失敗。這些孩子在為求生而掙扎的時候,眼前沒有一排排的電視機鏡頭,也沒有一個焦慮的世界在聆聽他們苦難深重的聲音。世界幾乎沒有注意到他們死掉了。為什麼?
部分原因也許在於我們知道很難作出反應。如果要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所要求的努力和犧牲,看起來比我們所願設想的更多,如果任何個人作出最大限度的努力仍於事無補,那麼我們很容易會把刺激和道德責任分開來看待。而且,一旦看到任何回應都注定了失敗,曾讓我們一度考慮過作出回應的景象現在就不僅讓人吃驚而且會讓人痛苦。這時候,我們不再對這幅景象作出回應,而是對它所引起的痛苦作出回應了。可是這樣一來,我們對世界的另一種基本聯繫又被分離開了:我們的感覺和我們的感情分離了,我們的眼睛睜著,心卻閉上了。我們視若無睹,聽而罔聞。
環境破壞的可怕圖景那麼多,我們往往不知道怎麼才能清理出個頭緒來。在一一考察這些可怕圖景之前,也許可以把它們略作分類,同時我們的思想感情也可以有個頭緒,以便對它們作出適當的回應。
軍事上有一種分類法,按照衝突的廣度把形形色色的衝突分成三類。一種是地方性戰鬥,一種是區域戰役,一種是戰略衝突。第三種衝突事關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必須從全球範圍來理解。
我們也可以這樣來看待環境威脅。大多數水污染、空氣污染和非法垃圾堆放是地方性的。酸雨、地下水源的污染、大規模的石油溢漏,這些基本上是區域性的。這兩類問題可能在全世界各個地方都同時出現,但是這些問題本身卻不具戰略性質,因為全球環境的運行並未受到影響,人類文明並不因此瀕臨滅亡。
然而,另一類新的環境問題卻影響到全球的生態系統,這些問題是戰略性的。最近40年來大氣中的氯增長了600%,這些氯氣不只彌漫在那些生產氯氟烴的國家上空,而且遍佈所有的國家,遍布南極、北極和太平洋,從地球表面一直延伸到最高的大氣層。氯水平的增長影響到全球範圍內大氣層過濾紫外線的功能,我們把越來越多的氯排放到空氣裏,來自太陽透過大氣層到達地面的紫外線也會越來越多,直到形成對所有動植物生存的一種新的威脅。
全球變暖也是一種戰略性的威脅。二氧化碳以及其他能夠吸收熱量的分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大氣中的濃度幾乎增加了25%。這就影響到地球調節大氣中的熱量的能力,構成了全球性的威脅。大氣中不斷增加的熱量改變了風、雨、地面氣溫、洋流、海平面,從而嚴重威脅到地球上氣候的平衡。氣候的改變又進一步影響陸地上海洋裏的動植物的分佈,對人類社會的居住生活更有巨大的影響。
換言之,由於人類文明突然具備了影響全球環境而不僅僅是影響局部環境的能力,人類和地球的整個關係發生了轉變。我們都知道人類文明一直對地球環境施加相當的影響,有證據表明,即使在史前時代,人為了獲得食物就曾有計劃地大面積燒荒。在我們自己的時代,我們在城市的表面鋪滿水泥,在鄉村精心耕犁養護牧場、稻田和其他種類的耕地。這些活動大規模地改變了地球的面貌。然而,即使如此,直到最近,這類改變對於全球生態系統而言仍是微不足道的。在我們這代人之前,的確可以有把握認為:無論我們做什麼,無論我們能做什麼,都不可能對地球環境造成什麼持久的影響。但我們現在恰恰必須扔掉這種想法,才能從戰略上重新思考我們與環境的關係。
人類文明現在成了改變全球環境的主要原因。然而我們不肯接受這一事實,總覺得難以想像我們對地球的影響的規模近乎於月亮對海潮的吸引,或風力對山丘的侵蝕。如果我們的確能夠改變太陽和地球的關係這樣基本的事情,我們就不得不承擔起一種新的責任,更加明智更加小心地使用這種力量。可是直到今天,我們似乎還一直沒注意到地球上的自然系統是那麼脆弱。
本世紀目睹了兩項急劇的變化,足以從物理實在方面重新定義人與地球的關係。一是人口的急劇增長,每10年都增加出一個中國的人口。二是科學技術革命的突然加速,使得我們能以從前無法想像的巨大力量來燃燒、砍伐、挖掘、移動、改變各種各樣的物質,從而改變地球的面貌。
人口劇增既是人與地球的關係發生改變的一個原因,也是這一改變的明證。若從人類發展史上著眼,就更容易看到這一改變多麼劇烈。從20萬年前人類誕生一直到凱撒的年代,一共有過2.5億人在大地上走過。1500年後,哥倫布揚帆去尋找新大陸的時候,地球上大概生活著5億人。1776年傑弗遜寫下獨立宣言的時候,人口翻了一番達到10億。到本世紀中葉,二戰結束之時,這個數字變成了20億出頭。
換句話說,從地球上出現了人直到1945年,經過上萬的世代,人口增加到了20億。而現在,在一個人的有生之年,就在我自己的有生之年,世界人口將從20億增長到90億。而這一增長此時已經過半。
和人口增長一樣,科技革命也是在18世紀開始漸漸加速的。而且它也以指數方式加速。在很多科學領域中,這一條已經成了定理:最後10年裏的重大的新發現要比此前全部時間裏的重大發現更多。雖說沒有哪一項單個的新發現像原子彈改變了人與戰爭的關係那樣強烈地改變了人與地球的關係,但這些新發現合在一起卻無疑徹底改變了我們開發地球的能力。同時,就像不加限制地使用核武器會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一樣,不加限制地使用我們今天開發地球的能力,後果也不堪設想。
我們和地球的關係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必須看到這種轉變,理解它將會帶來什麼。環境破壞的種種驚人圖景引起我們的警覺的程度也許各不相同,但這些在世界各地都出現的圖景卻有一點是共同的——我們必須鼓起勇氣來承認:它們都是同一個深層問題的症狀,而這個深層問題比人類任何時候面臨的問題都來得更加廣泛更加嚴厲。全球變暖,臭氧層損耗,物種滅絕,森林毀壞——這一切有個共同的原因:人類文明與地球的自然平衡之間的一種新型關係。
我們面臨的問題其實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認識到我們傷害地球的能力的確可能具有全球規模、的確可能是永久性的。我們已經成為造成地球現狀的一個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是認識到我們必須首先把自己看作這個複雜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才能夠理解人在這個系統中的新角色。我們從前習慣於把這個系統看成一個因果作用的簡單系統。現在看來,首要問題不在於我們對環境起了什麼作用,而在於我們和環境處在怎樣一種關係之中。於是,無論我們用什麼方式來解決環境危機,我們首先都需要重新審視人與環境的關係,這包括每一文明內部的種種因素之間的複雜關係,各個文明之間的關係,以及生態系統各種主要自然成分之間的關系。
對我們的思考形成這樣巨大挑戰的,從前只有一個例子:原子彈的發明。美蘇兩國把數以千計的戰略核武器佈置在世界各地。這一事實漸漸迫使我們痛苦地認識到:核武器所蘊藏的力量不僅永遠改變了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關係,而且也永遠改變了人和戰爭本身的關係。兩個具備核武裝的國家之間突然爆發全面戰爭可能導致這樣的後果:兩個國家同時整體毀滅。這一認識使我們變得比較清醒,引導我們從核戰爭的可能性重新審視美蘇兩國關係的方方面面。早在1946年就有一位戰略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核導彈的戰略轟炸“很可能會撕開長久以來一直掩蓋在戰爭現實之上的一種幻覺,這一現實就是——戰爭不再是拼殺,它已變成了毀滅”。
然而,在核競賽的早期階段,超級大國各自以為自己的措施會對對方的想法產生簡單而直接的影響。幾十年裏,每一次部署新武器的目的都是為了讓對方感到恐懼。但每一次部署新武器都導致對方部署更多的武器。有一點漸漸變得明顯了:核競賽問題雖然由於技術變得更加複雜,但它主要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從兩個超級大國的關係中生長出來的。核競賽的基礎是已經過時的戰爭觀念。
這一方或那一方部署某種最新最尖端的武器,或某一方單方面決定核裁軍,都不會最終解決核競賽的問題。解決的方法倒在於取得新的理解,在於兩國之間的關係的轉變。這種轉變包括武器技術的改變,包括防止不負責任的國家獲取核技術。
人類文明而今對環境的威脅已具有戰略性質,全球環境的改變而今也對人類文明造成了戰略性質的威脅。這兩種威脅像核武器一樣把一連串挑戰和虛假的希望擺到我們面前。有人爭辯說,某種尖端的新技術,也許是核動力,也許是生物工程,到時候會解決問題。另一些人則認為只有大大減少對技術的依賴才可能改善生活條件。這種看法至少是太簡單化了。現實的解決辦法最終要求重建文明和地球的關係,要求恢復兩者之間的健康關係。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就必須重新審視導致近年以來那些劇烈變化的全部因素。改變我們同地球的關係,這當然需要某些新技術,但關鍵的轉變所需要的卻是以新的方式來思考這一關係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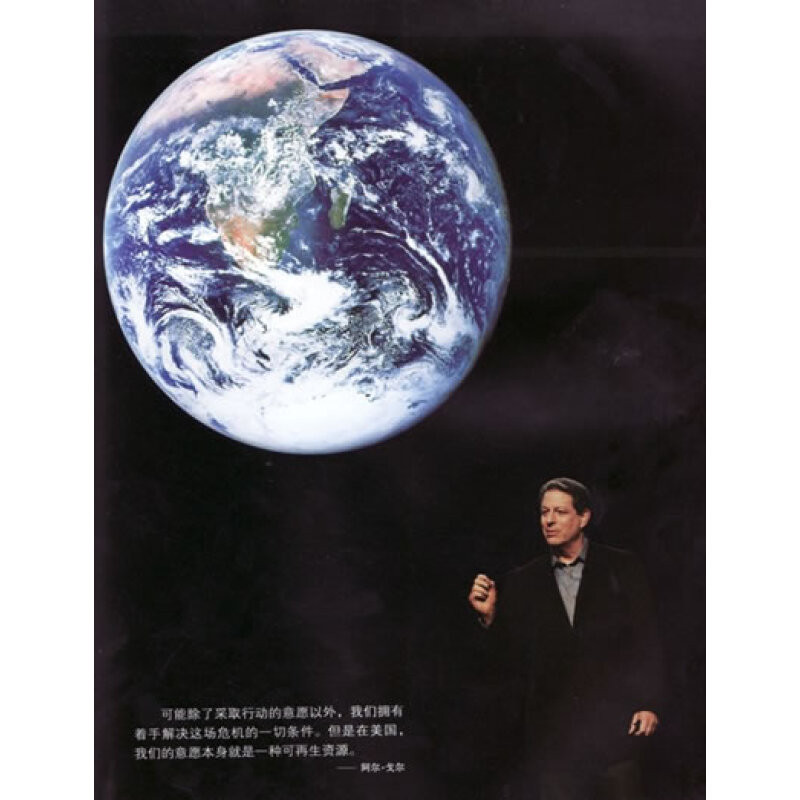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