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篇寫得真好!
看完之後還是很想再次到戲院和大家一感受小人物的悲與喜!
***
【聯合報╱張瑞芬】
真正「千年傳統,全新感受」的不只是小米酒,也是國片。曾經侯孝賢、楊德昌是一時典範,《海角七號》宣示著,現在換菜鳥新一代魏德聖上場了……
在風雨交加的中秋前夕去看了《海角七號》,走出電影院,髮絲整個撲在臉上,那最後一幕猶在眼前,〈男孩看見野玫瑰〉的悠揚樂音中,碼頭上白衣少女拎著大皮箱焦急張望,鏡頭一轉,花白滿頭獨居老婦的背影,青筋滿布的手緩緩拿起了木盒。我索性痛快讓淚水泉湧而出,像要洗去內心鬱悶,也像男主角阿嘉演唱會中的嘶吼:「世界末日儘管來吧!我還是要無樂不作。」外頭風雨猶原,淚水浸過的眼酸澀難當,我的心,卻像洗滌過了一樣清明。《海角七號》,這豈僅是一部網路上傳誦的好電影,簡直是一部住台灣的人都應該撥空去看一看的電影。
「1945年12月15日。親愛的友子:我已經完全看不見台灣島了,你還站在那兒等我嗎?」滿心愧悔的日本男教師,在船舷上悲泣神傷,不能自已,愛人的白色身影,隨著鳴笛聲遠去,在黑暗的海面,他在紙上顫抖寫下。
電影從破曉時分晨光熹微的台北街頭展開。憤氣勃然的青年阿嘉摔破吉他,告別寄居的台北,風塵僕僕一路騎著破機車穿越街巷、高架橋與省道,回到故鄉小鎮恆春。接替了八十歲老郵差茂伯的送信工作,一個寫著「台灣恆春郡海角七番地」的郵包,引起了他的好奇。打開這個原本應退還原寄件人的郵包,漆盒中一張老照片與整整齊齊一疊信件,揭露了六十年前一段日本男教師離棄愛人終戰返國,在蒼茫海上一字一句寫下的沉埋心事。
這時空錯置的荒謬感,很快就被逼近眼前的現實沖淡了。南台灣海岸陽光燦亮,每年的墾丁春吶,結合城鎮規畫與飯店行銷,帶來歡樂、美女、觀光客、商機與錢潮。夏都飯店油光水滑的黃經理,重金請來日籍歌手與熱門樂團,連帶一個與信件中女主角恰巧同名的翻譯小姐友子。滿臉橫肉的鄉鎮代表會主席堅持要有本地樂團,於是由阿嘉詞曲兼主唱,原民警察勞馬彈吉他,機車行夥計水蛙打鼓,唱詩班小女孩鍵盤,賣小米酒的「馬拉桑」貝斯,連原本彈月琴的茂伯也來參一腳,七長八短湊起一個令友子小姐氣炸的雜牌樂團。這形貌氣性都草根十足,生猛有力的一群老老少少,與負責督導演唱會進行的美麗日本小姐友子形成的戲劇張力與反差,就像日與夜,陽光和雨,海洋與星辰,隨著劇情進展,一波波湧上來。
「親愛的友子:十二月的海風,伴隨我進入日本海。我竟分不出這是歸鄉,還是離鄉。我只是一個窮教員,不能擔負時代的罪。」
「海風啊!為何總是帶來哭聲呢?我的淚水,被海風吹乾了。我不是拋棄妳,而是捨不得妳……」
「恆春郡海角七番地」,一個無人識得的地址。拋棄了台北樂團主唱身分,在小鎮自我放逐的阿嘉,正思忖著拿這些信怎麼辦時,因樂團練唱,展開了和友子小姐由衝突到相互吸引的微妙過程,也成了本劇愛情元素的主軸。人人心中一塊荒地,找不到投郵的路。絕望自己在都市混不出名堂的阿嘉,離鄉而無助的友子小姐,再也回復不了霹靂小組榮光的勞馬,暗戀老闆娘的夥計水蛙,滿頭大汗賣不出小米酒的馬拉桑,怨嘆彈月琴沒人聽了的茂伯,甚至連土俗跋扈的代表會主席也恨:「咱這片海這麼美,為什麼就是留不住人才?」
在友子小姐身上迸出激情火花,找到內心的深切感動,使得阿嘉振奮而起,譜出劇中動聽的歌。「當陽光再次回到那/飄著雨的國境之南/我會試著把/那一年的故事/再接下去說完……當陽光再次/離開那太晴朗的國境之南/妳會不會把/你曾帶走的愛/在告別前用微笑全部歸還」。時光渺渺,一首歌猶如穿越時空般,串接起兩個不同時代的故事。中日戀情,主客異位,西洋熱門樂團和戰爭記憶,前衛又懷舊,衝突又混搭。劇中,國、台、日、英語並用,甚至排灣族琉璃珠也來串場,奇異的傳達出異於北都會的南部鄉俚人情,真正生猛到位,俗擱有力,從茂伯等多位配角屢屢笑翻全場,比飾演男女主角的范逸臣和田中千繪還搶戲,可見一斑。
透過日本歌手中孝介低緩悠柔嗓音念出,那個多情男教員,仍在時光隧道裡孜孜不倦的寫著:「海上氣溫十五度。親愛的友子:仰望海上的星光,億萬年前放出的光芒,現在才能看到,多麼令人驚奇。山還是山,海還是海,卻不見了人。在瞬息萬變的人間,我想看一下永恆。」
「在海上遇見迴游向台灣的烏魚群,我向其中一隻寄託了我的思念與辛酸,希望妳的父親能捕到牠。」
「我留下一張妳在海邊的照片。祝妳一生幸福,我會以為這一切都是真的。這世界,誰都配不上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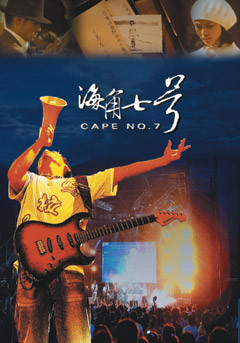
一疊六十年前的信,如同夜空中億萬光年前的放光,延遲了那麼久才收到,卻不是沒有意義的。友子小姐和飯店女清潔工(林曉培飾)一番心事吐露,意外找到了信件的收件人,並及時將信件送到她手中。雨後天晴,演唱會也終於在沙灘順利展開。日本歌手與本地樂團技壓全場,激情與怒吼,引爆了全劇最大的高潮。那片海灘,是蔚藍天光中模特兒巧笑倩兮的沙岸,是阿嘉失意望海的長堤,是夜裡小女孩大大與警察勞馬發呆的基地,也是六十年前英俊男老師幫小女孩友子攝下燦爛笑顏的地方吧!海水依舊,海洋分隔著人心,答案啊!在蒼茫的風中。
「海洋容不下愛情,總容得下相思吧!」
「提著笨重的行李,妳安靜的在人群中站著,戴著那頂不知從哪裡買的白色編織帽。妳站得如此安靜。我的心,像陽光下的黑影,我逃他追,我追他逃。我把愧疚寫成一封信,讓我原諒自己一點點。」
不甘願的,還有國寶大師茂伯啊!人生是一場無法追悔的棋局。安可曲中,老月琴孤獨奏著〈男孩看見野玫瑰〉,那台上執拗的白髮嶙峋身影,贏得觀眾如雷掌聲。「我奮鬥了十五年,結果還不是一樣失敗。其實我並不差。」這句阿嘉酒後的怨嗟,是所有劇中人,更多看戲的台灣人我們,以及導演魏德聖共同的心聲吧!更多的時候,我們是吐槽自己,卻永不放棄努力。
藝術果真不是表面好看的東西而已啊,必須有內在的生命力與價值觀。真正「千年傳統,全新感受」的不只是小米酒,也是國片。曾經侯孝賢、楊德昌是一時典範,《海角七號》宣示著,現在換菜鳥新一代魏德聖上場了。
「親愛的友子:我已經完全看不見台灣島了,你還站在那兒等我嗎?」地已老,天已荒,海水依然蔚藍,日本男教師老了,日本男教師死去,帶著他沉埋的痛苦與愧疚,與櫃子裡那珍藏一生的照片與不準備寄出的信。戰爭造成了離別與缺憾的人生,但南方小鎮,生機充滿,陽光與海,一年復一年。
這世界,明明已經無望,卻又心懷奢想的,是愛情,是人生,也是電影吧。如果這世界有所謂的「療傷歌手」,那麼就有「療傷電影」。在恆春小鎮,國境之南,夢土之濱,沒有結局的故事,寫下了無數感動在人間。
【2008/09/23 聯合報】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