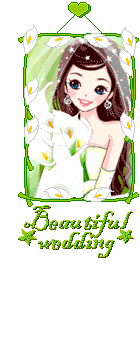【藝文賞析】我與他,與無花困樹之間--黃遠雄詩中的存在世界(三之一)◎辛金順
刊載日期:2008-08-29
1.
我最早嬝甽擊毓祖爾眲O在一九八六年中。那些大部份以左手人的筆名在七○年代間發表於《學生周報》的舊作,後來結集成一小冊的詩集。我就是通過那份薄薄的詩冊去認識我故鄉的一名詩人,認識他在詩的世界中所建構的鐵蒺藜、鷹架、風沙、不斷走動的樹、狂飆的瀑布,以及粗獷峋礪的生活歲月。在他那一系列的詩中,也讓我開始認識了詩。後來我還嘗試以青澀的筆尖探入了他詩中的意象迷宮,企圖探索他在文字背後所舖設的生命光影,但最後所得到的結果卻是一篇粗製濫造的詩評。
而那已是二十年前一份遙遠的舊夢了。如今回頭,我發覺,少年躲在書齋裡的眼睛,實是無法洞穿詩人背後的生活世界,以及他生命的存在處境。對於一支在水泥鋼骨間隙磨練的詩筆,與在鷹架與鷹架之間聶熊菑j氣磅礡的詩句,我所讀到的是處處述說著他那份風沙歲月的生活,卻讀不出隱藏在詩與詩背後,所沉浸於人生體驗裏的一份思辨與豁達。我在尋找淬煉的文字與意象,卻忽略了詩中的性情,而那才是詩人存在世界中最真實的聲音。因此,當釵h馬華詩人刻意在修辭技藝上進行外在的試練和創發,或嘗試從繁複的內在意象圖式中尋求意義的摺疊與展開時,黃遠雄卻仍一如往昔,沉穩地在自己腳下的詩路上彳亍獨行。或部A一切銘文立意,鑿句成象,對他來說只不過是近乎技矣的雕蟲遊戲;也或部A他所在乎的只是如何在現實生活中,逼視人生的困挫與崢嶸,並為自我存在見證?故我從他近期的詩中漸漸讀出了一種生命自然敞開的詩性言說,不論是對於時政、歲月、病痛、追憶等等,在在都指向了詩人自我存有的蹤跡││一種生命在時間裡流動的詩音。
誠如海德格(M.A.Heidegger)在評注荷爾德林(H.Holderlins)之詩時所指出的,詩人是諸神退隱後的信使,他給予了存在一種命名和意義。因此,詩人的詩性言說,展現了自我在場的姿態,生命的光影和聲音。而詩的語言,也幽隱迂迴的指出了「我思」的存在處境││煩憂和匱乏。這種現身情態,無疑成了詩人對世界最直接的反映,生命最真誠的呼聲。而黃遠雄的詩,在這方面常常意有所指,即使是生活情境的碎語,或日常之思的餘光,都可窺見其詩作深處所蘊含的存在隱喻,以及這隱喻背後所展開的自我/世界之間那份辯證與感知的情緒。故從這方面窺探,五十歲之後的黃遠雄,其詩中無疑比過去作品多了一份更深沉,卻又更加淡定悠遠的意韻。
2.
在遠雄最近剛出版的詩集《等待一棵無花果樹》中,釵h詩都是在生活裡淬煉而成的。詩的語言與現實對話,展現了其當下生命的狀態和情境。這一如Wallce Stevens所指出,外在的現實敘述,其實是一種內在生命當下的言說,它通過了語言技藝,使被遮蔽的世界敞亮。像遠雄詩中不時出現的「樹」這意象,指涉的不是外在物的現象,而是存有的投入,由此也給出了生命存在中的一種精神流向。因此從青年時期詩裡那「不斷走動的樹」,延至這本詩集中「要去流浪的樹」,以及「默默守著自己的根」之樹等等,正述說/召喚著一種自我本真(authentic self)的覺知。而「樹」的隱喻言說,其實是詩人的一種現身情態,一種更貼近存在本真的意指。最典型的是他的《要去流浪的樹》一詩:
因為樹林太濃密/他找不到自己/的身影
在此,「他」與「樹」,形成了互涉的轉喻,並開顯了存有的一份尋視。因而,當「他」在群樹(他們)中找不到自我的主體性時,歸屬的出離,遂成了一棵樹的流浪宿命。故不論從身體的流亡或心靈的流放,都是詩人在世和在時間中的一種跋涉;或從存在論來說,是一種「漂流」的存在狀態。而詩中的「浮萍」、「流域」,無疑注釋了存在者無家可歸感的離散意識,以及難遁於天地之間的死亡逼迫:
他回首/祖輩擁有的每一具輝煌/都是躺著/排列的/骸骨
俗世歷史追求的扑~││輝煌的骸骨。這宛如一則存在的寓言,敘述著離散族裔的命運。因此,當流浪的樹「拎著殘存的根鬚」歸來,「所有的樹/被當前的景物/掩臉,震撼/大聲痛哭」。詩的寓言性,一一指向了生命共同體的本質,同類/族裔相哀的存在悲劇。
故從此一詩中言說的存在之思,相當深刻地辯證了存有的追尋與幻滅、空洞與憂哀的情態,這是詩人內在生命的聲音,警醒的獨語。其詩的語言表現不在於修辭的華麗,或意象的精巧,而是在於詩蘊生命的深沉。同樣的,在他的另一首詩《樹總是》裡,「樹」成了一種自然的守護,生命「療傷的風景」。客體的「樹」與主體的「我」,在此存在著生命相互延伸的依義,並由此觀照了「我│世界」的存在處境:
樹總是,默默守護著/自己的根;根在/樹在/無論我走得多麼遙遠/
把傷跡留下/樹料理
「樹在」,一切生活的挫敗和創傷,也因此在日常世界裡有了「根治」的依據。更進一步的說,「樹」實際上已內化成生命的根鬚,靜靜支撐著詩人存在的勇氣。而「在」,給出了意義,使人不會遺忘了自我。這如莊子在《至樂》篇所言的:「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機運之處,自有神性的召喚。至於詩人運思寫詩,旨趣意遙,讓「樹」幻化為多方指涉,卻在生命的觀照下,趨向詩內感知/認識主體「我」的存在敘述,由此展示了其精神的無限追索。
如在《等待一棵無花果樹》和《真正的無花果樹》二詩中,詩人別有機鋒,辯詰著「無花果樹」的一分存在意識。前一首,詩無雕薄A卻音節頓挫地陳述著渴望有人帶「我」去瞻仰心儀已久的一棵「無需開花/卻果實纍纍的/神奇樹」;雖然至終詩人遲遲未有行動,然而此樹,卻隱然在其內心茁壯,並生機勃勃的往外攀延伸張著。至於後一首,則以近乎明朗的口語,敘述如何在日常生活的競逐與繁忙間,錯過了時時照面的一棵「無花果樹」,最後卻與一名友人輾轉尋訪下,而終於找到了它。詩的末尾寫道:
他說:/哪,你看那棵/無花果樹││//我終於看見了機緣/冥冥
之中或早有安排/在我與他、與無花果樹之間/開展了盡在不言中的/
契機與/氛圍//他說:哪,你看那棵││
兩首詩都以「無花果樹」開顯了存有的自我本真,尤其是當詩人處在操勞世界的忙迫之時,往往會讓自己陷落於「存在的遺忘」裡,就海德格而言,這是一種沉淪,或遮蔽,而「無花果樹」,做為外在之物,因緣觸動了詩人生命之感,讓詩人之思得以迴向自身,或復歸於自然的存在之境。「樹」在這兩首詩裡都是實物虛寫,是詩人靈視下的意念,前者於「繼續等待」中呈現拳曲之思,後者卻在「我與他」的共存(co-existence)之間,形成了某種存有的召喚。從現象的把握上,「我與他,與無花果樹」(在世的共存/因緣結構)在靜視的照面下,遂有了其內在的生命聯繫,而詩人就是通過對外在事物/他者的互動,觸發內心的感知,進而把握住「世界」的種種現象,由此,存有者也在其中得到自我揭顯。故從這方面來看,詩與思,與語言的敞開,似乎讓這兩棵「無花果樹」,在存在的詩意裡,產生了可以仰視的高度。
而貧乏的年代,詩人何為?無非不就是在無數混沌的暗夜裡,在燈下,堅持以筆撐起孤獨的身影,並循著神思的指引,孜孜走向生命道路上最遙遠的那個地方嗎?這過程,心靈的內索,自有其之存在境界的參照。是以「無花果樹」的證成,歷經了三十年「走失的詩和詩人」之後,遂有了詩人禱詞式的誓語:「做一個快樂、自足/努力不懈的吉蘭丹人,我/攤開紙與/筆,把記憶栽種/把足跡根植/澆鑄成日後我回眸/一棵永不凋謝/的大樹」(《大樹》)。因此詩創作,不只被黃遠雄視為生命創傷的一種書寫治療,而且也逐漸成了銘刻時間,紀錄現實,展現存有的認知意志。這是詩人存在而真實的證據。所以,從「無花果樹」,到「一棵永不凋謝的大樹」,這一書寫過程的跨越,之間,我們可以窺見了詩人在詩裡的自我觀照、省思、情態流露等等的存在蹤跡,那是感知/認識主體說出自己的一種解蔽方式,一種屬於「根在/樹在」的存有詩性言說。(3之1)※
來源:更生日報
++++++++++++++++++++++++++++
文章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