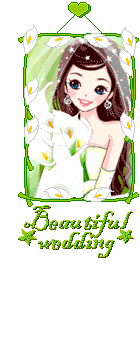【藝文賞析】我與他,與無花果樹之間--黃遠雄的詩中的存在世界(三之三)◎辛金順
刊載日期:2008-08-31
這存在的辯證,揭示了存在之兩難:即趨向獨立自我,或成為群眾共在的常人(das man)? 詩中彷似給了答案,事實上,在自嘲之下,卻留下了空白。而在寫於二00七年,置於詩集末尾的一首詩《面對》,我們似乎窺見了詩人面對歲月的某種坦然,之前生命的鏗鏘、躁鬱、不滿、悲憤、掙扎等等,盡全化成了:「坦然面對,一支鎮壓部隊/驢伏著動輒得咎的數據/延宕、沓踏/不可預設的行程」,以及「一吋一吋,我們慎重其事地造勢/為節奏渙散的隊伍,再三/夾道恭候、迓迎行將蒞臨但/終究會/煙硝雲散的一支曙光/洗塵」,舒緩的語言節奏,淡定的心情,陳述了生命面對歲月鎮壓的一種妥協,這是存在者「不得不」的生命展現,一種││智者對自我相處的最好方法。
以物象言詩,復歸於自我生命的舒展,是黃遠雄揭示自我的一種表現方式。而詩中物象的流動,與輻射出的符徵,讓詩有了迴旋的餘地;然而,有一小部份的詩,卻因為情緒的把持不住,而使得語言陷於意涵外現的窘境,這無形中也削弱了詩質。然而,就整體而言,遠雄的詩在存在言說的表現上,還是有其自我獨特的視域和聲音的。
4.
黃遠雄的《等待一棵無花果樹》,詩作排版以作品刊登日期為順序,分成四輯。故順此時間的流脈,讀者可以在翻動詩頁間,一路追蹤詩人深埋於文本之中的存在蹤跡,並以此進行「召喚的嬝炕v。而每首詩的詩題,以注音符號標注,予人一種回到原初(作者小學時)拼讀的歲月,這種語音的懷念和追憶,成了詩人「最後的在家」││存在的見證。
或部A在這本詩集中,釵h詩潛伏著語言主體的自我生活歷驗,以及感思;因此,有些讀者可能在探入詩內,跋涉之間,難免會遇到一些嶙峋磊石的阻礙而心生挫折,然而類此發乎生命之詩,若不搬開詩人胸中塊壘,豈能窺得其精神生命之究竟呢?接下來的問題是,讀者如何能搬開詩人胸中的塊壘?這不就是要回到孟子所說的老問題:「頌其詩,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萬章》下篇)的知人論世之說?當然,如果你把孟子的這一老套說法撇開,而信仰羅蘭‧巴特(R.Barthes)的「作者已死」,並認定一切都必須復歸於「文本」,「文本」之外無他物,以及強調讀者創造文本的意義等,那麼,就會引伸出另一個問題來,即為何無法在黃遠雄的詩語中找到一個生命感的共通?甚至想像?
黃遠雄的詩,常以現實的經驗、存在、以及通過當下的生活世界與感覺出發,這形成了他詩中在世的一種態度,或姿態。這種姿態不依傍於理論、知識,或主義之類,而是出自於生命本真,並藉由與外物對話,或隱喻;或比興,甚至有些詩,直白地進行「即物書寫」,訴諸於政治現象。這些詩強調「寫甚麼」,甚於「如何寫」的表現,然而同在這創作基礎上,其詩卻不若游川詩作的短小精悍、凝練、狠快與精準(當然,這是指游川的一些名作而言,因為游川也有些作品,因語言鬆散而垮掉,然而誰又能每一出手都是名作呢?)。再者,游川的詩取徑於台灣「笠」詩派,強調現實、批判和抵抗的精神;而遠雄的詩,主要卻還是在於生命的內視,自我存在的揭顯,因此其詩語言寫實,甚至舖陳、更有些詩介於語言概念化和物象的隱喻之間,使得詩的思維性質遠勝於想像,而導致提供給讀者的想像空間變小。另一方面,一些詩中所陳述的心理創傷,形成了一種壓抑循環的情緒,這與控訴現實的言談,常常相互輻湊,而成為一種私我的獨白,這使得缺乏此一生命歷驗的讀者,在嬝玟o類詩時會產生障礙;或曰之:隔。
在此做個粗淺的比喻,遠雄的詩語言,性趨木質,木質上雖有其年輪(時間)的切片和佈滿生命的紋路,然而卻密實嚴禁於一些自我的隱喻之中,往往使讀者不得其門而入,或產生誤讀(這是在「作者論」的意義下說的);它不若皺摺的皮層性語言,在皺摺和皺摺伸縮之間,因含攝了更大的彈性/張力,使隱匿其間的生命/歲月意涵,於摺層裡,有著可供人想像的空間;而且經由展讀,讀者也可以依照自己的文化脈絡和思考,隨著皮層語言紋路的開展而擴張。畢竟,詩的流傳,還是在於它的開放性和「多重意義」(connotation)書寫特質上的。而遠雄其實是自覺到這一點,在「文字密雨不透」和「匿附的符碼」(《墜樓》)中,他曾以戲謔的語調詢問讀者:「你在看我的詩嗎?你在讀我的詩嗎?你都懂了嗎?」並對讀者的誤讀和調侃不以為意,且以詩言志,堅持著自我詩法的理念,自比為蠍,高舉毒尾,大有生人勿近之意:「我倒喜歡,獨個兒/像一隻戰意鼓鼓的/毒蠍,鉤起紅燈籠般/虛掩的意象,蠆尾/高豎」(《蟹與蝎之間》)。
當然,做為一名詩人,不若馳騁商場,遠雄是有其寂寞的。然而,也因為做為一名詩人,他更能在風沙歲月之後,去聆聽和省思生命心靈的悸動;並以詩揭示自我。這是其之異於「常人」之處。而讀遠雄的詩,我常讀出了其詩的生命姿態,這樣的姿態,使他的詩在馬華詩壇上,有著獨特的聲音(在馬來西亞,一名作者若能於創作中,給出姿態,就可說是很不簡單了。而這姿態,包含了創作理念、語言風格、作品生命的意向性等等。若無姿態,實難成「家」)。如今,這棵不斷在風沙中走動的樹,已然移植半島南方的江岸,成了一棵無花果樹,詩果纍實,自成天地。然而,這樣的一棵無花果樹,在熙熙利來、攘攘利往的街市,又會有多少人停下腳來注目呢?
5.
現今,我在異國的桌上翻開遠雄的詩集,翻讀他那在歲月中一路遠行的文字,突然感覺,釵h懵懂的少年歲日都回來了,一如釵h年以前,就在東海岸那多雨的小鎮,在十二月季候風翻飛的雨聲裡,我低頭用自己四音不全,認字不多的華語,就雨點校讀著他的詩句。一句一句,都是自己青春的聲音。而現在,在島嶼暮春的校園內,在人到中年的時刻,仍能夠嬝爸鴩茼菑d里之外故人的詩句,無疑是件愉悅的事。而我相信,在創作的路上,就如遠雄自己詩中所說的:只要根在,樹也會在。而我更相信,只要樹在,詩也會在。是的,詩在,故我在。
而詩對詩人而言,猶如暗夜裡的燈,燈亮著了,詩人才會辨知自己存在的位置。
是的,就如《真正的無花果樹》中的那句:「我與他、與無花果樹之間」的位置思索,那裡頭,應該會有無限生命的契機,在遠雄的創作中,不斷召喚,不斷追問,並向前繼續開展著……。(3之3)※
【後記:十二年前曾答應要幫遠雄寫一篇評論,然而詩稿帶回台灣後,只寫了前面的第一段,後來輾轉遷移,詩稿不知何時卻給弄丟了。一九九六年,遠雄出了他的第二本詩集《致時間書》。今年新春回鄉,路經新山,見到遠雄,被告知說其第三本詩集《等待一棵無花果樹》即將由馬華文學館出版,我忘了此前諾言(真是輕然諾之徒),又答應他說詩集出版之後,會寫篇評論。四月初時,收到這本詩集,為免重蹈前諾之輕陷c跡,遂翻出十二年前所寫的第一段評文,稍加修改,然後續著寫,費一天半時間完成。心想,這十二年路程,像是個召喚,終於,算是還了這一份心債。二00八.四.二十四】
來源:更生日報
++++++++++++++++++++++++++++++++
文章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