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作家事進攻台視,直播介紹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改編電視劇。陳栢青(左)化身小說裡的小圓圓,顏訥是大鼻獅。(圖/顏訥提供)
只想當好學生,沒辦法成為好作家
●陳栢青
是因為才剛起步,或是正揭褲管怯生生腳尖涉入水面,儘管人家問「那是什麼感覺?」、「你到底怎麼做」的時候,會手扠腰大聲說:「大姑娘划船不靠槳,靠浪。」但其實心頭還是有點怯,人家問你工作是什麼的時候,交錯回答「寫東西的」、「文字工作者」,到底沒辦法輕易回答「作家」。覺得褻瀆了什麼。也許這個當下剛剛好,才剛成為這個行業新鮮的肝,水還很多的筆,能射過山,還沒滴腳邊,我們可以聊聊成為作家第一年的感覺。
成為作家第一年,發現光寫作不能謀生。不夠謀生。你要去演講。去評審。去寫很多雜稿。
成為作家第一年,發現人生至少應該有兩面。自己必須去做的,和自己喜歡做的。「必須」無關「喜歡」。「喜歡」未必「必須」。我一直都覺得「做你喜歡做的」是一種謊言,當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成為必須去做的,二合一。喜歡就變質了。因為喜歡的先決條件是一種選擇,可以任性的。那包括你可以拒絕,喜歡才能說no。但成為工作,那便沒有轉身的空間,很多事情都是硬碰硬,實打實的,咬著牙上的,你會感覺到很多雜質,你會感覺到裡頭不和諧的異音。成為作家第一年,要接受的不是這份無奈。而是要整理出原本到底喜歡什麼。第一年要我反覆思索「你到底喜歡寫作的哪個部分?」──書寫完成的瞬間?對更艱難題材的挑戰?讀者驚喜剎那的那張臉?
成為作家第一年,最大的心得是,只想當好學生的話,就沒辦法成為好作家。我一直都是好學生,所謂的好,其實也就是不犯錯而已。剛好踩線過關就好了。功課有交就好了,天分都發揮在發懶和找空子鑽上。寬容自己沒有上限,事事都和下限比,那當然會有很多餘裕,覺得自己有無限可能。
成為作家第一年,沒人管你了。 連我也沒辦法管住自己。心裡的猿,意中的馬。而且你每天可以逃。你有一百種理由,看別人的書說是找資料,一個上午躺在床上發懶或一口氣看完Netflix一整季影集說是休息。總是一回神又是下午三點鐘。什麼事都沒有做。窗前影子更伸長一點,身體退後一點。還有很多地方可以退。發現自己沒辦法退。
成為作家第一年,最大的發現是,不用上班了,所有的日子都是假日,就等於沒有假日。沒有人是老闆,那你就是自己的頭。只能自己監督自己,自己承擔失敗。成為作家第一年,你發現自己每一刻都有無限選擇,但沒有做下選擇,就等於沒有選擇。
成為作家第一年,明白的是,寫作和拜神一樣。終究是只有他和你自己的事情。不和別人比較。跟自己競爭。有沒有做到,到底只有你自己知道。你過不了自己這關。
雖然聊的是我們成為作家的第一年。但我一直覺得,這個問題不只對我們重要。回答這個問題對整個台灣文學都很重要。只是人們問問題的方式會跟我們不一樣。他們會問,這一代七年級、八○後為什麼這麼慢成為作家,好像有一種遲緩?有一種觀望,出場很早,但出手很遲。群體很龐大,但露臉三三兩兩。聲量大,生產力弱。代表多,代表作很少。
我們的第一年,時代裡已經很後面了。
我成為作家那一年──如果用狹義「出書」來看何時成為作家的話──開卷在那年停刊。新書銷售量又到了新低點,更多書店收攤。編輯抱怨「這世道越來越艱難了」。
我成為作家這一年,幾個模式確立了。以臉書作為銷售宣傳渠道。新人勤跑書店做宣傳。新人就是腳勤。看榜看的是博客來排行榜。虛擬決定實際。數位就是數字。
要我說,那是因為,在我們的第一年,上個世代的模式到了最後一年。一個變化是,文學獎、隨意結集在市場上早不管用了。讀者想要的書往往是一個明確的概念,一個企畫。一個清晰的形狀。有時候是一個名字,有時是一個口號或是鮮明的關鍵字,前者就是明星作家的生產,後者預言金句體的流行,以及一次成功的出版帶起關鍵字後一本書變成一整個櫃子同名作的複製人大舉進攻。
我成為作家的那一年前後,作家需要經營臉書。作家販售的不只是無形的理念,而是有形的臉。作家必須讓人可感、可觸。
那意思其實是,我們和所謂的故事力、故事包裝盛行大概在同一個時間前後。
我們是把自己活成故事的第一代人。
故事有頭有尾有中腰。有一種簡化。他單純。讀者想聽這樣的故事。而且越來越需要這樣的故事。有起伏,有啟示。你以前是寫故事的人,但你現在必須變成故事。
而一切傳播媒體提供這些條件,甚至逼迫你生產。你要在臉書上生出自己的臉,你被迫成為第二個自己,你貼相片,你在你預定的寫作之外寫你的生活,我們的第一年,故事和說故事的人被顛倒了。
過去我覺得世界是非常複雜的。作家的工作是將複雜變為清晰。從混亂中理出脈絡。條理出感覺的形狀。去問問題。
但如今,人們要的不是清晰。而是簡單。不是脈絡。而是S.O.P。不是「你可以這樣」。而是,「你這樣做就能xxx」。滿足於感覺,無法訴諸理智。想要一個形狀,只能接受一個。不想要問題。只追求答案。
我們是在這樣狀似「一切終結的年代」開始第一年。我每天都想,千萬不要讓他成為我們寫作的最後一年。心中積攬的東西以後寫一個少一個了。不要讓過程成為結果。讓目標變作阻礙。
成為作家第一年,試著回想什麼是「作家」,總感覺現在的自己不像,也不能是作家。但自己在更早以前也許已經是作家了。在網路明日報,在別人的留言板裡,那時候總覺得留言寫得比此刻的作品精采。回應別人比表現自身還熱情。想要的不是展露自我,而是如何與別人接軌。真心明白寫作超越表達,而體現為一種共感。不是為了突顯自己,而是「讓所有人在裡頭找到自己」。成為作家第一年,我終於找到自己了。何其軟,無比氣弱。而我怕跟著失去別人。
成為作家第一年,我學會的是,你要學會明白軟弱。並且學會如何勇敢。
你要學會擁有熱情。對寫作,對世界的熱情,像清晨的太陽,像臨界點正噴發的火山。要持續對世界打開那個敏感的苞蕾。不滿足其滿足。
你不要怕別人審度你。你要學會自己凝視自己。建立標準。勇於坦承,不隨便遷就,敢於改變。
你要擁有目標。如果沒有,就去找一個。你不要害怕去愛。如果受傷了。頂好你是寫作的,寫作不會讓你不受傷。但會讓世界上某一個受過傷害的人知道,他並不孤獨。
最重要的,「最不應該忘記的,就是,好好享受這中間的過程。」
成為作家的第一年過去了。成為作家的第一年還很長。很多年過去,都希望還保有第一年的天真。
不知道大姑娘你呢?
為了被看見,我們要長臉
●顏訥
成為作家的第一年,幸好大姑娘你已在前面破浪了。
成為作家的第一年,被問及「終於成為作家興奮吧?」大姑娘我儘管有時也想斜倚靠墊,搖晃紅酒杯嘴唇像染著鮮血,滿不在乎嚷:「老娘的鞦韆不用推,全靠蕩!」但明明一雙粗腿死蹬在鞦韆下,肩上扛著鬼,自以為妝容完美蕩起來,旁人看來是眼線橫流前後晃。
於是,苟且拿起作家title卻總抬不起頭,感覺像是借來的,有一天得還。不如心虛創造一堆近義詞,「寫作的人」、「文學愛好者」,等別人為統一格式建議不如用作家好嗎?才推三阻四答你都這麼說了那好吧。說起來,成為作家的第一年,的確回春成大姑娘,但欲拒還迎多,浪蕩時候少。
只是我沒想過,阿青你竟也有一樣的症頭。
對我而言,你成為作家的第一年,應是前塵往事才對啊。不管在哪一個階段,說起「陳柏青是作家」,無論如何都不會有人懷疑,甚至還有萬千文學少男少女暗中想成為你。
所以,當讀到你竟有冒名頂替,深怕褻瀆了這個稱謂的惶恐時,我突然感到悲傷。「成為作家」的重量確實無可想像巨大吧,好不容易推石上山,在山頂或許真有一秒確定自己值得這一片風景;但又隨即預感墜落之必然。下一次能爬得更高嗎?又或者,上山只是偶然,也許不會再有相同的運氣與力氣,去滾動一顆超載的巨石,而終將在半途壓死自己。
成為作家的第一年,我被無時無刻存在的「這樣真的夠好嗎」,找不到度量標準的恐懼捕獲。面對自己,背後總像站著一排想像的評論家,一邊轉身吼閉嘴有問你意見嗎,一邊默默把剛完成的五千字挪進垃圾桶。
為什麼我們這一代人共享遲緩。為什麼觀望成為習慣。為什麼明明頻頻出手卻總是心虛稱自己剛出場。就算寫了十年還想被歸類在新生代。我們趕上文學獎枝繁葉茂的時代,又養成於網路社群掀起巨浪的前夕;比起前一代,被看見相對不難,比起下一代,又免於被巨量訊息淹沒的困惑。可萬一擁有了時代給予的幸運,仍舊失敗,沒有時不我與可當托詞,那會否就只剩下自己能夠怪罪了。
如此一來,要為「成為作家」負責多可怕。如果永遠只是新手多好,始終停在開頭,一如你說,一切都還有可能,等著瞧,我們不只是這樣而已。走在深淵旁但只是路過,失足就說幹有人推我,害怕終於有勇氣負責,就得承認自己不過爾爾。那一刻來臨時,還有幾個人能歷劫歸來,說跳下去再爬上來就好呢?
我們是被卡住的一代,是巨嬰也是老人,幼稚又早衰。我們有龐大的群體但不必群聚,或許因此缺少一起為台灣文學幹大事的使命。可比起後浪,我們又不夠個人也不夠自由,上一代給予我們的那麼豐美,要怎麼才不算辜負呢?從網路入場容易想像自己還沒通過「嚴肅文學圈」認可;從文學獎出道經常焦慮自己只在小圈圈嗨而已。關於看見與看不見,成為作家的第一年,人人都說出版業的winter is coming,長城雖然沒倒,但還搞不清楚異鬼在哪裡。銷量奇低,出版品項奇多,以書養書,卻養不起自己。很多人出書,草原變大了,要燎原卻變難了。
我喜歡你說的,我們是把自己活成故事的第一代人。為了被看見,我們要長臉。
成為作家的第一年,我被自己的臉壓垮了。以為新的行銷模式必須多生產內容,才不會被演算法擠出去。於是,在社群媒體上最好敏於風向,善於製造事故來製造故事。說話以前是慾望,現在成義務,直到分不清楚說話是「喜歡」還是「必須」,直到面對自己的創作,也已經無話可說。
成為作家的第一年,常常幻想讀者患有FOMO症,但其實害怕與人失去連結的,根本是自己。越不確定群眾的邊界在哪裡,就越不確定自己在場內還是在界外。
為什麼寫作?為什麼出書?什麼是文學?散文究竟是什麼?感覺一年過去,我耗竭全部的想像力,生出好多故事,才有辦法回答這些問題。不可能說其實還不清楚文學是什麼,出書是因為自己其他方面太廢需要想辦法確認自己還有寫的能力。我還沒學會不怕別人審度,而搜索評價又太容易,我害怕自己想不出厲害的故事,清楚的議題,聰明的企畫來說明作品,我害怕讓人失望也害怕讓自己的作品失望。我還疑惑,在文學低到塵埃裡的時代,作家作為故事本身,是不是有義務把文學抬得比以往更高,才能開出花來呢?
然後一年過去,我凝視自己,開始看不清楚如今這張臉,是天生的模樣,還是進場維修好幾回。我開始懷疑自己用各種故事去描摹宣稱的文學觀,其實已經比作品本身更龐大,像一張空頭支票,總有一天會跳票,信用會破產。
是在這樣的一年裡,心底總惦記著言叔夏說的:「寫作和現實勢必要分得非常開,才能夠各自保護他們。」
可在重複對人調動內在,說明自己的過程,越來越找不到散文與生活之間互不干擾的距離。所有以為透過寫作的延遲性爭取到與傷害的時差,在還原、組裝成適合現身說法的語言,與現實中自我身分疊合時,瞬間都被取消,沒有遁逃的可能。我在眾人前揭露傷口,發現自己還沒準備好,又試圖遮掩、修整傷口,最後彷彿變成表演傷口。於是我感覺自己過分真誠,同時又過分虛假。那會是來自某種約定俗成,散文作者與讀者奇怪的默契嗎?寫作之內的我等於寫作以外的我,有人說寫散文必須誠實,還可能來審度、驗證你的誠實。以至於,作品一旦被否定,我便彷彿感覺作為人的自己,也一同被否定了。我還不知道,該如何向人說明以語言重組情感與事件的過程裡必然起的化學變化,怎麼樣的現身才算誠實?
所以,成為作家的第一年,我嚴重地感到作品與自我太不同一,卻又殘酷地感到作品與自我太過統一。我反省自己寫得不夠好是因為付出不夠多的自己,我又僥倖也許是還沒付出全部的自己所以才寫得不夠好。
可是,在這一年被困惑反覆碾壓的時光裡,幸好有你告訴我你的軟弱,於是我更多的讀到你的勇敢。是在此刻,我不免想,還有文學真好。謝謝你讓世界上某個正經歷作家第一年而充滿害怕的人知道,他其實不孤獨。這樣想著,也許就能容許自己帶著疑問與軟弱上路,往下一年跨過去了吧。
預備下一次墜落,也還有等自己爬上來的耐心。嘿,阿青,我們深淵旁見。
●陳栢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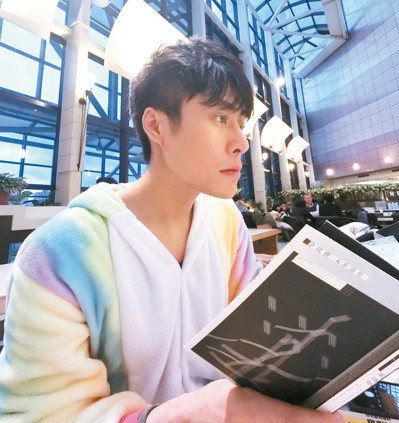
陳栢青。(圖/陳栢青提供)
1983年台中生。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畢業。作品曾入選《青年散文作家作品集:中英對照台灣文學選集》、《兩岸新銳作家精品集》,並多次入選《九歌年度散文選》。獲《聯合文學》雜誌譽為「台灣四十歲以下最值得期待的小說家」。出版有散文集《Mr. Adult 大人先生》。
●顏訥

顏訥。(圖/林予晞攝影,顏訥提供)
1985年生,城市裡的鄉下人。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研究港、台文學傳播與唐宋詞性別文化空間。創作以散文、評論為主,得過少數文學與創作補助。著有散文集《幽魂訥訥》,合著《百年降生:1900-2000臺灣文學故事》。
聯合副刊2019.05.06
文章定位:

